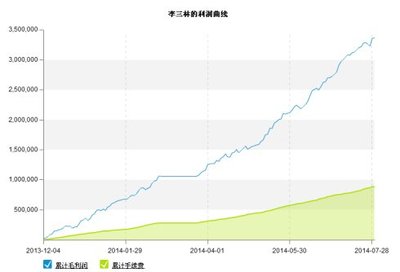从陈丹青到何美欢:也说民国范儿
果实博中说到民国范儿,眺山评曰“不可追”,果实回曰“是不敢追吧?”我辈庸碌,不可与不敢,实无二致。恰巧教师节来临,心中更回荡着因何美欢老师故去而生发的许多情绪。草草几笔文字,哀思所至而已。然则仅知哀与思,却是对不住她万里行来一力耕耘这片贫瘠土地之心的。
既如此,为何又要扯上陈丹青?一个爱发言的画家,一个不爱涉及“公共”场合的法学家,他二人哪有半点关联?
他二人确无半点关联,却有一点共同:都曾于清华大学执教,都自清华离开。陈丹青2000年起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因研究生招生及教学管理问题产生对于高校教育的莫大苦恼,于2004年末请辞清华美院教授职务,2007年离职。何美欢在清华全职教职开始于2001年,结束于2008年7月,后仍在清华担任暑期课程。
以二人在清华的经历来看,陈丹青是铩羽而归,何美欢则赢得一片美誉。若说陈丹青不合于教育体制,何美欢又何尝不是异类。前者于清华大学美术学2002年教学会议的发言,以“关于绘画专业的‘前瞻性’意见”之标题收入《退步集》,直击中国艺术教育症结;后者则以长文“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发表于《清华法学》,直指中国表面繁荣的法学教育之弊端。
陈丹青的美术是装饰品,何美欢的法学也是装饰品。前者装饰墙壁,后者装饰权力。故此,法学贵为显学,美术么,则是为人民群众生活增色添彩之物。故此,陈丹青想要的学生被外语、政治卡住,何美欢则不必担心没有资质大好的学生供她来教。或许,这就是两人在清华收获不同缘故之一吧。
陈丹青告别清华美术学院,用的是一纸辞职报告,言道“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
何美欢告别清华法学院,用的是一场题为“商法救国”的演说,亦颇有深意。何美欢在法学院,拥有教学之主动,她的普通法课程,所占用学生之时间,足以令其余课程无立锥之地。对于法学教育体制,她有许多批评,在实际教学,她因为并不领取特殊报酬并无特殊待遇而有相当的自由。
陈丹青因教学之勉强而苦恼,何美欢之苦衷,却未曾听到只言片语,只听说她几年间不曾有时间体检,需要休息。从那场题目浩大的告别演说之细节来看,也许亦疲惫于教育目标之偏差,其本愿不能达成,亦不复能承受身体的透支。
心力无法付出,是痛苦;心力全部付出而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亦是痛苦。何美欢比陈丹青幸运几分。因为法学院之于清华,毕竟比美术学院要紧些;也因为清华法学院尚未成为国内一流之时,已先走向世界了,明理楼从来都不缺少顶着各色访问教授头衔外国来的讲几堂课的先生们,何美欢的课程于是比何美欢重要,于是她可以尽心力于教学。陈丹青本人却比陈丹青的课程重要,于是他被极端重视,同时被忽视。
陈丹青在乎的事情,是能够帮助有天赋的青年走上艺术之路。何美欢在乎的事,是让中国的精英学子成为高端法律人才,他们应当参与国际商事规则的制定而不是仅有自己赚钱的志向。他们爱自己的学生,因而痛心或遗憾于学生之道路之走向。
聘用他们的美术学院和法学院在乎的事情是什么?美术学院在乎有陈丹青可以拿出去显摆,在乎引进了人才这个成绩;法学院在乎有中国大陆独一份的全英文普通法课程,在乎可以骄傲学生能无障碍去北美深造……整个学校都还在乎有多少学生加官进爵或啸傲商界或成什么家当上什么长。
每每提及大学,总不免惹来一堆“江河日下”的叹息,亦不免惹来对民国范儿的思慕。对教授们的赞美,“民国范儿”绝对是无上褒奖。按照陈丹青的说法,民国范儿主要是指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儿,那股藐视权贵心无挂碍的劲儿。陈丹青本人,便是民国范儿的。何美欢呢?生长于香港与北美,坚韧执着勤奋,亦是民国范儿的。
民国范儿而且执教当下,并不容易。倘若没有行政领导回护,你将孤单,你将被驱逐,你将被边缘。而奉行无单位主义,则很难有践行言传身教的可能。这就是所谓体制,以及不可不敢之缘故。

陈丹青显然是被很多人认同的,然而这些内心认同者却走在另一个方向,也就是体制框定的方向。何美欢是被学生赞美崇敬的,在“学术圈”,她却并非常识,亦有许多人对她直率的关于法学教育的观点以文章“商榷”。毕竟,大家都圈在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的套子里,能不在乎各色量化评估已是有个性的另类。有几人还真心在乎教育该是怎样?
徐友渔对陈丹青辞职事件有篇文字,末段云:“……在慷慨激昂的谈话之后,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开会、布置、填表、争经费、争项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坚决和彻底,难道不可以多多少少为改变不合理的体制尽力,而不是一面批评,一面却支持和巩固,以至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
托母校的福,亦结识不少什么学家,不少什么长,说起当下弊病,都是一套一套的。而从没见哪个身处重要位置的人有所行动。名士派头的教授,一面批判教学管理,一面又陶醉于通过量化、表格得来的精品课程一类的荣誉。
只袖手清议,大人物可为,因为他们可以吃老本,他们已经站得很稳,不用承担不作为的苦果。而年轻人呢?更年轻的人呢?只好等着吃苦果。所以必须有人不再袖手,而不是等着他人出手。大事一时管不了,份内的工作,总可以做得更纯粹些。比如教师,不再理会各色短视的评估何妨?
再说两位民国范儿的教授之于教育体制。陈丹青被困在排定的课表里,被体制所选择用以证明某种成绩,既不自由,只好归去。何美欢呢?即令体制亦用她来证明某种成绩,而她自己出资出力,另起屋宇,鞠躬尽瘁,便有再多的条条框框,能束缚她几分?所以我以为,陈丹青不可学,——以退却的方式归去即失去了有所作为的机会;何美欢虽也选择告别,却是我教师职业的标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