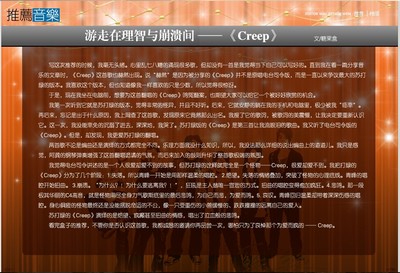今天一口气看完了《挪威的森林》,如果我是渡边彻,我肯定最后会选择绿子的,那结局我觉得也是这样的。直子只是一个虚幻的想象,就像千与千寻里面追寻的所谓爱情一样,跟绿子这样的人呆久了,会毫不犹豫义无反顾的爱上她,她就向“春天的小鹿”,喜欢她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如果寒是直子的话——现在看来估计是了,我如果能找到属于我的小林绿子,这才是一辈子最幸福的事了。2012.4.29
下面摘录都是经典的场景啊,不过是少了医院照顾父亲的情节,那个情节也很好啊,这些情节真是妙啊。
一、邂逅--“渡边君??”
这时候,我发现有个女孩常有意无意地盯着我看。这女孩剪得一头极短的短发,戴着一副墨色的太阳眼镜,穿着一套白色的迷你棉质洋装。我因为不记得自己曾见过她,便自顾自地吃着,但随即她却站起身走向我。然后便一手支在桌子上,喊我的名字。“渡边君?”我抬起头,再一次端详她的脸,但不管怎么看,就是不觉得眼熟。她看上去相当显眼,倘若见过,按理说是会认得才对。再说学校里喊得出我名字的人也并不多。
“我能不能坐一下,还是待会儿有人会来?”
我虽有些不解,但仍然摇头示意。“没有人来。请坐吧!”
于是她便大剌剌地拉出椅子,在我的对面坐下,从太阳眼镜后面直盯着我,然后又将视线转向我的盘子。
“看起来很好吃嘛!”
“好吃呀!这是香菇肉卷和豌豆沙拉。”
“嗯!”她说。“下次我也要点这个。今天已经点了别的了。”
“你点了什么?”
“通心粉。”
“通心粉也不错。”我说。“对了,我是不是曾在哪儿见过你呀?我倒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呢!”
“由里皮底斯。”她简洁地答道。“艾蕾克德拉。(译注:希腊神祗)‘不!连上帝也不听不幸的人说话了。’刚刚不是才上过课?”
我盯着她的脸。她摘下太阳眼镜。我这才想起来。原来是我在“戏剧史第二部”班上曾见过的一年级女生。只是发型全变了个样,一下子认不出来。
“暑假前你的头发还在这儿嘛!”我用手指了指肩膀以下十公分的地方。
“是呀!可是暑假就烫了。烫起很糟,看起来很可怕。当时还真想死呢!真的很糟。就像头上缠满了溺死了的海藻体一样。后来想了一想,与其去死,干脆就剪短算了。很凉快唷!现在这个样子。”她说道。跟着便动手去抚弄长约四、五公分的头发。又冲着我直笑。
“很好哇!”我边吃香菇肉卷边说道。“侧面让我看看!”
她别过脸,停了五秒钟。
“唔,很适合你嘛!你的头型一定不错。露出耳朵也挺好看的。”我说。
“是呀!我也觉得。剪短了,不是也挺不错的吗?可是呀!男人却都不这么想。他们都说像小学生啦、像收容所的。哎!男人为什么都喜欢留长发的女孩子呀?简直是法西斯嘛!真无聊!为什么他们总是觉得长发的女孩看起来有气质、又温柔、像个女人啊?我呀!就认识了两百五十个长头发又没水准的。真的唷!”
“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说。这并不是假话。我记得她留长头发时,看起来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漂亮女孩。但我眼前的她却像是迎接春天到来的初生之犊一样,从体内洋溢出一股鲜活的生命力。那对眸子仿佛是个独立的个体似的滴溜溜地转来转去,时而笑,时而怒,时而悲伤,时而灰黯。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不曾见过如此生动的表情了,我忘神地凝视着她的脸。
“你真的这么觉得?”
边吃沙拉,我边点头。
她又戴上黑色的太阳眼镜,从镜片后面盯着我。
“喂!你该不会撒谎吧?”
“可能的话,我尽量想做个老实人。”我说。
“哦!”她说。
“你为什么戴那么黑的眼镜?”我问道。
“头发突然剪短了,觉得没有安全感呀!好像一丝不挂地被赶到人群当中一样,根本没法安心,所以才戴太阳眼镜的。”
“原来如此。”我说。然后将剩下的肉卷吃下去。她兴味十足地看着我吃。
“你不回去坐不要紧吗?”我指着她那三个朋友说道。
“不要紧呀!等菜来了我再回去。没什么事嘛!倒是我在这儿会不会打扰你吃饭啊?”
“怎么会?我已经吃完啦!”我说。见她没什么回自己座位的意思。我便又点了咖啡。老板娘把盘子收走,跟着递上砂糖和奶精。
“喂!今天上课点名的时候,你怎么没回答呀?你不是叫渡边吗?渡边彻!”
“是呀!”
“那为什么不回答?”
“今天不大想回答。”
她又把太阳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用一种窥探关着稀有动物的笼子似的眼神直盯着我。“‘今天不大想回答。’”她重复了一次。“喂!你讲话的方式蛮像亨佛莱鲍嘉的嘛!有点冷峻。”
“怎么会?我很普通呀!像我这种人到处都有。”
老板娘端来咖啡,放在我面前。不加糖、不加奶精,我轻轻地啜了一口。
“我说嘛!果然是不加糖和奶精的人。”
“我只是不喜欢甜的东西而已。”我耐心地解释。“你是不是误解了些什么?”
“怎么晒这么黑?”
“我徒步旅行了两个礼拜!到处走,只带了背包和睡袋。所以才晒黑的。”
“走到哪儿去了?”
“从金泽开始,绕了能登半岛一周,然后走到新。”
“一个人?”
“是呀!”我说。“到处都会碰上旅伴嘛!”
“有没有什么罗曼史呀?在旅途上和女孩邂逅什么的。”
“罗曼史?”我惊道。“喂!你果然是误解了。带着睡袋、满脸胡须、随处乱逛的人要到哪儿去搞什么罗曼史呀?”
“你总是像这样一个人旅行吗?”
“是啊!”
“你喜欢孤独吗?”她托着腮说道。“喜欢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上课的时候一个人坐得远远的?”
“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想勉强交朋友。要真那么做的话,恐怕只会失望而已。”我说。“‘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愿失望。’”一边衔着镜架,她一边喃喃说道。“你将来如果写自传,这种台词就可以派得上用场了。”
“谢谢!”我说道。
“你喜欢绿色吗?”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现在穿着一件绿色的运动衫呀!所以找才问你喜不喜欢绿色的嘛!”
“谈不上特别喜欢。什么颜色都好。”
“‘谈不上特别喜欢。什么颜色都好。’”她又重复了一次。“我好喜欢你讲话的方式。好像在替墙壁涂上很漂亮的漆一样。从前有没有人这么说过你?”
我说没有。
“我叫绿子。不过我和绿色可是一点也不配呢!很诡异吧?你不觉得很糟吗?像是一生都被诅咒了似的。我姐姐叫阿桃,好笑吧?”
“那你姐姐适合粉红色吗?”
“非常适合。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要穿粉红色的衣服一样。哎!真是不公平!”
她点的菜已经送来了,穿着花格子衬衫的男孩叫道:“喂!绿子!吃饭罗!”
她对着那边举起手来表示知道了。
“喂!渡边!你上课做不做笔记呀?戏剧史第二部那堂课的。”
“做啊!”我说。
“对不起!能不能借我呀?我有两堂没上。而且班上的人我又不认识。”
“当然好。”我从书包里拿出笔记,确定上面没写别的东西之后,才交给绿子。
“谢谢!渡边,你后天会不会来学校?”
“会呀!”
“那你十二点的时候到这儿来好吗?我还你笔记,顺便请你吃饭。该不会和别人一块儿吃饭就消化不良吧?”
“怎么会?”我说。“不过这没什么好谢的。只是借个笔记而已。”
“没关系啦!我喜欢说谢嘛!不要紧吗?没有记在本子上不会忘掉吗?”
“不会的。后天十二点在这儿碰面。”
那边又叫着:“喂!绿子!不快点来吃会冷掉唷!”
“喂!你从以前讲话就是这种方式吗?”绿子对那声音置若罔闻。
“我想是吧!没特别去注意。”我答道。这还真是第一次有人说我讲话的方式与众不同。
沉思了一会,她笑着站起来,回自己的座位去。后来当我经过他们那张桌子时,绿子向我招了招手,其余三个人只稍稍看了我一眼。
二、阳台看火--你要什么样的爱情??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地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观看,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80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音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处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烟味儿。
"是阪本那里。"绿子从栏杆探出身子说,"阪本搬来之前是一家开室内建材店的,现在早已关门不做买卖了。"
我也从栏杆上探出上身朝那边张望。不巧正位于一座三层楼的背后,详细情形看不清,好像有三四辆消防车在进行灭火作业。由于路本来就窄,至多能开进两辆,其他车只好在大街那边伺机而动。路面自然给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我看最好把贵重的物品收抬收拾,这里也得避一下难。"我对绿子说,"现在风向相反,但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而且加油站就在跟前。收东西吧,我来帮忙!"
"根本就没有贵重东酉。"绿子说。"可总该有什么吧?存款原始印章证书……首先钱没有了就是麻烦事。"
"不要紧,我不跑的。"
"这里烧着也……?"
"嗯。"绿子说,"死了就死了呗!"
我看着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着我的眼睛。她一下子把我弄晕了:不知她话里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我注视了她一会儿,渐渐地,开始觉得反正都无所谓。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
"和我一块儿死?"绿子眼睛一亮。
"难说。一旦势头不妙我可得逃走。 要死你一个人死好了!"
"冷酷。"
"只讨你一顿午饭,怎么能连命都一块搭进去呢,晚饭也招待的话倒另当别论。"
"你这人!算啦算啦。反正先在这儿看一会吧。我来唱歌给你听。"
"唱歌?"
绿子跑去下面,拿上来两张坐垫、四瓶啤酒和吉他。于是两人眼望团团涌起的黑烟喝起啤酒来。我问绿子如此做法是否会招致左邻右舍的白眼。因为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算不得正当行为。
"没事儿,管它!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
她唱起以往流行过的民歌。歌也好吉他也好实在不敢恭维,但本人却是满脸自我陶醉的神情。她唱了《柠檬树》、《粉扑》、《五百英里》、《花落何处》、《快划哟米歇尔》,一首接一首唱下去。起始,绿子教了我低音部分,准备两人合唱,可惜我的嗓音实在南腔北调,只好忍痛作罢,由她一个人尽情尽兴地引吭高歌。我口呷啤酒,耳闻歌乐,眼观火势,而且专心致志。眼见浓烟骤然腾空,旋即不大不小,周而复始。人们或狂喊乱叫或发号施令。报社的直升飞机自天外飞来,震天价地吼个不止。取完镜头便掉头就跑,但愿别连我俩的行径也拍进去。警察的大音量扩音机对着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大吼大叫,命令他们再往后退。小孩没好声地哭爹叫娘,玻璃"劈啪"乱响。俄而,风头开始倒转,白灰状物朝我们四周翩然飞来。然而绿子兀自吱吱有声地喝着啤酒,自鸣得意地大唱其歌。会唱的一股脑儿全部唱罢,又唱起了自己填词作曲的莫名其妙的歌。
本想给你做领菜,
可惜我没有锅。
本想给你织围巾,
可惜我没有线。
本想给你写首诗,
可惜我没有笔。
绿子说这歌叫"什么也没有"。歌词不伦不类,曲调也怪里怪气。
我一面听她唱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歌,一面放心不下:万一火烧到加油站,这座房子岂不跟着上西天了!绿子这时唱得累了,放下吉他,像晒太阳的懒猫似的歪靠在我肩上。
"我创作的这首歌如何?"她问。
"别开生面,富有独创性。很能体现你的性格。"我慎之又慎地回答。
"谢谢你。"她说,"题目叫--什么也没有。"
"似乎可以理解。"我点头道。
"咦,在我妈妈死的时候……"绿子脸朝着我说。
"噢"
"我半点都没伤心。"
"啊?"
"父亲不在以后也一点都没难过。"
"当真?"
"当真。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你不认为我冷酷无情?"
"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缘由吧。"
"是啊,嗯,是有很多。"绿子说,"复杂着呢,我家。不过,我一直这样想:不管怎么说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要是死了或分开了,该悲伤才是。可就是不行,完全无动于衷。既不悲伤,又不寂寞,也不难受,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我妈,她从黑暗里瞪着我,挖苦说'你这家伙,我死了你高兴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兴,死的到底是母亲。只不过是说没那么悲伤。老实说,我一滴泪珠也没掉。小时候养的猫死了还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怎么冒这么多的烟呢?我捉摸不透。既不见火,看情形火势又没加大。只管绵绵不断地冒着浓烟。到底是什么东西烧这么久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和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感到伤心点……"
"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
她歪起脖子看我的脸,随即深深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拼着劲儿地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手脚大,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来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了不起!"我肃然起敬,"可有成果?"
"难呐!"绿子说。然后眼望着烟思考了一会,说:"也许等得过久了。我追求的是十二分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才这么难。"
"完美无缺的爱?"
"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容许我任性,百分之百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想吃酥饼,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绿子,这就是酥饼。'可我却说:'我又懒得吃这玩艺儿了!'说着'呼'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这和爱似乎不大相干啊!"我不无愕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绿子说,"对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把酥饼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酥饼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顶、麻木不仁。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再去一次给你买点别的什么。什么好?巧克力饼,还是奶酪饼?'"
"然后怎么样呢?" "那我就好好地爱他,来报答他。"
"我是觉得相当不近情理。"
"可对于我,那就是爱呀!倒是没有人能理解……"说着,绿子在我肩头微微摇了摇头,"对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一提的,或者说非常无聊的小事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
"有你这样想法的女孩儿我还是第一个见到。"我说。
"其实这样的人相当不少。"她一边摆弄指甲的底端一边说,"起码我是认认真真这样想的,也只能这样想,不过把它照实说出口罢了。我从不认为我的想法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也不去追求那种两样。坦率地说,我觉得她们统统是在自欺欺人或逢场作戏。因此有时候对什么都讨厌得要死。"
"想在火灾里死掉?"
"瞧你,那倒不是。单单是好奇心而已。"
"指在火灾里送死?"
"其实也不是,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绿子说,"但死本身却丝毫也不可怕,确确实实。不过被裹在烟里呛昏,直接昏死罢了。转眼之间的事,同我见过的我妈和其他亲戚的死法相比,一点不怕人。咳,我家亲戚都是大病一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死的。我总觉得怕是血统关系。要费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咽那口气,挨到最后连是死是活都闹不清了,意识到的只是痛苦。"绿子把万宝路叼在嘴上,"我所害怕的,是这种方式的死。就是说,死的阴影一步一步地侵人生命领地,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样子,连周围人都觉得我与其说是生者,倒不如说更是死者。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绝对忍受不了的。"
过了30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店街。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旋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顶头俯视地面上的光景。
火灾过去后,绿子显得有些疲惫不堪。身体有气无力,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的天空,几乎不再开口。
"累了?"我问。 "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体了,呼地一下子。"
我看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投影在脸颊上,看上去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然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观看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煦、亲密起来,而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接吻那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儿?"
"有的。"
"那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随即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的瞬间魔力已经杳然遁去了。
5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大天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三、相拥入睡--“喂,喂喂,说点什么呀”
我们轮流洗过澡,换上睡衣。我借他父亲没穿几次而差不多崭新的睡衣穿上,有点小,但总比没有强。绿子在摆着灵位的房间里摊开客用卧具。
“在灵位前不害怕?”绿子问。
“怕什么,又不干什么坏事。”我笑道。
“可以在旁边抱我,一直到我睡着?”
“可以。”
于是我倒在绿子那张小床边上,久久抱着她,好几次都险些跌下床去。绿子把鼻子贴着我的胸口,手搭在我腰部。我右手搂着她的背,左手抓住床沿,以免身体跌落。这种环境,实在难以激起亢奋。鼻子底下就是绿子的发,那剪得短短的秀发不时弄得我鼻端痒痒的。
“喂,喂喂,说点什么呀!”绿子把脸埋在我胸前说。
“说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我听着心里舒坦。”
“可爱极了!”
“绿子,”她说,“要加上名字。”
“可爱极了,绿子。”我补充道。
“极了是怎么个程度?”
“山崩海枯那样可爱。”
绿子扬脸看看我:“你用词倒还不同凡响。”
“给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暖融融的。”我笑道。
“来句更棒的。”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绿子紧紧贴住我的胸口,“好上天了!”绿子说,“既然这么喜欢我,我说什么你都肯听?不生气?”
“当然。”
“那么,你能永远不嫌弃我?”
“那还用说。”说着,我抚摸她像小男孩那般又短又软的头发。“不要紧,放心,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可我就是怕。”绿子说。
我温柔地搂住她的肩。不一会儿,她肩头开始规则地上下抖动,响起睡熟的声音。
四、绿子的信 --莫名让我想起初中一个女孩的纸条,不过却没有绿子这般美好了
“喂,怎么搞的,渡边君?”绿子说,“怎么瘦得这么厉害?”
“是吗?”
“干过火了吧,和那个有夫之妇?”
我笑着摇摇头:“去年10月初到现在,一次都没和女人睡过觉。”
绿子吹了声嘶哑的口哨:“半年都没干那个?当真?”
“真的。”
“那——为什么这么瘦?”
“成大人了嘛。”我说。
绿子扳住我的双肩,定定逼视我的眼睛。随即皱了会眉头,接着莞尔笑道:“不错,确实有点变化,同以前相比。”
“成大人了嘛。”
“你这人可真行!居然会这样想。”她不无感叹地说道,“吃饭去,肚子瘪了吧?”
我们去文学院后面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点了当天搭配好的便餐,她也没有异议。
“嗳渡边君,还生气?”绿子问。
“生什么气?”
“就是对我报复你不给你回信的事。那样不好吧,你认为?本来你都正式道歉了。”
“怪我不是,有什么办法。”
“姐姐劝我别那么做,说我太斤斤计较,太耍小孩子脾气。”
“不过这回心里总算痛快了吧,报复完后?”
“嗯。”
“那不就行了。”
“你真够宽宏大量的。”绿子说,“渡边君,你真的半年都没干那个?”
“没有。”我回答。
“那么,上次你陪我睡觉时是很想很想干的吧?”
“咦,大概是吧。”
“可干吗没干?”
“你现在是我最宝贵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你。”我说。
“当时你要是死乞白赖,我恐怕很难拒绝的,那时候简直都瘫痪了。”
她浅浅地一笑,手温柔地放在我手腕上:“我,那之前就已决定相信你,百分之百地。所以即使那时候我都能放心大胆地只管睡。心想和你在一起不要紧,用不着担心。睡得很香吧,我?”
“嗯,的确。”
“假如你不是那样,而是对我说:‘喂绿子,和我干吧,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和我干!’我说不定就真的干了。不过,你可别因为我这么说就认为我勾引你,挑逗你,我只是想把我感觉到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知道。”我说。
我俩边吃饭,边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发现有两门课选的相同,就是说每周可以同她见面两次。接下去,她谈了自己的生活。说她姐姐好长时间都过不惯公寓生活,因为同她们以往的人生相比着实可谓养尊处优,而她们早已习惯同时护理病人和给店里帮忙那种每天忙得团团转的生活。
“不过,近来她终于转过弯来了。”绿子说,“说我们自身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无须顾忌谁,尽情舒展手脚就是。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神不定,就像身体离开地面两三厘米似的。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如此快活的人生,而肯定马上就会掉到苦海里去,弄得两人紧张得很。”
“好一对苦命姐妹。”我笑道。
“过去太残酷了。”绿子说,“也罢,往后我们狠狠地补捞回来。”
“哦,你俩怕是做得到的。”我说,“你姐姐每天做什么?”
“她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表参道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每周去帮三次忙。其余时间就学做菜,或同未婚夫幽会,再不就看电影、发呆,总之在享受人生乐趣。”
她打听了我的新生活。我讲了房间的配置,宽阔的庭园,叫“海鸥”的猫,以及房东等等。
“有意思?”
“不坏。”我说。
“可就是没精神。”
“可惜大好春光。”
“可惜还穿着她给织的漂亮毛衣。”
我吃了一惊,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紫色毛衣:“你怎么会知道?”
“你这人真算老实。那肯定是挖苦你的嘛!”绿子意外地说道,“干吗没精神?”
“我倒想拿出精神来。”
“你把人生当做饼干罐就可以了。”
我摇了几下头,看着绿子的脸说:“可能是我脑筋迟钝的关系,有时捉摸不透你说的什么。”
“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大喜欢的不都在里面吗?如果先一个劲儿地挑你喜欢的吃,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这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过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倒也是一种哲理。”
“不过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从切身体会里学得的。”绿子说。
正喝咖啡时,闯进两个绿子同学模样的少女,和绿子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随即东拉西扯起来,什么去年德语成绩如何,什么在学潮冲突中你受伤了,什么这双鞋不错在哪里买的。在似听非听的时间里,我竟觉得那些话仿佛是从地球背面传来的。我边喝咖啡边观望窗外景致。校园春景一如往年:天空迷蒙,樱花开放,一眼即可看出是新生的男男女女抱着新书在路上走动。如此观望之间,神思又有点恍惚起来。我想起今年仍不能返回大学的直子。转眼看见窗台放着一个小玻璃杯,插有一枚白莲花。
两人道声“回头见”返回自己座位后,我和绿子走出店,在街上相伴散步。我们转了家旧书店,买了几本书,又进饮食店喝了杯咖啡,然后去娱乐中心玩了一会弹球游戏,接着坐在公园长凳上说话。差不多都是绿子一人唱独角戏,我哼哈作答。绿子说口渴,我去附近糕点铺买来两支可乐。那时间里她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刷刷”写着什么。我问写什么,她答说没写什么。
3点半时,她说得赶紧回去,讲好和姐姐在银座会面。我们步行到地铁站,在那里分手。分手时她把那张稿纸一叠四折塞进我外套口袋,叫我到家后再看。而我是在电车中看的。
恕我免去客套。
这封信是在你去买可乐的时候写的。给凳子邻座的人写信,在我还是初次。但不这样做,似乎很难把我想说的传达给你。因为无论我说什么你几乎都听不进去,是吧?
嗯,你可知道?今天你做了一件十分使我伤心的事:你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发型的变化吧?我辛辛苦苦地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好不容易在上周末把发型变得像个女孩儿模样,可你连这点都未察觉吧?我自以为十分可爱,加之久未见面,本想吓你一跳,然而你根本无动于衷,这岂不太跟人过不去?反正你现在恐怕连我穿什么衣服都记不起来了。我也是个女孩儿!你就是再有心事要想,也该多少正眼看我一下才是。只消说上一句“好可爱的发型”,往下无论你做什么,哪怕再心事重重,我都会原谅你。
所以,我现在向你说谎,什么要同姐姐在银座会面,全是谎话。本来我打算今天住在你那里,睡衣都带在身上。是的,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哈哈哈,傻瓜似的。但你偏偏不肯邀我去你住处。不过也好,既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似乎乐得一人孤独,那么就让你孤独去,去绞尽脑汁想各种事情,想个彻底!
不过这也并非说我对你有多么恼火。我仅仅是感到寂寞。因为你对我没少热情关照,而我却一次也没为你效力。你总是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却一个劲儿“咚咚”敲门,一个劲儿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即刻恢复原状。
现在你手拿可乐回来了,一副边走边沉思的样子,我恨不得你跌一跤才解气,可你并未跌跤。你正坐在旁边,“咕嘟咕嘟”喝可乐。买可乐回来时,我还期待你注意到我的发型,说上一句“嗬发型变了嘛”,结果还是落空了。假如你注意到,我会把这封信撕得粉碎,说:“喂,去你那里好了,给你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饭,然后和和气气地一起睡觉。”但你俨然一块铁板似的麻木不仁。再见。
附记: 下次在教室见面不要打招呼。
五-雨中之吻--“没办法,就是相中了你”
我每天去学校,每周在意大利饭店做两三次工,同伊东谈论书和音乐,从他手里借来几本巴雷斯看,写信,同“海鸥”玩,做细面条,侍弄庭园,边想直子边取乐,一场接一场看电影。
绿子向我搭话是6月快过完一半的时候。两人足有两个月没开口了。上完课,绿子来我邻座坐下,手拄下巴,半天没有吭声。窗外雨下个不停。这是梅雨时节特有的雨,没有一丝风,雨帘垂直落下,一切都被淋得湿漉漉的。其他同学全部离开教室后,绿子也还是以那副姿势默然不动。一会儿,从棉布上衣袋里掏出万宝路衔在嘴上,把火柴递给我。我擦燃一根给她点上。绿子圆圆地噘起嘴唇,把烟缓缓地喷在我脸上。
“喜欢我的发型?”
“好得不得了。”
“如何好法?”
“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
“真那样想?”
“真那样想。”
她注视着我的脸,良久,把右手伸出。我握住它。看上去她比我还要如释重负。绿子把烟灰抖落在地板上,倏地起身立起。
“吃饭去吧,肚子贴在一起了。”绿子说。
“去哪儿?”
“日本桥高岛屋商店的食堂。”
“干吗故意去那种地方?”
“隔些日子我就想去一次那里。”
于是我们乘地铁来到日本桥。也许从早上就开始下雨的关系,商店里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影。整个店内充溢着雨气味,店员也因无所事事显出无聊的神情。我们走到设在地下室的食堂。细细看了一遍陈列的样品,两人都决定吃盒饭。虽是午饭时间,但食堂里人并不挤。
“在商店的食堂吃饭,这可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我一边说一边端起几乎惟独商店食堂才能见到的光溜溜的白茶杯,喝了一口。
“我喜欢这样。”绿子说,“觉得好像做了一件特殊事情。这大概同小时的记忆有关,小时很少很少由大人领着逛商店。”
“我倒好像常逛,我妈喜欢逛商店的。”
“真好。”
“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