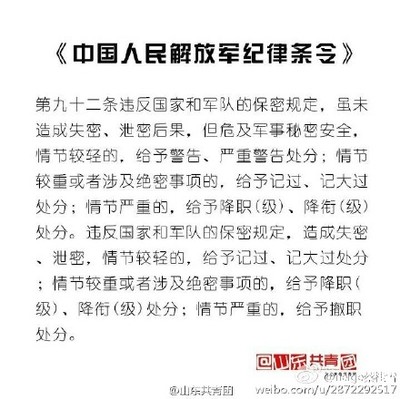咱们平平淡淡地过吧,我的明星妈妈
——李谷一女儿肖一讲述风光妈妈背后的辛酸
口述/肖一整理/侠子
李谷一,国家一级演员,曾以演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知音》、《乡恋》等歌而蜚声中外。1978年受到美国总统卡特的接见。其演唱风格和技巧,对我国民族声乐和通俗音乐和发展有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谁也不会料到,风光背后,她的丈夫和女儿却一把辛酸一把泪地忍受着聚少离多的痛苦,而她本人也有多少冤屈和泪水窝在心里。应本刊之约,本文作者在北京中旅大厦采访了李谷一的女儿肖一,揭出了这其中无人知晓的一幕……
童年,我的寄养生活
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妈妈事业的颠峰,她正以《知音》《乡恋》等歌走红,忙得连回家都顾不上。爸爸是将军肖劲光的儿子,在部队工作,每周能回家的机会不多。
那时,我和父母住在中央乐团的筒子楼宿舍里,房子很小,也就十来平米,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炒菜都要在楼道里。因为父母工作忙,家里没有人带我,3岁时,我就被寄养到中央乐团一个退休的老爷爷家。老爷爷和老奶奶差不多都有六七十岁,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孙子和孙女,所以对我也谈不上什么特别的照顾。
妈妈每年都有六七个月在外地演出,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也是在团里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想见妈妈一面难,有时非常想妈妈,想得都想疯了。我常在下午或傍晚的时候踩在老爷爷家的大床上,双手扶着窗台,翘着脚尖向窗外张望,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早点出现,早点来接我啊。但是妈妈能来接我的时候很少,我只有一个人呆呆地盼,呆呆地想。我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的家,所以平时也很少说话。
后来,我被寄放到了奶奶家里,奶奶身体也不好,就请了一个远房亲戚过来照顾我们一老一小。
有一次我发烧,引起了心肌炎,妈妈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发烧,也没太在意,就去外地演出了。躺了两天后,我就开始浑身冰凉,昏迷不醒。奶奶一看我的样子吓傻了,赶紧找人把我送到海军总医院。但海军总医院的医生看了我的症状后很抱歉地对爸爸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情况很危险,赶紧转院。
妈妈在得知我病重的消息后,结束当天在外地的演出冒雨匆匆赶回了北京,回来时已是深夜。那时北京还没有那么多出租车,特别是到了夜里,爸爸通过关系打了不下几十个电话,一次次地恳求,一次次地和人家说好话,才问到了几个儿童医院专家的住址。等妈妈赶到医院时,爸爸已经不知从哪儿借了一辆小三轮车,拉着妈妈在细雨飘飞的夜里一家家也地去敲那些医生家的门。
当时我昏迷着,不知道这些,后来听说妈妈就是这样在深秋的雨夜里,一路流着内疚而悔恨的泪水和爸爸为我到处奔走。
后来遇到一个位医生,半夜里怎么也不肯去其他医院看病,后来听说是李谷一求他看病,立即起来迎接,忙乱中把衣服扣子都扣错了。爸爸妈妈非常感激,四处找车,将这个掌握着我生命大权的医生接来治病。
在医生的嘱咐下,他们又在雨夜里为我联系医院,办转院手续。那一场病让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每天都打针、输液,身体的痛苦难以用语言详述,每打完一次针,我的枕头都是湿的,那些疼痛和眼泪陪伴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当时我的两只小手的手背被扎的全是针孔,后来实在没地方扎了护士就扎我的脑门,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筛子一样,到处都是眼,是洞。
那时,父母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着我,可他们都还有工作,妈妈每次来看我的时候,都极尽温柔与怜爱,抚摸我,亲吻我,但过不了多大一会,她接到新的演出任务就会再一次抛下我而离去。
最难过的是那些小病友的父母来看他们时,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小床上干巴巴的看着。那种孤独和被冷落的感觉就像自己真的被遗弃了一样,我羡慕他们,甚至有时想如果自己的妈妈不是个著名的歌唱家多好,我也能和他们一样常会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上幼儿园以后,父母常顾不上接送我,我就带着堂弟一起去上学。可能是平时在父母面前一直都扮乖乖女的原因吧,他们不在身边时我就想撒野,想淘气,也许是心里太压抑了,一次为了抄近路我带着堂弟准备从幼儿园的铁栅栏墙翻过去,结果没翻好,一下子头朝下摔下来了。
我昏迷不醒。是堂弟跑回家告诉奶奶,奶奶又打电话把去上班还在路上的爸爸给叫了回来。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胳膊疼得像断了一样,等爸爸送我到医院后,才知道骨头已经断了。医生给我拍了X光,把骨头接上十几天后,仍然疼得不得了,复查时,才知道骨头接错了位,只能生生的掰断重新接。当时在X光室里那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用爸爸的一句话说就是鬼哭狼嚎。
最难过的还有妈妈,妈妈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当时拿着电话就傻了。爸爸说:“肖一的胳膊摔断了,现在已经接好了,没什么危险了,你不用担心。”爸爸的这个电话是在医院里打的,妈妈明白过来以后,哽咽着非要爸爸到我病房里打电话,妈妈急切地说:“我要找肖一,我要和肖一说话。”
握着电话,听着妈妈的声音,我委屈而思念的泪水潸然而下,受了那么多的苦,有多少话要对妈妈说啊,可是我只说了一句:“妈妈,我想你——”然后就再也说不出话了,我们母女俩在电话里都已泣不成声,那一刻,眼泪成了我们母女最好的语言。
我爱妈妈,也恨妈妈。恨妈妈没有太多的时间陪我,让我有时像个野孩子一样。一次,爸爸妈妈忙,把我送到一个朋友家好几天。当他们去看我时,我特别生气,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亲生的,他们为什么老是把我“送来送去”的。爸爸妈妈可能是特别想我,一见面就把我抱到怀里亲吻我,我强忍着委屈的泪水,却怎么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我狠狠地朝着爸爸正吻我的嘴唇就咬了一口,当时爸爸疼得一下子叫出了声,我松开嘴后,发现爸爸的唇已流下血来。那一刻,我压抑已久的委屈与泪水又一次暴发出来。其实我不是不爱爸爸妈妈,我这是在向他们抗议,我多希望他们能多一些时间和我在一起啊!
从那时起,我开始叫妈妈为李老师。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就是李老师,整天带学生,教人唱歌,有时喊她“妈妈”喊好几声她都没听见,但一喊“李老师”她马上就答应了。爸爸说妈妈是个合格的“李老师”,但不是合格的“妈妈”。所以很多时候为了能引起妈妈的关注,我就和她的学生争风吃醋,叫她李老师。
我上学以后,因为学校的老师都知道我是李谷一的女儿,每次有活动和演出时,都让我上台独唱几首歌。当然老师也是为我好,觉得我是歌唱家的女儿,怎么也有些遗传基因,再怎么唱也应该不错,可我就是对唱歌有一种抵触情绪,特别是他们这种人为的安排。我心里老大的不舒服,为什么歌唱家的女儿就得上台唱歌,那时我真希望妈妈就是一个平民百姓,那样我就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可以享受同等“待遇”了。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或有其他文艺活动的时候,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刻。我对唱歌没有兴趣,老师见我面无表情,音色也不是很准,特别是那种应付的态度,让老师很为难,一次次私下里找我谈话,我对老师说,我不喜欢唱歌,而且歌唱得也不好,为什么因为我是歌唱家的女儿就也得上台唱歌?
老师工作做得紧了,我只得回家和妈妈临时学一首歌,妈妈常让我单独唱一首给她听,可我当时除了《国歌》外,几乎唱不下一首完整的歌,妈妈教了我好几首,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小路》《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都是大家非常熟悉且会哼唱的,可我就不会。妈妈说在音乐方面我可能真的没有培养价值,主要是我没有兴趣。后来老师见我如此勉强,就建议我去唱合唱。虽然老师还是好心地把我安排在最前排最中间的位置,但是我在合唱开始时,连嘴都不想张。老师拿我没办法,又一次次给我做工作,最后见我并不热情,也就不怎么勉强和为难我了,有时干脆就让我在最后一排滥竽充数。
(后面还有两节,一共六千多字,故事很精彩,可惜新浪不让一次发完。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