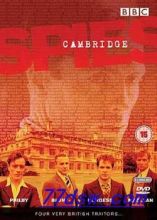(电影《我11》剧照-来自网络)
有博友看了我写的博文《三线厂的露天电影》,建议我看看最近上映的、王小帅导演的新片《我十一》,于是就上网下载来看了,象电影《青红》一样,故事依旧简单,反映那个特殊年代里小人物的挣扎和无奈,人性和自由在极权政治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但影片在政治上又不能涉猎太多,王小帅就将那个时代西南三线工厂的许多场景堆砌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一定陌生不知所云,但我却看到许多记忆中熟悉的场景,对我这样的同龄人来说,这就算是一部怀旧片吧。因为在电影所叙述的1975年,我也是生活在同样的三线工厂里,且那一年我也十一岁。
关于“捅炉子”
电影开始有一个场景,小主人公王憨在家里奋力地捅炉子。这个活儿,也是我那时每天必做的功课。中午放学回到家中,先把下面的炉门打开,再站在小凳上(因个子还不够高)用钢条磨制的炉钎捅碎封在炉火上面的煤饼,让炉火能得到充分的氧气,慢慢地燃烧变旺。因为中午的时间短暂,若大人们下班回家后再打开封火,需要等到炉火慢慢变旺后才可以做饭,会耽搁不少时间。于是捅炉子的任务往往就交给了家里的孩子们,因孩子们通常放学时间比大人下班早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那时烧的煤是有烟煤,捅炉子时难免煤灰和浓烟飞扬,搞到灰头土脸。
家家门口用砖砌个煤池,用来储放煤粉,但直接烧煤粉浪费不耐烧,还要掺和一定比例的黄土,于是隔几天就要拿上铲和筐,去家属楼后面的山坡上取些黄土回来。有一次借来邻居家的一副担子,想一次多取些土,没想稚嫩的肩膀第一次挑担,担子硌得肩膀生疼,回来一路摇摇晃晃、瓷牙咧嘴。当每次要给炉子添煤或封火时,要先用水将煤粉和黄土调和均匀,加水加土要适合,否则烧起来烟很大。耐烧是做到了,可这样的炉火用来炖煮东西还凑合,想爆炒却是不可能的。大概直到1978年以后,大家才逐渐用上蜂窝煤,终于告别了捅炉子的时代。
也在1975这一年,我领教了煤气中毒的厉害。那时一家四口住一大一小两间,大间靠外隔出个厨房,父母带妹妹住里间,在兼作客厅和餐厅的大间摆张单人床我睡。那天晚上父亲出差不在家,天快亮的时候迷迷糊糊中被母亲叫醒,母亲在里间软弱无力地说,她和妹妹煤气中毒了起不来床,问我感觉怎样,我那时很清醒就说没有感觉到,母亲让我赶紧去隔壁邻居叫人,我起身出来敲开了邻居家的门,告诉他情况后往回走,到家门口时却眼前突然一黑栽倒在地,摔在地上时我马上又碰醒过来,很快爬起来,这时邻居也过来一起打开家里所有的门窗,我对邻居说我没事,邻居就去卫生所喊医生来。医生来了给母亲和妹妹打上了吊瓶,我对他们说感觉没事,后来我居然还自己去上学了,只是自己感觉头痛了一天。事后父母亲分析可能是封火后烟道被煤渣堵住不通畅,厨房和大房间之间的门,睡觉前可能也没有关好,晚上煤气悄悄溜进了屋里。
关于“吃肉”
电影中,王憨的妈妈中午从供销社买回来一块肉,来改善家里的伙食。我们那时中午往往只能吃面条,因为这样节省时间,早上父母已经把面粉舀到盆里,我回到家捅完炉子去“换面条”,就是端着面粉去厂里的压面房换回同样重量的面条,再给上几分钱的加工费。吃肉往往要等到周末,买回来的猪肉要切下肥肉来炼猪油,炼油剩下的油渣还用来炒菜或拌面条。最好的伙食改善,算是星期天去周边的村庄赶集,买只活鸡回来,就像电影最后场景中,王憨饶有兴趣地看他爸爸宰杀鲜鱼,我则会兴致勃勃地看父亲杀鸡退毛剖膛切块的全过程,以致当我长大后亲手来做这一切的时候,感觉轻车熟路一般。
关于“做白衬衣”
电影中,王憨的妈妈亲手为他做了那件重要的新衣服-白衬衣。我们那时厂里,一度也流行家庭主妇们自己缝制衣服,家里买了缝纫机(也算是一个大件呢),母亲跟人学怎样裁剪和缝纫,后来给我做了件绿色小军装-那个时候男孩子们最流行的衣服。不过做衣服终究是门技术含量较高的手艺,母亲也没有在这上面再发展提高,以后每当过年的新衣服还多是买的,缝纫机也就主要用来缝缝补补、打个补丁什么的。至于白衬衣,我们那时只有在重要的节日或活动日,例如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才会穿出来,平时都舍不得穿的。
关于“捉迷藏”和“集烟盒”
电影中,王憨跟同学玩捉迷藏、弹弹子等游戏。这些游戏也都是我们那时常玩的,特别是吃过晚饭后,一大帮孩子聚集在楼下,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捉迷藏,一直疯玩到九、十点钟,被大人们多次喊叫,才恋恋不舍地散了回家。电影中还有一个场景,王憨翻看收集的香烟包装纸,镜头特写那张夹在书本中的红色中华香烟纸。我们那时,差不多每个男孩子都有过收集香烟包装纸的经历,能集到中华牌香烟纸差不多只是在梦中才能实现的事,因为在山沟里几乎没有人有资格或经济能力抽到这个牌子的香烟,有幸见到的几张估计多半是在大城市里集到的、然后通过某种途径流传到了山沟里。
关于“两道杠”
在影片中,王憨胳膊上戴着“两道杠”的少先队臂章。但在我的印象中,1975年的时候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戴红领巾不叫“少先队”而叫“红小兵”,也没有“两道杠”或“三道杠”这样的臂章,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恢复了“少年先锋队”的称号,也有了小队、中队、大队这样的少先队建制。我们工厂的子弟小学规模不大,一个班级算一个中队,里面有两到三个小队,整个学校是一个大队,那时我也算是学校的“红人”,做过中队长和大队长,有幸戴过“两道杠”和“三道杠”。
关于“红”“军”
影片中,那个被人玷污的女孩子叫“谢觉红”,王憨的玩伴中有一个叫“卫军”。我们那个年代,女孩名字中带有“红”字、男孩名字中含有“军”字的特别多,记得在工厂子弟小学里,仅我们年级约40-50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女孩名字有“红”、男孩名字有“军”。那个时代,红色是革命的颜色-红旗、红五星、红领章、红宝书、红五类、红卫兵、红小兵,总之有“红”就是革命的、进步的、正义的,沾“黑”就是反革命的、落后的、反动的,所以大人们都爱给自己的女儿起名“红”。那个时代,军人是最令人羡慕的一群,象现在的当权高官千方百计送子女出国留洋、进入金融经贸或政府公务员,那时的当权高官千方百计送子女去参军,军人崇高的地位也就造成了大人们爱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军”。
关于“上海话”
影片中,王憨父母和那个工厂里的人们大多说一口上海话,说明这个三线厂可能是从上海搬迁来的,或者是从上海工厂抽调人员来组建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有些三线工厂是从城市整体搬迁到山沟里的,也有些三线工厂是从各个大中城市里的工厂抽调人员到山沟里新组建的。我的父母就是从位于宝鸡市的军工厂抽调到山里的,所以厂里头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北京、天津、上海等这些大城市的人不少,我父亲就是北京人,母亲则是上海人。当那些来自于同一个城市的人们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彼此亲切地用家乡话聊天,所以我会常常听到不同地区的口音和方言。贵州那边的三线厂可能是上海人挺多,大学里同班同学中就有一个贵州三线厂来的,两年前一次在上海出差,居然在上海新天地巧遇了这位同学,虽然大学毕业时分配回了贵州,但终究全家人还是回到了上海。
关于“大澡堂”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在大澡堂里拍摄的。影片中的澡堂内地面墙壁已经贴上了白色瓷砖,但我记忆中那时厂里的澡堂还全都是灰色水泥面的。正如影片中所描述的,大人们泡在澡堂池子里议论厂里发生“杀人”的事,王憨则在一旁静静地偷听。那时的大澡堂的确是工厂里人们的社交场所,人们一边洗澡一边谈论聊天,内容自然是天南海北、包罗万象。我那时有点羞于泡澡,因为生来皮肤比较白,成为了一些大人和同学的讥笑对象,而我自己也感觉惭愧,似乎觉得肤色白得没有劳动人民本色,而羡慕那些皮肤黝黑的伙伴。
关于“父亲带儿子去画画”
影片中,王憨的父亲带他去野外画画写生,路上碰上了那个被人玷污的女孩谢觉红和她的父亲,然后遇上大雨他们一起跑回了谢觉红家里,谢觉红的父亲向王憨的父亲哭诉家里发生的灾难,王憨则懵懂地偷看谢觉红换衣服的背影。我的父亲也常常带我去野外,不是去画画,是去钓鱼、捉青蛙或去赶集。那时工厂周边尚未污染的小河中有很多的无鳞小鱼,每次钓上几十条回来,裹面油炸吃,非常难得的美味;捉青蛙不是用手,是在长竹竿头部绑上铁丝磨成的三齿刺,发现青蛙后悄悄地靠近,然后用竹竿猛然插住青蛙,虽然那时我从书本上知道青蛙是益虫,吃稻田里的害虫,但面对青蛙大腿的美味诱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到周边的村镇赶集则是去买猪肉、活鸡、鸡蛋、豆制品等,或买木材回来打家具,我们常去的村镇是保安镇和永丰镇,去保安镇要翻一个陡峭的山崖,小路在山崖上蜿蜒,厂里人都形象地称为“十八盘”。有一次我和父亲在十八盘的底下休息时,遇见了班上的女同学和她父亲也赶集回来,两个大人闲聊了一会儿,我跟女同学却什么话也没说,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里男女同学很“封建”,彼此不说话。不过那时谁也想不到的,十来年后这个女同学竟然跟我在北京成了夫妻,直到现在,老婆还“耿耿于怀”那时在山下我怎么不理她。
想不起这张照片是哪一年拍的了,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吧,与影片中王憨的年龄相仿,不过王憨已经懵懵懂懂有了点性意识,我那时则还是什么都不懂,估计连小孩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明白,惭愧啊。
这张照片大概是1978年拍的,老婆也十一岁,抱着她的小弟,在所住家属楼旁的马路边照的吧,一年以后她们一家人终于“逃离”了深山沟,离开了三线厂回到城市。注意看她身后路旁的小松树,栽种的时间不长,还不够高。
这是30年后我们带着儿子重访山沟里的三线厂,前面那张照片中那些路旁的松树,已经如此的高大茂盛,不过栽种它们的人们早已在1992年全部离开了这里,时代变迁、光阴如梭,怎不让人徒生出许多感慨。
这是我们家在1989年离开山沟前、最后居住过的房屋,这种带有独立阳台的楼房是八十年代中才盖的,而在七十年代那时候我们住的都是通走廊的楼房。就是这么好的楼房使用没有超过十年就废弃了,门窗、上下水管等所有能拆能卸的都早已被当地农民拆去换钱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