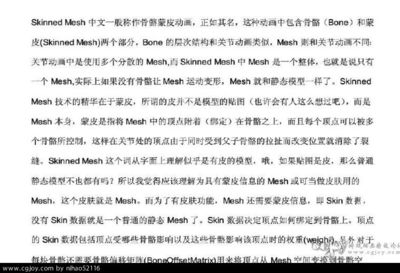风中的鸟巢
雪小禅
我真喜欢那些风中的鸟巢。
在冬天的荒野里,在肃杀杀的寒风里,我看到那些枯枝上的鸟巢,挂在树梢上,看着岌岌可危,无
限孤单,但又具有饱满的坚挺的力量。
它在风中,在一片枯黄的冬天的树梢上,独自承担风给它的力量。我喜欢那鸟巢的样子,圆圆的,
有毛刺,不规则,在茂盛的夏季和秋天,鸟儿们一点一点衔来树枝,然后和着唾液一根根地搭着——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工程!
那些风中的鸟巢,多么疏离,每隔几十米就会突兀地出现一个鸟巢,黑黑的,远远看去,很孤单。
可是,我喜欢那孤单。
那是应该有的孤独样子——它独立于时间之外,好像偌大的冬天只有它了。在空旷的冬天,我路
过那些鸟巢,路过那些孤单——好像我也是一只风中的鸟巢,游走在这冬天的寂寞里。
这鸟巢像印度女歌手Koaly的歌,足够寂寞,也足够打动人。我在听她的歌的时候,常常想起那些风
中的鸟巢。我在那些歌声中游走着,凉凉的,薄薄的,感受这风中的冷和凄然。但真的很好——那些
风游走在销骨的寂寞里,和那些鸟巢一样吧?我坐在车里,车里的空调开得很足。不,不冷。那些鸟巢
在寒风中偶尔抖动,但不会掉下来。它们高高在上,它们在冬天里,但又在冬天外。
这样的寂寞其实销骨。但又别有风情——似大雪天一个人行走在天地间。我把车里的空调开得很
大,热气扑到脸上,Koaly的声音很空灵,似一条小蛇游进我心里。她带着印度特有的神秘和巫气,带着
一些前世的味道,款款而来。声音是紫色的,略带忧郁,又一声声让人心醉。在关键的地方,一下能击
中你,动弹不得。可真好。
它和鸟巢相辅相成,都孤单得很饱满,恰如其分。
有一个人说,“无论睡在哪里,我都睡在夜里。”这句话让我想起风中的鸟巢。无论睡在哪里,它
们都睡在风里。
想想吧,睡在风里。像一个人的名字,是的,林风眠。他喜欢自己这个名字,他说,就是小鸟在风
中睡着了。他说的风,是春风。
但鸟巢是睡在冬天的风里,更有一种意境上的美感和孤清。有些孤芳自赏吗?有!有些文艺吗?当
然也有!可这是文艺不是装的,不是小情小调,是刻骨的!是带有腐蚀性的!它侵略了我的灵魂。
我在路上,在冬天的路上,伴我的有这些风中的鸟巢,还有那永定河边的一排排枯树,桑树,柳树
,槐……都有古意。旧得让人可以发呆,黑黑的树皮皲裂着,我试图走近那些树,那些风中的鸟巢,可
我知道,走近了,一定没有了现在的荒凉味道。
它们就应该在时间之外,在冬天之外。
我只喜欢那些冬天的鸟巢。它们和春天夏天秋天的鸟巢不一样,春天的鸟巢还单薄,夏天的太狂躁
了,秋天稍显俗气的热闹,只有冬天的鸟巢,显得这样的饱满又这样诱人。那种诱人,是鸦片似的诱,
越孤单,越寂寞,越寂寞,越诱惑。
整个冬天,我时常路过那些风中的鸟巢。我习惯了它们的姿势——有些过分的清高和薄凉,稍微
有些弱势,可是,恰到好处。它似一个寂寞的男子,人到中年,无人能知,无人能懂,人前是欢笑的,
颓败时,就做了这样一只独立于世的鸟巢。
如果你没有绝世的容貌,那么,你有绝世的姿态也是好的。这样想的时候,我打开一包雪茄烟,我
不是抽烟的女子,但喜欢这孤独傲世的雪茄烟,它和冬天的鸟巢如此相配。我点燃一支雪茄,试图加速
这孤单的速度。在这冬天,在这空旷的田野里,其实,我是试图做一只冬天的鸟巢。
我身边剩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是我,刻意减去那些不必要——我才知道生活中不必要原来这样
多!它们占据着我太多私人空间,霸占着我的精神硬盘,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只想做这样一只风中的鸟
巢。
不沟通,不奉迎。冬天的旷野里减去了很多东西,就剩下这一个小小的鸟巢。把自己放在里面,独
自、很独自地发呆——我忽然很羡慕那些风中的鸟巢,它任凭世间如何繁华,一个人在那冬天的树梢
上高高地挂着,寂寞都寂寞得这样风华绝代!
铁线蕨
我一向对不开花的植物抱有持续的好感。
何况,铁线蕨的名字实在是好。
像一个稳妥的中年男子,一直稳妥着,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线,而且,干净雅致——蕨类植物,
历来有着难得的干净与简洁,并且带着深深的古意。
没有织锦繁华,没有裂帛之痛,只是这干净与简单,不开花,只绵延跌宕着这绿意,很流畅地铺排
开。做植物,干净和简洁是难的,大多数全是繁花似锦,努力表现的样子,而蕨类植物的铁线蕨,有着
异样的温暖和朴素。
初见是在我的院子里。
春天里,在阳光下散步,看到墙角布满了这种小叶子的植物,很听话又安静地呆在角落里。
再见是在贵州的原始森林里,青苔上爬得到处都是,非常浓郁。
带着湿绿和苍茫的味道,我喜欢那种绿——一下子可以把人的心都染绿了,湿润着,却不芬芳。
只是湿润,带着凉凉的温度,可是,我愿意告诉它——这是最踏实的湿意呀。如果一个中年男子温文
尔雅深情款款,如何能不吸引你?单是他的眼神,就足够让你觉得安定、稳妥,心神荡漾,倒是其次的
事情了。
铁线蕨,实在有一种飘逸的静寂之美。
读清少纳言的文章时,常常会想起这样的植物,而清少纳言,也配得起这样的静寂之美:
“淡紫色的衣,外面罩了白衫的人,刨冰放进甘葛,盛在新的金碗里,藤花梅花上落雪积满了……
”真美呀,每每于午后,一杯午后红茶放在阳台的小几上,就有这种蕨类植物的美感,好像自己也成了
一株植物似的,那样接近了空灵与美丽……
幽寂,玄妙。我实在喜欢这样的光阴,于是也养了一盆铁线蕨,长势并不好。我养什么东西都不易
活,而尤其不喜花,极少种花。我性格中偏阴偏冷,易与不开花的植物相缠相伴,似是它们的知音,用
沉默表达高贵——沉默是难得的。是的,我就在角落里,你们说吧,你们说够了吗?不,我不解释,
我不争辩,我做一枝这样的孤寂的蕨类植物,展示着内心饱满的寂寞和喜欢。
我不把铁线蕨想象成女子。确切点说,更安静的内心,更强大的东西,男子身上更多一些。
它一样呈淡淡的阳性,或者中性,有一点点颓,可是,也有一点点向上,叫人恰巧喜欢的那种—
—喜欢穿麻,白色,头发黑,而且传统的那种发型,眼神清澈,带着难得的明亮,虽然历经岁月,却依
然被淘洗得特别动人。至少,可以看得到干净的东西。这样的男子就是铁线蕨吧?
他一定是文雅的,低沉的。一定有着自己最动人的落寞,即使寂寞,他也是优雅的——他不愤世
嫉俗,一点也不。
他最迷恋不动声色。却也温暖。很书卷,很儒雅,很中国。哲学的味道在绿意和舒卷的姿势上非常
达意,难得有这样不动声色的植物——是的,真难得呀。不动声色是难的,大多数时候,喜形于色,
张狂,惆怅百结,一日豪似一日的花开富贵,能够低眉的人简直太少了。
只有风安静了,雨停歇了,所有的繁华终于不再车水马龙一样的出现,才会有那样的时刻吧?收敛
了所有的傲气,在大雪压住红尘的夜色里,就着冷银的月光,照在雪地里,有了听雪超尘的心情。这时
,已经是株寂寞的铁线蕨了——这样的寂寞,素素然,是我喜欢的格调。
有些植物,虽然看似茂盛,但是,“格”不好。可是,铁线蕨有着别样的一种气质,虽然所有的东
西都会随着时间消失掉。可是,终究有一些东西会永远沉淀在心里,比如思念铁线蕨的这个冬天的早晨
。这是2009年的11月,才刚进11月,第二场雪又来了,远远地看去,屋顶上有了白白的一层,雪意总会
让人感觉到清冷和洁白,这恰巧和铁线蕨的格调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听雪超尘的早晨,我写到了铁
线蕨,我知道,无论再喜欢多少种植物,铁线蕨,还是我最爱的那一种。
它呀它,低低地朗润着,在这个落雪的早晨,一点点地,蔓延到我的心里,喜悦着,沁凉着。
精神强度
我喜欢“精神强度”这个词语。
非常达利。我在看达利的油画时常常会想起这个词语。他反对时间,把时间变成变形的钟表挂在树
上,把沙发做成马桶。那种精神强度可以把一切扭曲。他的画不凌厉,但看后的震撼是无限的激荡,好
像得了脑震荡的人,好长时间会缓不过来。
我在给一个美国朋友写信时说,精神的强度超越一切,超越年龄、性别、地域、时间……它的弹力
最大,可以绵到心的任何一个角落。
他在丹佛画画,说丹佛的白天真亮啊。又说那里的夜黑。
丹佛是哪里?我不知道。我喜欢这两个字的发音。有一种奇妙的香。他又说丹佛有金矿。我说金矿
好,用什么工具可以把金矿挖出来呢?我们说着一些精神世界里的花朵,他种了一园子,我种了一园子
。都争先恐后地开着。
其实精神真是最形而上的东西。最不可靠,也最可靠!就像过分美于一种植物的叫法。我喜欢铁线
这个植物。只是喜欢它的叫法。它有一种突兀的美。我喜欢类似于它的人,干净、倔强、饱满……喜欢
长风浩荡,喜欢渺目烟视……内心里越是野旷人稀,它呈现给艺术的越是生动疼痛。
一个作家说,三十岁以下的爱情不靠谱。因为完全是肾上腺素分泌太多的结果。三十岁以上,意识
形态完全成熟了,步入了一种精神领域,再喜欢一个人,精神的成分要站得住脚。
即使和爱情不沾边,有精神强度的人,不会轻易被打倒。虽然有时候他很脆弱,但这脆弱,其实是
艺术里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架,犹如寂寞花园里一朵绮丽的花,安静地开,安静地谢。
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记录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荪的。钱学森、杨振宁全是他的学生,他开中国物理
系先河,终身未婚。把自己交给了物理,交给了学生。在“文革”时期,被说成特务,为了不牵连学生
,在清华遇到学生时,他假装不认识。有学生上前打招呼,他摆着手说,不要来,不要来。那时他背已
驼发已白,每天不说一句话。他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床上,放着整摞的物理书。而他睡觉的地方,只
是一张椅子。事后有人问过他,觉得寂寞吗孤独吗绝望吗?他答,我有物理,有书,有天空,有深的精
神。如果不是精神世界的强度,或许他早就和一些大师一样选择自杀,投湖或吊梁。他倔强地活在自己
的芬芳世界里,一直到生命最后。
看《杜拉斯传》,惦记于这个女人的精神强度——她的一生,总在打倒别人,从来没有被别人打
倒过。即使爱情。她用她的文字打倒读者,用她的爱情打倒男人。在离别时,她不哭男人哭。在爱着时
,她得意地说,你多幸运呀,你爱上我,你爱上这么著名的一个作家!一点不自卑微,一点不示强弱。
不,一点也不!
我在她的强度里感觉到了无限的软弱。她没有性别,她是杜拉斯。她说,我渴望堕落。
而大师黄永玉,一直在用画来表达他的精神强度。“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
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这是黄永玉同
他表叔沈从文聊天时说的话。
黄永玉问表叔,这样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沈从文答:“懂了就值了。”
是啊,懂了就值了。
这世间,必有一种懂得是精神,穿越灵魂,幽幽而来。总有那个明白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
的惆怅的人,总有发个信儿就刹那间说慈悲的人。因为,他的精神强度恰巧与你在一个线上,不远,不
近。你说,他懂;他说,你懂。
即使没有那个一起来看杏花的人,还是饱满的。因为内心是强大的,是蓬勃的,是生生不息,是杏
花春雨里最美的笛声,是一个人的自斟自饮。是徐悲鸿说的那句,我就要一意孤行。
那些有精神强度的人,是金,藏于内心,不显露。但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会闪现出非常动人
的光芒。
即使在最孤寂的地方,他也不凋落;在最热闹的地方,他也不张扬。
他用精神支撑着内心,那个花园里,妖妖地开着一朵又一朵世间难寻的花,如果你进得去,那么你
看得到。
潦草
看过莫迪利阿尼的一张画:《露妮柴可夫斯基》,我很喜欢那个女人的神态。突然冒出来的词就是潦
草!我喜欢潦草!很潦草!从眼神、发型到嘴唇,都带着暧昧的潦草和不安!
潦草!多好的潦草,坚决不细腻不动人不精致,不盲从!当然不!
这样的潦草让我心生欢喜。生活太细腻太格调太朝九晚五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这种潦草让人安心
,很健壮,很无所谓。
想起陆小曼也是这样的女人。生活得没有章法,潦草得一塌糊涂。处处是口红、丝袜、过度的爱情
、没有节制地花钱、感情泛滥……不,不精致——虽然她梳爱司头,穿软缎衣服、着绣花鞋,用法国
化妆品,没有用的,她的眼神,透出无限的潦草。她的生活,更是潦草得一败涂地,一点也不像林徽因
,在精神上都井井有条,在生活里井然有序,反映在眼神上,坚定,固守。是的,固守。据说,生活中
的林徽因是一个坚硬的脾气坏的女人,脾气坏到可以用暴躁来形容——我非常满意这种说法,她和她
的长相,就应该背道而驰。
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她常常写到这样的女子,目光清澈,穿着洗得发了白的白衬衣,白球鞋。在
写到头发的时候,她说,她的头发非常潦草,干枯……我很被打动,我喜欢这样的女子。不喜欢太过精
致的女子,提着LV的包,一丝不苟的发型,几千块钱的衣服闪着蕾丝和钻石的光芒,对于红地毯上的那
些露着大部分乳房穿着华服的明星,我从来抱有微词,并且,嗤之以鼻。
那头发潦草的女子,于我而言是一株野生的植物,有着自然中最喑哑的光泽,生动,饱满,不修人
际中最无聊的边幅。
我迷恋那些过度青涩的东西——白衬衣、球鞋、潦草的头发、干净的眼神、简明扼要的语言、寡
言的男子……在淘宝网上,我看到“江南布衣”的一款深蓝裙子,下面只有一句话就打动了我,“如果
配上一双白球鞋,会非常动人”。我几乎没有停留半秒钟就订购了这条裙子,一是因为蓝,二是因为,
可以配上白球鞋,这真是一种要命的情结。
那些无耻的精致与我何干?有一天我穿了一身黑衣出现在一个人面前,他说我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女
人。这让我反感至极。不,我不接受“精致”这个词!我潦草得像一团草,从生活到内心——我决不
渴望精致。精致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女人的事情,我的内心,匆忙,慌乱,一副张望的样子。我了解它,
它渴望动荡,渴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渴望有迫不及待的潦草。
曾与一个戏曲演员同桌吃饭,她化精致的妆,那精致让人肃然。连粉底都透出油腻,头发更是梳理
得纹丝不乱,手上画了七彩图案,指甲极长,嗓门是高亢的——大概因为唱河北梆子的缘故,身上脱
不出世俗的艳气,而且,油粉的世故让她生出艳俗的种种可能。我与她邻座,一直寡言。我穿了白衬衣
灰裙子,没有任何饰品,手上寡白白的。她的金项链据说有30克,在香港购得。又尖声说着许多男女趣
事。我的头发泛出了潦草的荒意,我的眼神更加潦草。有男人逗她,她就开始唱梆子,很高亢,难以自
制的得意。声音绕上去,在空气里,好似在炫耀,完全附和当时的酒场气氛。我看着她,忽然庆幸—
—幸好,我这么潦草,潦草得这样干净。也幸好,读了些诗书,让我沉静似水,面露清水之色。
那些精致离我有多远呢?我决不肯文了眼线眉线,决不肯洒了香奈儿五号才去一些场合,也不肯镶
钻镶银地去穿一件衣服。我更靠近那些野生的自然的东西,近乎潦草,带着率真的苍老和墨绿,内心清
醒,不茫然,想想,这是多么奢侈。
如果在风中,我是那穿了布裙的女子,顶着一头潦草的短发,不怀幻想,果断而坚韧地迎着风走,
怕什么呢?我不怕风吹乱了我的头发,不怕沙打在脸上。那样的味道,是历经了几百年的青花吧,虽然
褪了颜色,但是,谁能不承认,它比新鲜出炉的东西更有味道,更迷人?
有一天我彻底不再年轻,而且有了再也褪不去的皱纹和更为潦草的心时,我会和那个叫杜拉斯的女
人一样,不怕老不怕丑地抽着一支烟,很强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傲然地说:我的内心很庞大,我可以
同时爱上几个男人。
这样坚硬的潦草,是我所羡慕的。
粉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苏州,真没有比粉更合适的了。
一定是粉,绝对是粉。
可以用来听的,可以用来闻的,可以用来看的。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颜色来形容苏州,或者说,找
不到恰到的气息来表达苏州。
它让我迷惑,因为离得远,或者说,因为离得近。近或者远,都会稀释一些东西。
我游荡在苏州的街巷中,游荡于粉墙黛瓦间,游荡于小桥流水的苍茫与纯真,吴侬软语的绵软。那
过马路时偶然邂逅的侧身而过的苏州老女人——她穿着软缎的粉绣花鞋,她烫了栗色的头发,皮肤松
了,可是仍然感觉出了当年的细腻和水粉。她个子不高,眼睛眯起来,张嘴说着苏州话,和唱评弹一样
。这就是苏州了,到老了都风情万端。
我更喜欢叫它姑苏。
因为突然有了人间烟火气。姑这个词,沦落到乡间,突然与苏州相遇,居然有一种夫唱妇随的妙处
横生。
还有一种暗。
我迷恋那种暗,绸缎微凉的暗。摸上去,凉凉的,但是光泽很温柔。比如那些千年的桥,或者旧墙
,凋落的皮,和北方的富丽堂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旧是宋词,是南宋凄凉的月光,是从山水画中找
到的视觉审美,不跌宕,就这样委婉地提醒着,这是苏州了。
暗和旧,可以让眼睛很舒服。因为旧,就带来稳妥。又因为暗,可以柔软。
但又隐约散发出一种气息。
是格非常高的气息。
有点像远古。人们都去忙着奔命了,可是,剩下这一个小地方,依然故我。不慌不忙,听听评弹,
唱唱昆曲。破旧的小店里,摆着当天的《姑苏晚报》和新做的青团子、酱汁肉。
早春里,粉就更有那种味道。
黄昏里,有老人在桃花树下聊天。小桃花就三两枝,还开得不茂盛。他们顶着一头银发说着苏州话
。吴侬软语就一种极美的意境,说不清的婀娜,说不清的湿润呀。也是粉色的,勾魂的。不似红的夺目
,不似白的骄人。红和白在一起,其实就是粉。
昆曲《牡丹亭》里,在游园和惊梦两场戏里,杜丽娘着粉装出场。其实是更惊艳,粉有一种暗俏。
不是第一眼就豪夺人目,可是,目的还是要夺你的目。
苏州街上,有一家照相馆就叫“粉青春馆”。拍照片叫做粉。多好听呀,多引人呀。
还有卖戏装的,挂着一件粉衣,就在春风里飘摇着。我看着香樟树下飘着的戏衣,听着远远近近的
昆曲。平江路上埋下了很多暗线,小音箱里整日在放着苏州评弹。这样的城,是引人堕落的,至少,想
发发呆,喝杯散淡的茶。
我坐在评弹博物馆中听评弹。
一男一女,一琵琶一三弦,坐于高高的台子上。女人穿了廉价的旗袍,妖艳的蓝色,开始唱曲调婉
转的评弹。其实我一句也不懂,但重要吗?太不重要了。
我坐在那里两个小时,听着他们很烟火又很入戏地又唱又说。天色将晚,我看着天光渐渐沉下去。
我身边全是当地苏州老人。我就这样把苏州的下午一个个耗了下去,很粉。
这粉,是闲情逸致。是小桥,是流水。是几千年的风致骨头,即使成了残渣,仍然是苏州的。
那粉,还表现在苏州的细节里。
整个城市是慢的,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几千年就这么过来了,有什么着急的呢?
在苏州的老街上游走,常常觉得自己的脚步太快。那些古老的铺子,散发着沉年的暗香。甚至卖生
煎包子的俏女子,脸上的表情都是寡寡的,并不着急,慢工出细活的样子,好像要把时光雕成油画或者
散文。
只有苏州,留下了那么多老建筑。把新城全建在了城外。我喜欢游走在老城,柔软的绸缎那样起伏
着。意识形态之惰性,之味道,只有苏州有。只有苏州。
粉,除了艳,其实还有颓的味道。颓,是要有资本的。经历过时光打磨的东西才颓得起,白云怡意
,必是经过了朝飞暮卷。
在姑苏,小试宜春的面,只得由它缱绻。三春好处有人见,见了那苏州的粉,可真端然。
那小金铃,那苍苔,那老绿,那花愁颤,都是粉又颓的苏州。
金粉半零星的早春,我怀揣一帘幽梦,为苏州的粉,浅吟低唱一声罢。
春耻
最怕春天。
一到春天,春就放荡了。一副不要脸的样子,简直不知羞耻了。
大片大片的花。
桃花、杏花、梨花,一个开完一个开,比赛似的。
仿佛晚了来不及赶上这一场春天的合唱了——生怕被落下,生怕错过了这一季,下一季真的来不
及了。
还有蔷薇。
不仅是热烈,简直有一种一起赴死的决然。只有春天,艳成了爱情最初的样子——多艳也不怕艳
。桃红柳绿,红也是那个红法,绿也是那个绿法。很要命的深情,无可救药了。
却感觉大面积的忧伤。一片,又一片。
凛冽到铺天盖地了——谁说我不爱你?这春天就是最无耻的证据。
就这样为你盛开着。近乎恬不知耻,近乎贱。
这是爱情的春天。不沉醉,不沉溺,不算完。
却有一种逼仄的惆怅,款款而来。
那种纠缠的不安,和春天有关。
太意兴阑珊了。
太放肆了。
一点也不内敛。一点也不温柔。
就像一支浩如烟海的军队,席卷所有堆积在你脚下——谁都再也无有还手之力。
硕硕的花们呀,开吧,开吧。那些总嫌不够的抒情,那些永远不嫌腻的甜言,就在春天发酵吧。
不知今夕是何年。
更不知要如何地收起这一颗已经燃烧成灰烬的心——零落成泥散作尘,香如故。
只有春天可以浩荡成这样,多浩荡还嫌不够,像一个女人贪婪地爱着她的男人,倒在他的怀中,深
深地缱绻着……
责任编辑王秀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