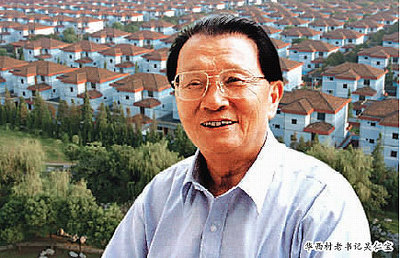迟到30年的诺贝尔奖
□文 记者/吴海云
2007年10月22日,住在伦敦西郊的多丽丝·莱辛迎来88岁寿辰。这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生日——十几天前,她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于是,老太太的这段日子不再平静。她忙于接受各国记者的采访,忙于收拾原先堆满图书与杂志的寓所,忙于接听人们打来的祝贺电话——她不无惊讶地听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声音。
她的宠物猫这些天则闷闷不乐:不只是由于女主人这些天对它疏于照顾,还因为房间里多了奇怪的色彩。多丽丝·莱辛以典型的英国人的欢庆方式,让鲜花布满自己的起居室,而那些花只有两种颜色:橙黄与朱红。
“人们显然喜欢把我和夕阳联系在一起。”莱辛对来访的记者如此解释。
诺贝尔为何授予莱辛
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前,夺标呼声最高的是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那位多产而备受争议的犹太老人,以描写手淫、政治和男人的神经质闻名于世;最终,他败给一个多产而备受争议的文学祖母,后者为人熟知的文学内容包括月经、政治和女人的神经质。
没有多少人猜到今年的诺贝尔会垂青于莱辛——包括莱辛自己。许多年前,这位作家在瑞典参加一个文学聚会,坐在她身边的一位诺奖评委直率地对她说:“你永远也赢不了诺贝尔。我们不喜欢你。”
然而瑞典文学院还是在这位作家的米寿之年给出了一道恩典,这也又一次向世人证明这一世界最高文学奖项的不可预期性。当人们觉得诺贝尔是“远离政治”的奖项时,它将桂冠授予偏好种族和宗教问题的南非的库切和土耳其的帕慕克;当人们觉得它倾向于“政治作家”时,它选择了倾向于“小”主题的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和哈罗德·品特;当人们认为诺贝尔属于文坛的“终身成就奖”时,它让米兰·昆德拉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享誉世界的文豪一次次落选。
当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总是具备一些共性。比如,他们都是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具备一种独立的、自我的,通常是勇敢的思想见解和政治信仰。他们有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立法者,但无论如何,他们在自己所在的群落里备受推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诺贝尔喜欢的作家,与其说是一个提供艺术大餐的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相对于文字的风格来说,诺贝尔似乎更看重那些文字所表达的激情与思想。
从这些角度来衡量,莱辛的获奖不算出人意料。归根结底,她是一个描述理想和理想主义的作家。后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这些20世纪流行的思潮,在莱辛的小说中都有所涉及。莱辛本人对此不无讥讽地说:“我贴上过一切可能的标签;而我自己,却从未有过任何改变。”
风雨飘零人生路
童年不幸,少年失意,婚姻草率,遗弃子女,信仰失落,半生飘零。这些会被大部分人定义为“不幸”的人生经历,是莱辛一路走来、一路笑看的风雨过往。
和其他两位获得过诺贝尔桂冠的英国作家——V·S·奈保尔和哈罗德·品特——一样,莱辛是一个局外人、大英帝国的局外人。她1919年10月22日出生于伊朗(当时仍称波斯)西部的克曼沙,父母都是英国人。6岁时,随全家迁往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今日的津巴布韦)。莱辛从小没有受到太正规的教育,14岁时就辍了学。好在她的母亲执着于将她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淑女,因此源源不断地从英国订购文学名著。于是,莱辛的少女时代便与狄更斯、吉卜林、司汤达和史蒂文森为伴。
15岁时,莱辛离开家当保姆。她的雇主给她阅读了一些政治、社会学书籍,让她迷上共产主义思想。19岁,她嫁给弗兰克·韦兹登,生了两个孩子。几年后,她弃丈夫与孩子于不顾,独自私奔,成为一个左翼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在那里,她遇到弗里德·莱辛。两人很快结婚,生了一个儿子。1949年,她带着两岁半的儿子离开丈夫,搬到伦敦。就在这一年,她加入共产党,并且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
离婚与政治,这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莱辛的写作。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莱辛偏爱描写婚姻破裂的女人,确切地说,是描写因为失去丈夫而生活支离破碎的女人。但她觉得,自己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我自己的婚姻都不怎么天长地久,但那并没有长久地影响我”,莱辛对英国《卫报》的记者说:“但是一个女人竟如此受婚姻的限制:一整代的女人,嘴里谈论的与她母亲时代的没有任何差别——这个现象长期以来都吸引我去仔细探究。”
政治,也许是多丽丝·莱辛与其他女作家拉开差距的根本原因。莱辛的许多作品都可以定义为“女性文学”,但并没有局限于感性的情感题材。她不诗意、不哀怨;相反,她咄咄逼人、一针见血。比如,她在小说中解释自己之所以加入罗得西亚左翼组织,其原因在于“左派是这个镇上唯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们理所当然地把种族隔离看作洪水猛兽”。
五十年写作丰碑
在50年的创作生涯中,莱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她的风格与题材始终转换不停。在研究者看来,莱辛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的50年代。在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之后,莱辛创作了以5部小说构成的《暴力的孩子》组曲。在这些作品中,莱辛阐述了她热情而又激进的社会理论;与此同时,一种将在日后确定莱辛文坛地位的思想元素——女性主义也暗暗抬头。这一系列小说描绘了女主人公马莎·奎丝特的觉醒与解放,字里行间蕴藏着一种迫切的、先锋性的女权意识。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的60年代。莱辛开始在写作中尝试大量的实验写法,以此来解剖人们,尤其是女性的想法。很多时候,莱辛的解剖具有令人惊悚的文学效果。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出版于1962年的《金色笔记》。该书分5个小节,记叙两位单身母亲(安娜和莫莉)的生活和事业;而各小节之间夹有一串“安娜的笔记”。这些笔记片段以笔记本的颜色(黑、红、黄、蓝、金)命名,分别记录着女作家安娜过去的非洲经历、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和体验、一篇正在构思的小说以及她当时的生活。
很显然,这本厚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安娜便是作家本人的化身。她所记下的笔记没有太多的多愁善感,只是铁了心地向往自由生活。欧洲的女性主义者公推安娜做她们的代言人,集体抵制那种“从禁锢在小阁楼里的童年到消耗在相夫教子、买菜烧饭的青春”的传统命运。莱辛也由此成为当时在欧美国家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的标杆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莱辛将她的文学实验转向另一个领域。她突如其来地迷上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并将笔锋转向科幻小说,出版了《天舟座老人星:历史档案》系列。莱辛本人对她的科幻小说似乎非常满意,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媒体表示《天舟座老人星:历史档案》系列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然而,大部分文学评论家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莱辛压根不适合写科幻小说,其“转型”简直是在浪费自己的才华。美国资深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位。他向美联社记者表示,莱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简直让人读不下去,是“四流的科幻小说”。人们倾向于认为,如果莱辛没有涉足科幻,应该早就可以摘下诺贝尔。
瑞典文学院似乎站在评论家这一边。
反女权主义的女性主义标杆
在评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时,瑞典文学院给出了这样的判词:“这个表述女性经验的诗人,以其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一个分裂的文明作了详尽细致的考察。”他们只字未提莱辛的科幻小说,反而将作家写于45年前的《金色笔记》单独罗列出来,称它是一本“先锋性的作品”,是“影响了20世纪的男女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之一”。
诺贝尔把莱辛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先锋战士来奖赏;可这对于莱辛来说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由于《金色笔记》,莱辛无可争议地成为英国最年长的女性主义“代言人”;但自从此书出版以来,莱辛无时无刻不想摆脱那个恼人的头衔。
莱辛不希望被视为“女权主义者”。在一次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她说:“女权主义者希望从我身上找到一种我其实并不具备的东西,那种东西其实来自于宗教。她们希望我能说这样的话:‘嗨,姐妹们,我与你们同在。我们共同战斗,为了迎来一个再也没有臭男人的金色黎明。’她们发表的关于男人与女人的宣言无聊至极,但那正是她们想要的。我对她们无比失望。”有女权主义者询问她,是否认为战争都是男人发动的,她幽默地回答道:“我并未发现女性成为首相后,会特别爱好和平。”相反,她表示,一些最糟的罪行是女人干的。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吊诡由此出现:人们视《金色笔记》的作者为女权主义的开路先锋,然而那个作者本人一点都不想成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英国同行;她甚至不想效仿弗吉妮亚·伍尔夫(尽管莱辛对于伍尔夫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耿耿于怀)。在莱辛的世界里,女人的不幸可以解剖,但不可以用来控诉。她的人生信条是:寻求自由的女性必然要付出代价。她没有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男人——尽管那些男人可能入不了她的法眼。
这就是多丽丝·莱辛,一个坚定的“反女权斗士”——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不管这位作家本人怎么否认,她确实是在与广大女性“共同战斗”;不管是记录下女性日常意识的笔记本,还是描述女性社会的科幻小说,都证明了她的战斗。只是莱辛太聪明了,无论是她天赋的才华,还是她个人的经历,都让她在很早之前就明白那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即使是她这样的聪明人,也是一个永难平衡的性别社会的产物。
来源:2007年第31期 总第272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