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严”以来台湾的家族书写虽然是个人叙事的多音调唱和,但不同方式的家族叙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承担,叙事立场与对家族的认知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回复,还体现了当前台湾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处境、心理与文化认知。从书写者自身的处境与叙事立场来看,在书写家族过程中的各种观念、对家族的态度、对现实的看法,都体现了作者再现家族的文化关怀。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的特征与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的特征与意义全文如下:台湾在1987年政治“解严”以来,社会文化渐趋多元,不同的文化诉求与文化观念影响了不同群体的家国认知,在多元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家族”成为再现内在情感与表述文化立场的重要场域,出现了不少家族书写之作。本文所指的“家族书写”有以下几个要素:以家族为书写对象,或者透过核心家庭来写家族;通过对家族的想象、追忆或建构展示书写者的家族情感、价值判断或自我认知,“家族”不仅是书写的对象,且成为书写者抒发情感、表达各种理念的方式。“家族书写”严格来说并不是一种文类上的区分,而是从作品的主题内涵,以作品的实际情形与历史条件作为主要的思考面向与依据。因此文本的选择,并非仅以“家族”题材作为参考,更注重其对家族的探寻、追忆和思索,对家族和个体命运的审视,对历史的反思。
一
海峡两岸的家族书写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常以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指向一种预设的观念或看法,虽然家族故事的演绎以多个人物的行为进行,但在同一文本中叙事人称较为统一,像大陆的《红旗谱》和台湾的《华夏八年》等小说,而全知全能的叙述视点也强化了作者的解释权。但在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家族书写中,家族叙事的叙述视点发生了变化,更多以“我”的角度呈现。尽管所有的人称后面都存在一个叙事主题,但叙述者以“我”的姿态出现时,很容易成为叙事主题的替身。这就意味着更为个人的、私密的话语表达形式突破了曾经的宏大叙事结构。
叙述者“我”对家族故事的讲述与参与是近年来台湾家族叙事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几乎所有的家族书写都展现出这种个人化样貌,当然“我”的存在是多样的,“我”不仅是叙述者,还是家族故事的扮演者,是家族当下处境的代表者、观察者,以“现在”的情感、姿态、感受与那个“过去”的家或家人所处的时代对话、沟通。这一被叙述的时空是从“现在”的家向“过去”的家滑行,又以“过去”参照出现在“家”的形态、处境。形成现在与过去的交织,虚实交互的家族想象空间。
在张大春的《聆听父亲》中,“我”首先以说书人的形式出现,对一个想象中的孩子讲述家族故事,先交代讲述的目的、动机,继而讲述“我”和父亲在台湾的家庭故事、大陆祖家的故事:
让我和你――我的孩子,一起回到我生命中那个十分天真的时区,看一看那饭桌旁我们一家三口所受的微不足道的委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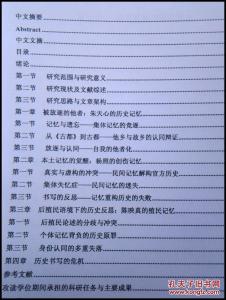
五个世代之前的故事,完整的只剩下一则,我把它先翻译成白话文――像抓住一片在狂风之中飘零不落的灰烬――告诉你。
通过说书人的视角,“我”游离在家族故事之外,又成为纯粹的叙述者,家族故事因而具有传奇性的一面,好听而有趣,如“长者估衣”、“外戚活诸葛的教诲”、“庵清大爷”、“信守”等成为独立的家族故事。
而说书人的姿态则带有表演的性质,是“我”以父亲的姿态向孩子“你”的深情诉说,也是试图与自身经验拉开一定的距离回观这些消散在历史中的家族记忆,但这种客观化、陌生化的努力却无法掩盖书写者对家族故事的沉浸,因而形成叙事艺术的张力。黄锦树曾指出,张大春要么是纯粹的叙事,要么是反叙 事――博议、旁白、好现身说法做模仿秀的叙事人,但这两种形态都指向一种和故事有关的乡愁――对传统说书人的召唤。在张大春的家族叙事中,“我”作为说书人的意义,正体现了黄锦树所指出的旁白、现身说法,以拉近作为孩子的“你”聆听的距离,形成多重的对话,“我”与“你”的对话,“我”与“父亲”的对话,“我”与遥远家族中许多家族成员的对话,是游走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想象家族史的努力与情深,是一个作家从叙事试验和语言游戏走向现实人间的表现。
忽而祖家故事、忽而父亲的故事、忽而“我”的童年、忽而以“我”作为儿子和父亲的口吻议论祖家、人生与人性,以此打散线性的家族叙事,将家族故事分成块,进行拼贴、重组,家族史亦非传统家族叙事中的完整统一。然而《聆听父亲》中的“我”不再是张大春早年创作“后设小说”时那个拆解意义的发言者,对家族故事的拼贴亦非为了解构故事的意义,“我”反转以往怀疑一切的精神,在父亲、孩子面前显得如此深情,努力拼凑记忆中的祖家或父亲言说的家族史,使之成为一个有现实意义与情感价值的叙述框架――大陆的祖家是源头和象征,移民者的后裔抚触着家族痕迹,在融合与断裂中认识自我。
讲述故事的角度与态度代表了讲述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与价值判断,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故事设计者的意图与思考,李昂的家族叙事则体现出另一种样貌。小说《迷园》以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进行交叉叙述:“朱影红”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所展开的大多是悲情底蕴下的关于童年、家族及父亲的记忆;第三人称的“她”的视角讲述作为女性在现实社会的各种挣扎;第一人称“我”的回忆、心理感受的意识流动重复回望前两个“我”的存在与意义,是真实的自我印证或继续前两种讲述。《迷园》以此制造一种重叠的、不连贯的、多层次的叙述空间,从不同角度展现一个女性的身世经验、家族记忆与社会位置。而叙述人称的交叉变换,正造成记忆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跳跃,同时说明记忆的凌乱、历史的断裂与不可还原,“看似凌乱的叙述正可显现女主角的女性身份与国族身份不可分,以及多重创伤造成的断裂”,李昂书写家族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家族创伤记忆声援一种政治意识,还提供了女性通过建构家族史所展现的性别意识――通过朱影红的努力完成父亲、母亲修复家族园林的愿望,而企图建构女性在家族、历史与社会记忆中的主体位置。
相对于张大春含蓄深掩的家族情感,以及李昂以不同角度叙述家族史所凸显的鲜明的性别、政治及历史思考,骆以军的家族书写常常以叙述人称多变与叙事空间的流动性位移制造一种梦幻的、戏剧性的场景,常在叙述中以“()”来注解自己对父亲、家族与迁移历史等各种事件的看法,使记忆再现成为凌乱的碎片,形成一种对家族往事对父亲历史的游离与质疑。在《月球姓氏》中,叙述者“我”似乎总在担心叙述无法表露事情的真相,总是迫不及待地旁白、补充解释,想要证实一些什么,不顾及叙述进行到哪一步或情节如何,例如对家族成员哥哥的讲述:
我哥从小眼皮就厚,不会察言观色(我看过我哥小时候的照片,确实像某种眉骨突起,半透明眼膜遮蔽住上半眼球,莽原之类的两栖类幼生期的模样。
这段姓氏变迁的过程,暗喻着我父亲作为迁移的第一代,以及我阿嬷作为无神主牌的养女世系,两个漂泊者对各自出资的受精卵(我哥?),某种各自极度匮缺极度憧憬的姓氏观念的强悍意志之对决。
在回忆哥哥样貌时进行插入补充,似乎是叙述者“我”担心事实或真相不被信任,但补充的叙述中比喻修辞又如此的滑稽无厘头,造成另一种不可信,对姓氏变迁的讲述也同样显示出一种质疑,在提醒大家相同“受精卵”所诞生的不同姓氏的兄弟所隐藏的家族秘密。在很多叙事文本中,第一人称的出现是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性或一致性,但骆以军所设置的第一人称叙事反而为了打乱故事的的整体性,制造一种不断离题的漫游,游离在记忆或事件的叙述之外。
在限知性的第一人称之外,骆以军的家族叙事还不断让第一人称“我”转换成“他”、“你”进行叙述,如以“他”的视角讲述文本中属于“我”的行踪或记忆,营造一种远景的观望视点,在“动物园”、“医院”这些故事场景中的叙述即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所有的讲述都与父亲有关,父亲的身影、照片、日记或“我父亲说”的痕迹,父亲的身世在“我”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与言说中渐渐聚拢。当家族叙事以较为客观的角度展现“我父亲”为主体的逃亡故事时,父亲的历史在被叙述时同样呈现巨大的分裂。以此,骆以军的家族叙事,作为历史记忆回溯浪潮中的产物,所要探讨的核心,绝不是“再呈现”而已,而是在凌乱的记忆
材料中挖掘被忽略的故事杂音,舒展抒情诗意――那陈述、遗忘、追忆的动作,如慢格画面,在骆以军笔下形成华丽的割裂,而叙述者不断介入历史记忆的重组活动,将记忆作丑怪处理,看似驳杂纷呈,实则企图将所有杂音与奇想笼摄到诗意底下,诗化破绽的历史。这是骆以军通过多重叙述角度所再现的家族史与父辈历史的断裂。
总体而言,在近年来的台湾家族书写中,叙述角度较为多元,家族故事或家族记忆是焦点,通过不断变换的讲述角度使得家族故事的情节发展打破传统家族叙事中平面化的、历时性的结构。而以多重叙事角度、多样化的叙事线索营造立体的叙事空间,同一叙述人在文本中拥有多种叙述人称,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在文本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文本以特征[7](139)。家族故事也因此充满张力,历史叙事也充满各种歧义与破裂。尤其是第一人称替代作者在文本中的表现力,在向自我的内里收敛的同时还技巧性地将自我经验投射到身世叙述中,拉开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与故事的距离,展现由虚构与想象生成的文学空间,突出了家族叙事的主观情感性及作家的审美体验。这些叙事特质成为“解严”以来台湾家族书写的独特之处,而这一特质正源于书写者对家族与历史的独特体验。
二
“解严”以来台湾的家族书写虽然是个人叙事的多音调唱和,但不同方式的家族叙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承担,叙事立场与对家族的认知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回复,还体现了当前台湾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处境、心理与文化认知。从书写者自身的处境与叙事立场来看,在书写家族过程中的各种观念、对家族的态度、对现实的看法,都体现了作者再现家族的文化关怀。台湾“解严”前后至今的家族书写大体呈现出以下几个层面的关怀:从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家国之思、对家族/族群文化的再建构,到对生命美学的执着、在叙事中寻求救赎。也就是前文论述的家族书写在叙事视角上越来越趋向于个人,家族承载的历史意义逐渐被一种对家族场域中个体生命意义的探寻所替代。
在“解严”之前,以萧丽红的《桂花巷》与《千江有水千江月》为例,在其所建构的家族中,家族人物的言行都浸染着旧文化的美感与道德承载,家族叙事充溢着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她的家国观念中也并未将台湾女性或台湾人特别区分出来,而是统归在“中国”这一文化身份之中――《桂花巷》中的赐红被萧丽红看做是在汉文化漫漫五千年的岁、月、光、阴里生活过的众多中国女子之一①。《千江有水千江月》则全面肯定家族制度、宗法制的生活方式与伦理形态,处处是诗词玄机、传统之美,日常生活亦成为是一种略带刻意的诗性空间用以颂赞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书写姿态亦被认为一厢情愿地美化中国文化,虚构浪漫的乌托邦。
作为台湾本土女性,萧丽红所创造的桃花源看似建立在台湾的乡野,其实是理想化的古君子国,这个古君子国,寄托于乡野与古早时代,盖时空的推远,有距离的美感,也有象征的效果,是神话也是寓言,描写的是文化中国的乡愁[9](173)。萧丽红的家族叙事所体现的文化关怀似乎受到七十年代末台湾文化界“回归中国”/“回归乡土”论争的影响,以地理台湾的书写实践文化中国的想象。但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颂,在其“解严”后的家族书写如《白水红春梦》中不复存在,家族不再是纯净的礼乐乌托邦,而是承载政治暴力的创伤记忆所在。通过萧丽红在“解严”前后对家族的不同观照,可以看出家族从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转移到作为被压抑的场景,这其间亦是书写者叙事立场的转变,文化中国在本土意识的攻击下渐渐成为不可言说的存在。但萧丽红的家族叙事不仅提供了我们思考家族在台湾文化语境中的寓意转变,还提供了以家族书写寻求化解历史创伤的可能途径。
若以作品出版的时间先后而言,李昂的家族叙事恰弥补了萧丽红从文化中国抽身转向本土关怀的空白时段。李昂的《迷园》是在台湾政治“解严”后较早以家族书写表露去中国化的文学实践,通过对家族空间的重构体现其个人化的本土立场的家族言说。在《迷园》中,李昂以一种怀旧与恋物的心态雕饰了鹿城朱家的贵族气质,显然对旧日家族的想象是为了衬托家族在日后的衰落与凋零,并强化一种日据时代的朱家反而比战后还要好的观念,因而父亲以要求家人使用日文对抗现实政治,这种不满继而成为对家族园林――“菡园”实施去中国化的实践。
麦克---克朗认为文化影响了日常空间,“菡园”作为朱家生存活动的家族空间,是先祖对传统中国依恋与孺慕的象征,不仅在空间形态上是大陆家族园林的翻版,在布局与植物种植上也以模仿大陆建筑格局为主。例如种植台湾刺桐,本意是取大陆梧桐会落叶的意思,在书房旁种榉木,取“榉”音表达希望中举之意。在这样的家族空间中,显然朱家数辈人的生活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心物合而为一”。当朱影红的父亲受挫,家业衰败时,对家族空间的整顿显示出极其复杂的家族情结,不忍抛弃原有的文化空间,又对这种模仿大陆的空间布局不满。而至朱影红,父亲的犹疑变成她的坚定,改种台湾树木,并将家族园林修整之后以民间形式捐献。这些显然都只是铺垫,李昂的用意在于通过对植物的
更换表明家族的台湾属性,先祖所建构的家族被新的文化观念拆除,以朱影红的视角指出:“我要这座园林,属于台湾,属于台湾两千万人,但不属于任何一个压迫人民的政府。”叙述者朱影红的立场与看法,显然就是李昂所要表达的――“小说的呈现,自然就是我要说的”。李昂以家族叙事所实践的去中国化意图昭然而出,叙事的目的也正迎合了八十年代末期之后台湾本土化声潮的浮起。在极力而为的菁英姿态之下,《迷园》在家族叙事中以极为造作的对历史创伤的不断重复叙述,迎合了近年来弥漫于台湾社会的浮泛的滥情及仪典性的创伤记忆姿态,复制了通俗性的历史意识。
随着台湾政治语境的变化,尤其是在两千年经历了政党轮替,本土化潮流影响了历史书写与记忆再现的方式,作家因政治意识形态或身份认同的立场被贴上不同的标签。因此,在新世纪以来的家族书写中,中国文化与原乡意识成为边缘的存在,如朱西宁在《华太平家传》中所苦心经营的家族叙事成为没有读者的,写给自己看的为了书写而书写的作品。虽然文化环境如此,朱西宁还是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理念,其家族认知与原乡情结使其最后的家族书写成为孤独的存在,他以及他的文学意义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尾声。因此,等到朱西宁的后辈展现家族时,历史与文化渐渐黯淡,家族成为一个符号,一片荒凉的废墟。在张大春的家族叙事中,家族故事还略带传奇,有情节有意味,叙事中透露一种对过往的怀念和留恋,如祖家的门联匾额、家信等都是无尽的故事。虽然中国近现代历史在祖家几代人的命运沉浮中有或隐或现的痕迹,但显然张大春并不是像朱西宁那样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关注家国命运与现代性问题。
张大春以极为个人化的叙事方式将大历史转换成个人成长的印记,大历史如日本人向济南城开炮,不过是二姑出生,得名“大响”又被伙伴们戏谑成为“惨案喽!”,而关于“五卅惨案”,父亲的记忆不是多少士兵杀了多少士兵,而是个体对生命和情感的体验,他只记得他那时出水痘被关在地窖,母亲给他包了一板子蚕豆大小的饺子,而回忆只能让他更加思念祖家,思念母亲。张大春的叙事是通过想象祖家而向后看再向前看,给未来的孩子一个交代,也给父亲的衰亡一个交代,亦可谓之个人抒情的父祖追忆,在其中寻找命运之于“张家门”的痕迹。这种温情的姿态与在家族追忆中对传统家族文化的依恋,在另一面说明“多年来的‘说书’和小说技艺追寻,对古典的丰富智识和修养,张大春展现的‘旧’和‘深’暴露了在‘先锋’形象背后,他真正所坚持的乃是(保守的?)文化价值。”如吕正惠所认为的,《聆听父亲》是一部和自己的过去握手言和的书,是对过去自己不信任的父亲的历史重新思考,他的“家族史”扩大来看可以说是台湾外省族群的心态 史
这种“心态史”渐渐演绎成更细微、更私语性的家族再现,是对个人生命美学的着迷与沉浸,关于记忆、身体与命运的思索。承续者是与张大春有着师承关系的骆以军。骆以军的家族叙事琐碎而冗杂,最显著的特点是时间背景淡化,对空间感的营造使得叙事成为近乎凝固的慢镜头一一映照在不同的场景,慢慢推移到一群杂乱的家族人物,在如废墟般的梦幻中潜行。因此,家族历史成为模糊的概念,除了对父亲1949年的逃亡叙述,家族中关于迁移的故事宛如传说一样散发着迷魅的错乱。家族记忆是散乱在火葬场、办公室、超级市场、动物园、废墟般的官邸、医院、中正纪念堂、校园、机场……这些流动性空间中的片段性的拼凑。Doreen Massey认为,空间往往是在和时间作对照,时间往往是和历史、进步、文明、科学、政治与理性,形成一种联系关系,而空间则经常和静态、复制、怀旧、感情、美学、身体形成另一种隐喻关 系。
骆以军关于家族的记忆刻意营造特殊空间中的感受,记忆已经变形,宛如谜语碎裂在各种恍如废墟的空间缝隙之中,以此召唤、复归关于父亲及家族的凌乱历史。家族叙事既提供了寻根的努力,看到家族之源头,又让这一根源变得破碎不堪,除了夸张外省第二代的孤臣孽子姿态②,其意义在于安顿父亲的历史与记忆。安定父亲的历史,事实上也是以书写寻找自我,安放纠缠在记忆中的与父亲的关系,对曾经的家族执念释然。
与这一外省族群“心态史”的家族书写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安抚相比,简?的作品同样是以叙事寻求心灵的救赎。她的《天涯海角――福尔摩沙抒情志》通过家族史的追寻和建构“所写的‘福尔摩沙’史,所记录的既非世代交替与政权移转的台湾史,也不是岛上个别居民个别的挣扎史,而是集结战争、移民、冲突、生态、自然、欲望、期许、悲伤于一堂的心情札记”[12](50)。这样一种视野开阔的家族书写提供的是尝试打破被框定的族群神话与身份认同的区分,通过叙事将之转化成台湾岛上普遍性的非特定文化意义的常识性认知。简?书写家族溯源的“刺点”不是为了怀旧或者如外省第二代那样安顿父亲无所着落的灵魂,她的“刺点”源于立足本土的“血统纯正”令她不安,家族史是一个切入点,但是她不想仅局限于此,她以为只有将家族史放大到与台湾岛的身世有关,唯有如此,意义才大,因而简?从历史架构来看家族与
个人,来检验自己已知的、隐藏的血统――“我之所以会那么坚定地去发现自己的不纯正,一方面是为了跟潮流对抗,另一方面来自设身处地的感受:我跟一个‘纯正的外省人’结婚了,我从他们家族身上发现“纯正”的焦虑与脆弱”③。因此,家族书写回到对普遍人性的尊重与理解。简?提供了我们感知家族书写的另一种维度,书写的意义不仅在于拯救个体心灵在时代潮流中的沉浮,更在于以文学拯救抚慰被政治意识形态搅乱的历史根源与日常生活空间。
家族书写并不只是为了讲述家族记忆,在作者进行叙事的时候借由叙事呈现的是立足当下的思考。对当下文化观念的附和或正反辩证也正是家族叙事的价值承担,这一叙事价值至少提供了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书写者的个人情怀得以释放,无论是惋叹一种文化的失落、父辈的逝去或是想要建构新的主体地位,家族叙事都提供了作者诠释现实与历史的个人立场;其次是被书写的家族人物在叙事中凝集成不同的世代位置,不管他们是故意被大历史或现实政治遗忘,还是她们被家族文化与性别观念遗漏,他们或她们的故事通过家族叙事得以重新拼装组合,成为独特的个人命运得以被记载并赋予新的文化意义。
注释:① 萧丽红在其小说《桂花巷》的后记中讲到赐红时说“汉文化漫漫五千年的岁、月、光、阴里,不知生活过多少这类中国女子”。
② 王德威认为《月球姓氏》“夸张外省第二代孤臣孽子的姿态”是为了死亡叙述与时间谜语,延展叙述与时间角力。
③ 简?的表述来自访谈,张清志记录整理的《在梦中书房遥望天涯海角简贞VS罗智成》, 发表于台湾《联合文学》。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