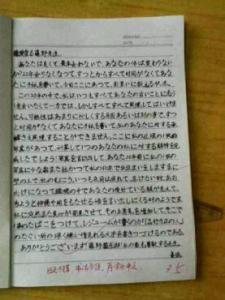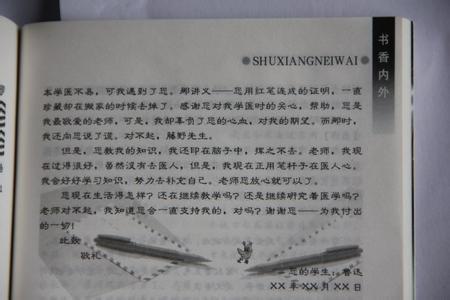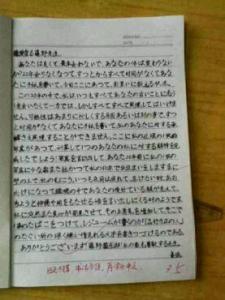我喜欢将我生活的点滴与Z先生分享,好像在述说一个零散的故事,却又是在说一段人生。下面小编整理了给亲爱的Z先生写一封信,欢迎阅读。
给亲爱的Z先生写一封信篇一
亲爱的Z先生:
你一定知道乌斯怀亚这个地方的吧?
所谓的,地球最南的城市。坐标是54°48'S 68°18'W / 54.8°S 68.3°W / -54.8; -68.3。
算起来的话,坐标是109°31'E 18°14'N 的三亚,号称自己是天涯海角还真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据说很多中国人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一部叫做《春光乍泄》的电影。
演员有眼神迷死人的梁朝伟,有胡渣扎死人的张震,还有那个因为太不开心,就纵身跳了楼的张国荣。
按理说,我应该并且必须看过这部电影才对,根据我年少时无比愤世嫉俗的桀骜个性和极其风花雪月的文艺腔调来看,这部电影光是剧情和色彩就该符合我的口味。
可是事实上,我确实没有看过。
多少年来,依稀从不同人的口中,获知了“黎耀辉深爱着旧台灯”“张宛满世界地寻找爱”“何宝荣抱着毯子哭泣”之类的片段讯息,但我即便在最百无聊赖的时候,也没有动过半点要把这部电影看完的念头。
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不喜欢梁朝伟。不喜欢张震。不喜欢张国荣。
更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去看一部关于纠结的爱情的电影。
我倒是知道张震在影片里是去过乌斯怀亚的,在那座号称地球最南的灯塔上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
当别人告诉我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其实也刚从那座灯塔上回来不久。
我曾跟一个人玩过一个游戏,比赛说看谁最先到达地球最南的灯塔上。先到的人,就要在灯塔的墙上刻上一个问题,由晚到的人负责去回答。
先到的人是我,然后我就在某个角落的墙壁上,刻了一个问题。
后来我有问那个人,他是否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却是一脸茫然地告诉我:明明先到的人是我才对。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座三色灯塔里,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他留下的信息的。
而他也完全没印象,我那个留在不算太显眼的角落里的奇怪问题。
再后来,这个人死了。被一种我第一次听说的癌症夺走了生命。
他死掉两年后,我学会了使用GOOGLE。才发现,其实地球最南的灯塔,是在一个叫做合恩角的小岛上,惊涛骇浪,水流湍急。
我去过的乌斯怀亚三色灯塔,其实不过是游客所能方便到达的最南的灯塔,是专门为游客所准备的,一厢情愿的产物。
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我问了什么。
我也再没有兴趣去寻找他的问题。
我们两个人,一辈子都没有交出我们的答案。
那次的事情,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永远”。
是啊,毕竟他的生命早早地就到头了,他的时间结束了,以后他就只存在我的记忆里,对他而言,我成了相对意义上的“永远”。
我没有用我的生命,去等来我渴望的“永远”。反倒是以一种我不怎么喜欢的形式,送给了别人一个相对的“永远”。
我自然不会觉得开心。
如今,我跟你也开始互相说“永远”了。
你曾慨然地说,“谁又可发誓,他今生一直是这般的如一!”。
其实谁也没有资格发这个誓的吧——谁比谁早死了,剩下的那个人就失去了“永远”的权力,他还活着的那些岁月里,哪怕只要有一丁点的移情别恋的念头,那个被蒙上了神圣光环的“永远”,就会如同贞操一样,被很粗鲁地糟蹋掉。
可是呢,我却依然愿意跟你说“永远”。即便有可能你比我早死,我也有兴趣去挑战我对情感贞操的捍守极限。
或许两个人相爱的最高境界,不是看谁更擅长嘘寒问暖无微不至,而是一意决心比对方活得更长,然后把“永远”的美梦送进对方的棺材里下土陪葬。
不肯跟朋友下楼去做脚底按摩的
R先生
XXXX.X.X
给亲爱的Z先生写一封信篇二
亲爱的Z先生:
每个城市都有至少一个地标。
伦敦有大笨钟,纽约有女神像,巴黎有埃菲尔,北京有天安门,就连那些毫不起眼的小城小镇,也必然会有当地居民熟悉的大型地标,通常是人民公园或者百货大楼,约别人见面的时候比较好找。
东京有什么?
都厅一座,八公像,表参道,外场摩天轮,彩虹大桥,Omotesando Hills,汐留大楼群……
掰着指头数一数,重要的真不少。
还有从法国借来的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以及还是从法国借来的埃菲尔铁塔的拷贝品。
东京塔。
人们明明都知道它是埃菲尔铁塔的借尸还魂,但人们都从不把它当作是异国的血脉流在东京的中心。
它是我们的。健太郎曾这么跟我说过。
第一次见到东京塔,是在下雨天。
铁架上的红漆,在有些发乌的天气里显得略微班驳。
我坐在出租车里,从远远地眺望,到高高地仰望,那座铁塔离我越来越近。
下车的时候有人撑伞过来接我,穿着黑色西装的青年,连伞也是黑色的。
他姓宫地。笑起来总是雨天里的太阳。
今天不宜参观。他说。
然后带我走去别的地方吃拉面。
第二次见到东京塔,是个大阴天。
我已经没有信心再把我那半吊子的学业进行下去,于是坐了车从京都跑来东京闲逛。
快要走到入口前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拉住我的胳膊。
是个背着运动挎包的男生,脸上的青春痘正旺盛地滋长着。
我后来知道他叫清志。一心想做未来的足球明星。
今天不宜参观。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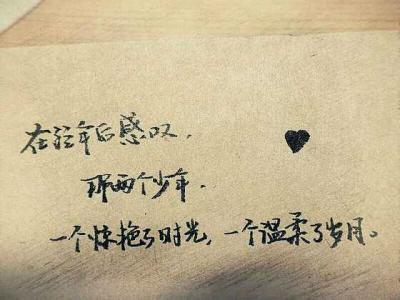
然后带我走去别的地方吃拉面——
不是上次那一家,要更加远一点点。
第三次见到东京塔,竟然在半夜。
下榻的酒店就在神谷町邻近,我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晚上亮灯的东京塔,只可惜因为层高的缘故,顶端的部分被档住了一点点。
那时我心高气傲,却又偏偏被一连串的现实打击压榨得身心俱疲。
东京塔竟然让我看得心头一暖,我忙不迭地奔出房间,去敲我楼上那个房间的门。
请跟我换房间!我大声地向前来应门的,从香港来的一位老先生请求。
请便。他从愣神中反应过来,亲切地露出了微笑。
我将大床费力地挪到窗口,把窗帘全拨到一边。
那晚是东京塔陪我入眠。
第四次见到东京塔,是个大晴天。
我要离开日本去台湾,临别前念念不忘地想探访这个钢铁大朋友。
登上150米高的观望台的时候,我看着巨大玻璃墙外的东京市区,微微有些心事被触动的感觉。
你应该再往上登100米。有人站在我身边说道,是个眼睛细长的高个子男孩。
你运气很好,今天非常适合参观。他带着我往特别展望厅的电梯走去。
那是整个东京的天顶,漂亮的阳光把地面和建筑物都晒得如同刚从洗衣机里捞出来似的新鲜。
烦恼会走,寂寞离散,没有谁会一直守在自己的身边。
但是东京塔始终都在,你需要它的时候,随时可以过来看看。
它的寿命比我们都要长的多。
那个男生,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后来再也没有回过东京。也自然再也没有拜访过东京塔。
但是我的电脑里存满了东京塔的照片,宫地君送我的东京塔小挂件我也一直随身携带。
每当我闷了累了烦了恼了的时候,我就会看看照片玩玩挂件。
想起它曾陪我度过许多艰难的时光,便觉得有如知己爱人般贴心亲密。
而且直到我死了,它也依然还在。
只要没有哥斯拉。
每个人心中也都至少有一个地标。
东京塔是我许多年来,光是想起就觉得温柔的地标。
因为关于它的记忆,始终温暖。所以无可替代地成为我的精神依靠。
而你,则是我心中那座矗立在纽约的东京塔。
又翻出老照片来一一回顾的
R先生
XXXX.X.X
给亲爱的Z先生写一封信篇三
亲爱的Z先生:
即便是我这样贪生怕死的人,有时也会想要去体验死亡。
因为那是一种,只能体验一次的感觉。
体验完之后,就什么都完了,连去体验别的东西的机会也都一起剥夺了。
所以,死亡应当是每个人要放在最后,再去体验的事情。
什么都体验够了,只剩下死亡,然后去体验掉,便再也没有什么遗憾。
可是人生这么多的新鲜东西,只凭借短短几十年时间,又怎么能全尝试完?
难怪秦始皇一直都想长生。
有一个牌子的香氛叫Demeter,是美国人将世间万物用嗅觉进行描绘的感性反馈。
北京的三里屯也开了这家店,存下了近百种气味,有雪花,有洗衣间,有蜡笔,有沙发,有太阳晒过的床单……是关于气味的图书馆。
我找到一瓶叫做“天国的呼唤”的香氛,英文名称是Funeral Home,其实应当翻译成殡仪馆才正确。别人还给我推荐了两瓶,一瓶是Bonfire,一瓶则是Christmas Tree。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晚上,把这三瓶香氛混着喷满整个房间,接着静静地躺在床上,闭上眼去呼吸。
这大约就是一种火葬场的气息了。
我居然会很迅速地就睡着了,一直熟睡到第二天的早上,睁开眼的时候因为没有看到天堂的景象而感到略略有些失望。
看来,我似乎还满享受这种短暂地,死掉的感觉。
不擅长大声说“我爱你”的古人,往往会把“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时死”视为是浪漫的极致体现。
那么,我也许会找一个时间,把你拉到房间里,再将剩下各半瓶的Funeral Home、Bonfire、Christmas Tree喷得到处都是。
然后紧紧牵着你的手,两个人一起闭着眼呼吸。
我们就那么简单地,一起享受,死去。
打算呆会要去刮胡子的
R先生
XXXX.X.X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