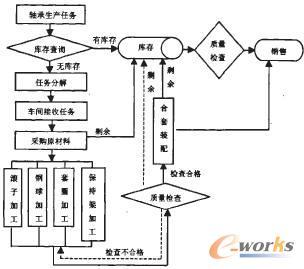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道路艰难而坎坷。在民族认同上,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人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转变。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深入探讨这一转变对于正确认识巴勒斯坦民族的复兴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以色列、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对于认识现代民族的分化与整合也具有参考意义。
一、学术界关于民族过程的理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发展阶段已有不少研究和论述。在论述巴勒斯坦民族发展历程之前,有必要对学术界的有关论述进行简要的梳理,以便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行深入分析。
斯大林曾把民族的形成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他说:“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处于民族形成的高级阶段,车臣和卡巴尔达处于民族形成的低级阶段,而柯尔克孜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我国学者也提出,在民族形成以后,就其内部的凝聚来说,还有一个从雏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从民族的初型到定型也有一个发育过程,即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民族的发育”。
在对民族过程的研究中,根据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情况,可将其划分为“潜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三种状态。最早对民族发展形态做出“自在”和“自觉”划分的是费孝通先生。他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形成时讲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先生在此仅就中华民族的形成谈到了“自在”和“自觉”,但实际上这也是民族形成和存在的两种普遍状态。
在完整意义上提出民族发展状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希恩博士。他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一文中,提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即“潜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在民族诸要素完全凸现、构成完整的民族实体之前,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虽然还不是民族,却具有滋生民族因素的土壤,具有向民族转化的趋势,故可视为“潜在民族”;“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的区别在于族体能否被自身认识,即民族认同问题。由于民族是人类相互隔绝的产物,而民族认同只能发生于民族交往、形成对比之际,认同的完成也有从个别到普遍的过程,因此,一般来说来,民族认同的发生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同步。民族认同在“自在民族”发展阶段并不一定存在,但却是“自觉民族”发展阶段的必备特征。以民族认同为标志进入“自觉”发展阶段有两种途径:由“潜在民族”到“自在民族”,经民族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顺序型发展进程;“潜在民族”未经“自在”阶段便先行发生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跨越型发展进程。
笔者认为,王博士的理论对于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下面笔者就以王博士的理论为依据,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经历,探究巴勒斯坦民族的状态和发展历程。
二、从“潜在民族”到“自在民族”在阿拉法特时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潜在民族”。它虽拥有语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个“原生民族”,而是一个“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途经:(1)从民族分化而来;(2)由民族聚合而来;(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显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属第一种途径,它是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自我认知以及民族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是需要人为努力的。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初始形态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这种初始形态的民族意识还不可能为全民族所认识,要想使其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为群体成员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传播。而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广泛传播;他为巴勒斯坦人赢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从“潜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只有1/3的人继续留在当地,且大多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于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总体上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经历了一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其民族主义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给犹太人建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加利利地区、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带;剩下的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东区由约旦控制,西区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在1949—1967年间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败阿拉伯联军,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又成为一个社会。
1967年战争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出现,同时还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创造了一个聚合空间。这个过程是在1967年战争后的年轻一代成长时开始的,又向上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长时,约旦河西岸是在约旦统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将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并人约旦)之下,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没有感到必须持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间均已“约旦化”或“埃及化”。自约旦赋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1967年战争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取代了它们。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事实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在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组织也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一股政治力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