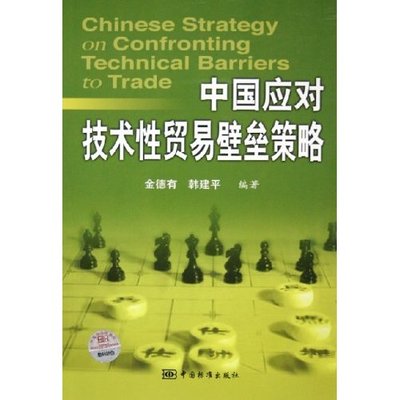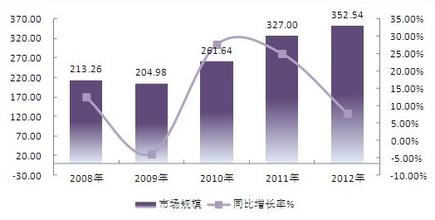伴随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思想的发展,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对社会现状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争取到了选举权,教育和就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并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一切歧视、束缚妇女的反动法律。在宪法和有关选举、劳动、教育、婚姻家庭和继承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中,都鲜明地体现了彻底的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同于实质平等,现实世界的多个领域中仍然存在着阻碍女性获得更高职位或更高薪水的无形壁垒。“玻璃天花板”现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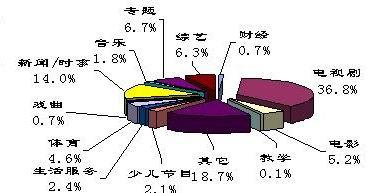
一、女性通往高层的无形壁垒——“玻璃天花板”
“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是一种比喻,指的是设置一种无形的、人为的困难,以阻碍某些有资格的人(特别是女性)在组织中上升到一定的职位。也就是说一些女性没办法晋升到企业或组织高层并非是因为她们的能力或经验不够,或是不想要其职位,而是针对女性的升迁,组织似乎设下一层障碍,这层障碍甚至有时看不到其存在。现在,“玻璃天花板”一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被用来指称处于机构顶层的女性的稀少[1]。这一针对女性的无形壁垒在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主要表现在政治、科学、经济等领域。
在政治领域,女性参政水平极低。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位女性皇帝——武则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的参政水平实现了跨越式进步,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政坛上依然存在着男强女弱的现象。根据统计,全国128位省部级四大班子领导中,有7位女性,其中五位省(市)政协主席,一位澳门立法会主席,一位省长。现任的2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一位女性[2]。656个城市中,正职女市长仅有31位。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权力资源的配置同样出现了两性失衡的局面。在农村村委会中担任村委会主任的女性仅占1%[3]。由此可见,中国女性领导在政府部门中的比例明显偏低,而且层级越高,比例越低。
在科学领域,科学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男性气质的历史,女性科学家好像一直在作为配角行走在科学领域的边缘。虽然居里夫人、梅耶夫人这样的女性科学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但这样的女性是凤毛麟角。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一直是世人所公认的最高荣誉奖项。 在它的六个奖项中,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或生理学)奖尤为引人注 目。据统计,在诺贝尔奖设立的100余年(1901年—2008年)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男性科学家有446人次,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女性科学家仅仅13人次。其中,物理学领域的女性获奖者为2人次,化学领域为3人次,生理医学领域8人次[4]。现实的这样一种尴尬反映了女性科学家在科学领域遭遇了与男性科学家不同等的待遇,她们有着和男性科学家不平等的地位。
在经济领域,女性在就业、升迁等方面机遇小于男性,下岗、失业风险却大于男性,女性就业难、升迁空间小等问题突出。甚至在一些公认的女性更为擅长的领域中,真正有所成就的还是男性居多,比如:厨师,平常做饭的大多是女性,但获得各种荣誉的名厨往往是男性;美容美发,从事这一行业的大多是女性,但取得国际国内大奖的往往是男性。这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二、无形性别壁垒成因探析(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男人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而女性则沦为男子的附属物。为了固化这样的模式,产生出与之相应的道德标准,长期的思想奴役使得女性从一出生起就要接受她是劣于男子的“第二性”的潜移默化。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如此,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更是如此。
在欧洲,对欧洲文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和反对女权的精神。《圣经》借上帝之口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痛苦,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恋慕你的丈夫,而你的丈夫要管辖着你。”[5]中世纪的僧侣哲学加深了传统的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他们不厌其烦的告诫人们肉体诱惑的危险性。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女性的屈辱地位才有所缓和。但是传统的夫权仍然保留下来。连资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预言家卢梭也认为女性是价值不大的个人。
在中国,封建礼教束缚了女性的发展:从女性政治地位来说,封建女性没有政治参与权。红颜祸水之说,使女子无论是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还是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都会遭到强烈反对;从女性经济地位来说,在封建家庭中,一切财产的支配权和家务的管理权都统一掌握在男性家长手里;从女性教育地位来说,儒家教育旨在维护男权统治,于是“理所当然”的将女子拒之门外,使女子的受教育权限遭到限制,也丧失了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只能在家中接受有别于男子的有限的教育;从传统的才德观来说,宣扬“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 从一出生就被教导不需要学习新知,只需要懂得如何取悦男人,对男子应当尊敬、崇拜和服从,依靠男子取得生存的资源等等,编织众多的理由把女人们禁锢在狭小的私人空间里,人身自由被剥夺,思想也随之惨遭禁锢,这些都成为无形壁垒产生的历史根源。
(二)路径依赖的广泛存在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在“女性上升的无形壁垒”这一问题中路径依赖存在于多个方面:
1、路径依赖决定了对男女性别群体的不同性别期待。由于女性长期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角色的缺失,使人们形成一种观点:认为女性是没有进取心和社会责任感,只能充当被看的花瓶。这种观念就形成了特定的性别期待。这种特定的性别期望把职业刻画为适合男性的,而男性也是适合于职业的,对女性的可能成就期望极低,因此在就业时对女性设置诸多门槛,或者安排女性到边缘岗位,这样就限制了女性的发展机会。2、路径依赖的存在造成了男女性别群体之间资本占有的不平等。由于民间“传男不传女”继承制度的继续存在,造成了男女家庭资本占有、教育资源占有、社会资本占有等方面的不平等。“男主外、女主内”“女人不宜抛头露面”的文化传统可能使女性自身与她们的家人很少期望她们能在社会关系上有所作为[6]。因此,女性往往对社会关系资本的占有和利用也是不够的。资源占有的劣势阻碍了女性的进一步发展,使女性的上升空间受到局限。(三)复杂的现实决定性1、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无形壁垒的继续存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整体不够高,并且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男性生理优势——体格强壮的优势影响继续存在,这就决定了实质不平等继续存在的可能。同时,男性生理强壮又是造成其心理弱势的一个诱因,他们对无论何种形式的女性的强壮都是难以接受、心生恐惧的,正像劳伦斯·迪格斯所说“男人之脆弱在于其外表之力量;女人之力量在于其外表之脆弱”。
2、家庭劳动分工的不合理也是阻碍女性上升的重要原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往往承担着繁重的、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如洗衣做饭,教育孩子等。现当代女性也参与了社会工作,但是并没有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恰恰相反,受到了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剥削,而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当家务劳动分离了大部分女性精力的同时,在工作中的能力将受到制约和限制,这也阻碍了女性的发展。
3、特定的性别教育,造成女性性别认知异化长期的男权社会的统治,形成了一套自古至今改变甚微的性别教育模式。比如:刚出生的婴儿,就根据其生殖器官的不同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玩不同的玩具,选择不同的玩伴等。给女孩往往选择红色、黄色的衣服,而给男孩选择蓝色、绿色的衣服;让女孩玩洋娃娃,却让男孩玩手枪、汽车等玩具;夸奖女孩的词语往往是“漂亮”,称赞男孩往往是“聪明”。最初的教育直接影响了男孩女孩后期性格、思维方式的形成。科学界早有定论,颜色对人的心理有直接的影响作用—红、黄色让人更热情、活泼、感性,蓝、绿色让人更沉稳、内敛、理性;而洋娃娃的选择是让女孩从小就有美的认识,为“花瓶”形象奠定基础,并且让女孩从小就开始接受母性的教育,为以后贤良淑德、相夫教子的女性形象铺路。
这样的教育模式和环境影响,使女性的自我认知也发生了异化。由于受到来自各种渠道信息的不断地、重复的灌输,女性往往就在心理上接受来自于外部的对女性的评价,并且会无意识的向那个方向靠拢,还会产生一些合评判标准的思维,比如:我是女性,我的思维就是感性的,我不适合对理性思维要求过高的职业领域;女人不工作也行;要生一定要生男孩等等荒唐可笑的想法。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女性被男权社会奴化以后,就变成了制度学派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用在“路径依赖存在”实验里的猴子,不仅完成了这一不平等观念的自我强化,还时时刻刻维护这一观念,成为这种道德标准的传播者,身体力行的给身边的孩子灌输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几代人。小孩子就是一张白纸,后天的教育、环境影响将她塑造成了人。
这些都印证了作为女性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波伏娃所说的话,“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由此可见,无形性别壁垒的产生主要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
总之,无形壁垒的存在反映了男女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地位,社会主义正义概念的中心要求——自我发展的平等权利还只是美好的理想,未能成为现实。“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是值得怀疑的,这里的“人人”不是社会所有人,只是符合道德需求的部分人。而作为女人,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经历或将要经历许多不公正,这是多方面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也是与道德公平正义原则相违背、相冲突的。男女两性之间这一伦理道德关系直接关系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打破“玻璃天花板”,帮助女性突破无形性别壁垒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