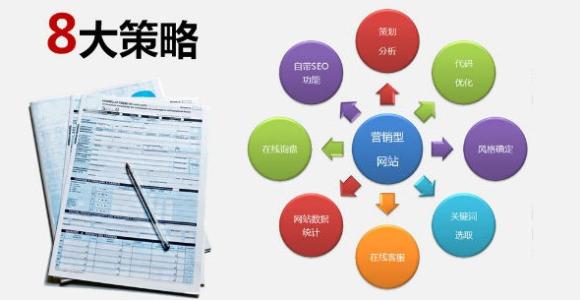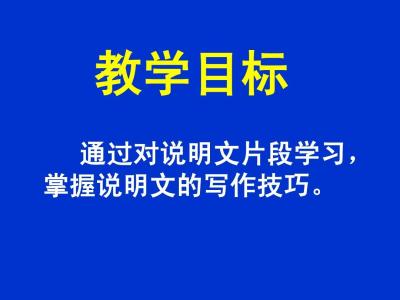演讲稿又叫演说词,它是在大会上或其他公开场合发表个人的观点、见解和主张的文稿。那么,演讲稿有什么写作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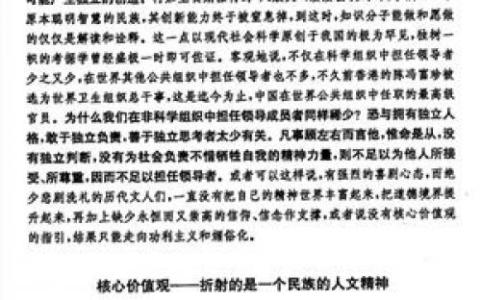
嚼面包的过程
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而一个比喻用到了滥时,它的本意也许就被忽视了。譬如“我爱读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常有人喜欢引用,到了后来才发现,对许多人而言,这不过是一时一事的语言形式而已。没有书读的时候,朝思暮想一旦有书读,又会思援弓以射鸿鹄。像如今一些自称的文学青年,一见到卡拉OK,一见到交谊舞、保龄球,就再也不知读书为何物了。把读书当成斯文的招牌,不知道饥饿为何物的人,怎么可能把书当作面包呢?
现在同学们读书的条件比我们那一代人要好得多。我18岁就去插队。“文革”之中,要想读书也是罪过。好在农民的批判能力并不那么强,也不尖锐,见到我们看书,也没有什么意见。但那些年,书源是个大问题,有什么就读什么;不像今天,想读什么就能找到什么。我记得刚开始时无书可读,竟然把一本搞来的《联共党史》读了好几遍,越读越觉得荒唐,后来终于认识到这那是一本不真实的书(或者可以称之为“秽史”),但我当时的确是以极认真的态度读那本书的。后来我看到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深有同感。那个被单独监禁了几年的犹太人好容易从看守那里偷到的一本书,竟是枯燥无味的棋谱,他并不会下棋,结果他连那种书也反复看,一看几年,逃脱纳粹魔掌后,在旅途中与人对局,竟两次把世界冠军打败了!想起我们当年在农村读书的事,我对那种文化禁锢的残酷性体会特别深。但是,这“有什么就读什么”对我而言也未必是坏事,嚼“面包”的过程和方法可能更重要。
演讲稿
现在同学们要买一本唐诗宋词,可以百般挑剔,各种选本琳琅满目,但在我们那时,根本找不到一本古典文学读物,压根儿就不出版。1972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版了,要从感情而论,这本书真让人无法喜欢,无论是观点本身还是论证的方法,都到了可笑且可憎的地步。但是当时我们几乎人手一册,因为无论如何,这本书里好歹引用了李杜的大量原作,而我们只要有原作读就行了。“文革”结束,这类书我们都扔了,因为大批好书出版了(听说这两年《李白与杜甫》反而奇货可居,可惜我们当时没有那种“文物意识”)。
那时候我把偷偷带下乡的几本小说翻烂了,一本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本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后一本书的很多细节我甚至能完整地口述出来。后来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也能复述故事的全部,因为他下乡时,手头也只有这样一本小说。还有一次,我借到一本陶菊隐先生的名著《六君子传》,爱不释手,又不得不还人,于是便反复琢磨品味,最后我几乎能把它背下来!后来我读其他人写的传记,常用这本书去作比较,眼光就厉害多了,能分辨出高下优劣。
由于书少,我那时读书几乎都记笔记。有一次看一本俄国小说《对马》,是写1905年日俄战争时对马海峡大海战的,由于没有读过相关的历史资料,我在读书时把双方舰队的情况及在整个海战中的活动整理出来,整理出来的资料,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感兴趣,但是这是我的读书经过,所以我保留了很多年。1972年以后,认识了赋闲在家的剧作家陈白尘先生,他也是太平天国史专家,借给了不少有关资料给我,我前后读了两三年,大概把他家所藏的资料全都读完了。我读的时候,整理出一百多个重要人物的活动情况,记录和摘录的本子大概有两三公斤。后来我没有专门研究历史,但是那一段读书生活养成了我搜集整理资料的一些方法。我还学会了辨析问题,比如读一本书,能分辨出优劣,判断一则史料的真伪,看出一段话是从哪本书中借过来的。总之,不因为“扑在面包上”就狼吞虎咽,品出了面包的滋味,才有兴味再去寻找面包。
我之所以对同学们说这些,是因为发现有不少同学,你一劝他读书,他就叹息,没有书读呀,不知道读什么书好呀,没有时间呀,等等,反正总有不少不读书的理由。其实能否真正把书读好,主要还在自己的需要。中国人注重形式,对读书也是如此。自古以来,读书人就喜欢给自己命名出一个书斋,要准备下多少多少书,甚至还幻想“红袖添香”,相对而言,读书本身反而不重要了。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读书的欲望,注意在读书的过程积累知识,摸索方法,一定能培养出自己的某种能力;即使起点不高,积久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风格。只知道把读书挂在嘴边,追求形式,充其量能摆个读书的功架,看起来吓人而已。当然现在可读之书要比我们那时多得多,同学们在阅读问题上不至于要走我们当年所走的那些弯路,那就更要注意阅读的效率。也有些同学过于追求读书的效果,认为读书应当立竿见影,才读了三五本书就希望作文能写好,语文考试分数上升,--持这种功利思想,把读书当成现买现卖的交易,就更不容易掌握读书的方法,难有什么实际的收获了。
所以我认为,对今天的学生而言,已经不是“扑在面包上”的时代了,要重视阅读的过程,要理智地选择阅读的内容(当然,书读得杂一点绝不是坏事),要尽可能地在阅读中培养自己辨析问题的能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