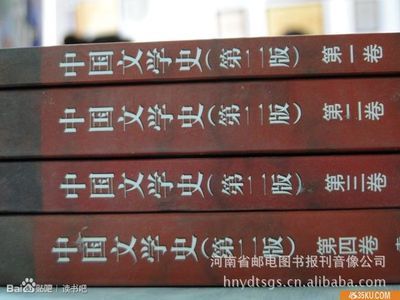一
面对发生于80年代农村的经济、文化变革,文学史可能会谈到何士光的《乡场上》,谈到从来直不起腰来的冯幺爸如何在土地承包和市场开放之后挺直了腰杆;也可能讲到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和武耕新的“壮骨法”;或者是贾平凹的《小月前本》《腊月・正月》,那些普通人在社会环境变换之中观念的冲突与变化。这些作品反映着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益处,反映着改革时代的步伐,但在这整齐划一的颂歌和凯歌中,有一个疑问是应该存在的:在那个年代,社会是否存在更尖锐、更复杂、关乎历史恩怨与现实权益的矛盾?作家们是否因此而面临着种种矛盾和困惑?
1985年,吴雪恼的《主人》②和王洲贵的《水与火的交融》③分别发表于《鸭绿江》和《朔方》;1986年,马本昌的《不平静的柳河渡》④发表于《青年作家》。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社会切实存在的题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原本被剥夺了种种权利的地主分子及其后代获得了经济、政治上的“翻身”,这种社会生活秩序的变动甚至是社会角色的互换,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在人们内心引起了怎样的波动。
《主人》中,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巴咸天蒙蒙亮就爬起来,整理好犁轭、牛缆,打算按照合同去别人的责任田里干活了。可是“冤家路窄”,雇他干活的恰恰是自己的祖辈、父辈都为之打过工的地主花提的�L孙长甲。而这个长甲,偏偏又曾在他手里犯下了“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被送去劳改过五年。原来的领导者与专政对象,如今成了雇工与雇主,生活中发生的这种变化,人们将怎样面对?在王洲贵的小说《水与火的交融》里,第一句就是:“我真的要到地主家里去当雇工吗?”发问的是原“贫协”组长王登强。王登强十七岁就给地主陈有德扛长工,后来世事大变,陈有德被打翻在地,成了专政对象,可没想到“四人帮”倒台之后,政策又变了,“地主分子全摘了帽子,成了社员、公民,和贫下中农一样了”。现如今,要从乡政府领救济款的王登强突然被陈有德的儿子陈自强邀请到自家奶牛场“工作”,去还是不去?《不平静的柳河渡》叙述的故事开始于1948年的秋天,保长秦万贵被判死刑。就在即将枪决的那一刻,他的小老婆抱着一个婴儿喊道:“当家的,给娃儿起个名再走……”秦万贵咬牙切齿地冲女人说:“勾践,这小子就叫勾践!”时光一晃就到了1985年,万元户秦勾践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去县委招待所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久,他不但迎娶了当年枪毙他爹的村长石二爷的弟媳,而且决定竞选村长。那么,一个是从前伪保长的儿子,如今的专业户万元户秦勾践,一个是老村长石二爷的侄子,如今的泥瓦匠石虎――“你说,选谁个呢?”
三部小说几乎秉持着相同的叙述逻辑与情节走向。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使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权力秩序发生了变化的话,他们的“前世恩怨”则使矛盾在所难免。
无一例外,阶级出身依然是这些小说展开故事的前提。巴咸承认,“自己家跟长甲家,确也很有一番阶级的仇恨在,虽然对方的祖辈父辈还没有把自己的祖辈父辈逼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地步,但血汗确实让他们榨干了,据阿普(爷爷)和阿爸的追忆,花提那家人对待长工短工的确下得狠心的”。陈有德也是一个厉害地主,懂农活,还亲自劳动,把长工们使得团团转。王登强记忆里,有次顶撞了陈有德,结结实实挨了两个耳光,还要磕头认罪。当然,这种阶级的仇恨也不是单方面的。土改之后,无论花提、长甲还是陈有德都成了专政对象。长甲油滑,不修人造平原,搞起地下包工队,因为“一个个发了大财,惹得全大队人眼红不已,影响极为恶劣”,于是巴咸“趁着那一股风把他卷进了班房”,一判就是五年。王登强坚信已经接受改造的陈有德“人还在,心不死”,不但时时监视,认定生产队病死的耕牛是因为陈有德投毒,而且向组织建议把他调到掏粪组,又脏又累也不可能搞什么破坏。秦勾践就更不必说,与石二爷有杀父之仇,又眼看着母亲被民兵连长侮辱之后吊死在屋檐下。由此可以看到,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阶级矛盾在具体的政治斗争里被以一种个体的、私人恩怨的方式不断激化、积累,在一个阶级的政治诉求中,相当比例地裹挟着“趋势”“眼红”等公报私仇的极端解决方式。在此,即便抛开抽象的阶级矛盾,仅凭“前世恩怨”,就足以使“两个阵营”的冲突难以化解。
同时,长甲、秦勾践们经济上的崛起与政治地位的翻身又被赋予了张狂、挑衅、阴谋诡计、伺机报复的色彩。原本只给工钱而不供饭食的长甲见是巴咸受雇,一定要亲自背了酒菜,“带着一种微妙的、主人的优越感去欣赏他的上司和往日的对头怎样屈节于钱财之下,为他挥汗效劳”;羞辱过巴咸之后更是得意地贴出“昔日世态炎凉磕头烧香总无益,今朝政策英明见官不拜又何妨”的对联。变成万元户的秦勾践不从城里调农机,硬是花高价雇人犁地,要的就是看他们“早些年一直拿勾践当猪尿泡踩,如今呢,却为几张大票子卖苦力”;他一个三十七岁的万元户,一定要娶石二爷四十四岁带着三个娃守寡的弟媳,要在柳河渡人“惊愕的、困惑的、难堪的、恼火的”目光下,把娶亲的鞭炮在石家门楼前放得惊天动地。在此,我们必须承认人在特定时机的微妙心理,但三部小说同时以近乎夸张的方式来描写长甲等人“今生得势”时的扭曲嘴脸却不仅仅是巧合。按理说,长甲等人作为新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可能更需要某种正面的描写,但因为他们阶级出身难以抹除的烙印和“变天”式的发家历程,小说显然更倾向于以道德的劣势和人格的缺陷来消解其形象,将他们从合乎国家政策顺应时代潮流的道理层面的认可推向读者情感层面的拒斥。这不但迎合阶级出身论最基本的形象预设,而且为小说最后的转折埋下了伏笔。 事实证明,三篇小说的结局完全处于意料之中。当长甲妄想以广散钱财来制造自己“庄严又慈善”的形象反被“吃大户”时,他还得去求巴咸。而这时的巴咸,不再是长甲的雇工,而是他的支书,可以帮他“上县、上州、上省”打官司。巴咸的一句话很重要:“我是这里的主人。”这是长甲必须接受的现实。王登强在陈有德的羞辱下抡起了巴掌,虽然通过调解实现了“水与火的交融”,但小说最后领奖金、穿西装、坐飞机、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只有这个当年的“贫协”组长。同样,试图以金钱贿选的秦勾践最终落败,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迈着稳健步伐走来的是石二爷:“咱村的爷们不稀罕这个,稀罕的是这里的四两肉!”――巴掌当然是拍在石二爷自己的胸膛上。
不难看出,面对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的现实状况,作家们及时地做出了反应,并且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从中也能发现作家们在处理这一系列现实经验时的摇摆、含糊,发现长期以来阶级原则至上在文学创作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发现他们对金钱与权力、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简单理解。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现,时至80年代中期,人们在那场经济秩序与权力秩序的大变革之中,在那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与价值观博弈之中,依然对一个未知的前景表现出来自政治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迟疑、期待、迷茫和焦虑。
二
三篇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评论界比较激烈的争论。《鸭绿江》连续五期开辟专栏,讨论《主人》及其反映的问题;《作品与争鸣》于1985年第6期转载了《主人》并刊发了一系列争鸣文章;《朔方》杂志于当年第7期开始组织了对《水与火的交融》的系列评论;甚至到了1987年下半年,仍然有文章就三部作品的题材问题进行着讨论。如果说作家们面对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与权力秩序的变革有意无意流露出他们的摇摆与含糊的话,那么评论家们则并不掩饰他们的态度与立场,试图通过阐释与争论使作品中的一系列问题明确起来。
如何看待农村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秩序调整和角色互换,构成了评论者们最主要的分歧。有人认为,这种让党的干部给地富分子及其后代打工的描写无疑是一笔新的“变天账”;但也有人认为,作家对这一主题的选择展示了新时期农村现实生活的一个特定场景,书写着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揭示着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
中耀在《写什么人、怎样写?――对〈主人〉的思索》⑤中说:“我看这是地道的‘反攻倒算’,虽然‘文化大革命’完全应当彻底否定,但是那时常用的‘一语泄露天机’‘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两句话用在这里是合适的。”他认为斗��地富的记忆依然在长甲身上发生着作用,这是他的“阶级根源”,文学创作要对这样的人物有足够的警惕和充分的认识:“今天,文艺界要彻底反‘左’,要‘百花齐放’,但是我们写什么样的人物?怎样写这些人物?这是每一个作者要认真思考的,象长甲这样人物,不能让他们打着‘纵横自由’的牌子为所欲为。按社会主义原则,被批判的人物始终应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与此同时,贾捷在《关于〈水与火的交融〉》⑥中认为:“他(陈自强)是一个脱离了历史并必然脱离现实社会的人。这样的人在思想上对社会发展所作的错误判断,使之变成了一个用纯粹的农民意识去占卜历史命运的预言家――他以为社会上阶级消灭了,就等于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便消失了;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而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上鼓励个体商品因素,就等于这种历史现象永恒化了。《水》把个体农民的暂时感觉当成民族的历史思维,陈自强把他的现状当成人类永恒的未来。”为此,对于长甲、陈自强、秦勾践等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形式的出现,贾捷坚信“国家企业与陈自强这种个体‘企业’之间存在一个无法抹杀的区别”,“既不能由陈自强滥用的‘现代化企业’、‘企业管理者’之类以假乱真的虚讹与国家的企业混同起来,又掩不住陈自强作为个体私有者和其父在本质上相一致的身份,更抹杀不了迟早必将消灭的他与王登强之间的雇佣关系。归结为一句话,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本身就是限定陈式个体经济恶性膨胀的辩证法则”。
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汪宗元在《悲剧的终结和喜剧的开端――读〈水与火的交融〉》⑦中以邓小平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重要依据,认为小说对变革中的农村有着真实而严峻的描写,“对过去我们曾经相信不疑的穷社会主义和坚定不移的阶级路线,作了极为客观有力的嘲讽与否定”,“王登强们为之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的穷社会主义,确实不是真正的富裕之路,这样的时代悲剧早该终结了”。田志伟在《不以一眚掩大德――简评短篇小说〈主人〉》⑧中提出要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语境中理顺这一问题,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要摈弃对历史与社会变革简单、划一的方法,更不能重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不能动不动就强调“阶级本性不改”,毕竟“极左的幽灵还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徘徊”。他对《主人》所塑造的长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同情,认为这个过去在生活中没有地位的人,如今要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手段跻身于生活主人的位置了”,虽然他的行为带有某些“新人”的特征,但他“有文化、懂科学、会管理,巧于安排,工于心计,多少有点狡猾,甚至还不得已搞点小小的欺骗”,但不能否认的是,长甲“自觉地、不自觉地促进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加速着农村中这场巨大变革的进行……从总的方向上看,他的行为是会纳入巨大的历史进程的轨迹的”。同样,李作祥的《有点酸、有点甜、有点苦、有点辣――杂议〈主人〉》⑨也积极为小说和长甲辩护,强调“地富子弟并不是地富分子”,长甲“从过去‘左’的冰层下解放出来,感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实行新政的春风温暖的时候,他当然会对过去所受的屈辱有一种激愤,有点牢骚,有点不满,甚至有点耿耿于怀,这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这反倒让人们从中“感到了时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信息”。因此,李作祥认为,“长甲对过去的骂也好,对现在的喜也好,对巴咸的某种盛气凌人也好,都是对我们当前农村大变动的一种赞颂,是对党的新政的一种赞颂”。
无论是立场的水火不容,还是行文中剑拔弩张的情绪与口气,都使这些争论弥漫着十足的火药味。它不似后来学术讨论的温文尔雅,也没有多少就事论事的界限,各方都在毫不含糊地甚至是急匆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因而更像是两个阵营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着当时评论界、知识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格外敏感。其实从这些评论文章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言说已然脱离了小说本身,让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人们于当时的情境应该如何看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的变革及其带来的不仅仅局限于农村的社会经济、权力秩序的新变化和新格局,而对小说如何讲述了这些新的问题与矛盾并不是十分关心。这甚至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联想,似乎是两个厉兵秣马的军团早已按捺不住,焦虑地等待着某个恰当的时机或者导火索,而在这个时候,三部小说的出现恰恰制造了这个关键的契机,至于之后的纷争,可能就与它没有多大干系了。然而这些联想并不完全是错觉,有关三部小说的争论几乎涉及到新时期以来知识界所要清理的一些重要问题,它向前反思几十年来中国革命及社会改造的得失,向后讨论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机遇中如何推进改革,着眼当下则关心着公民、法律、权利等一系列问题。 于此就不能忽�1983年的文学境遇。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往往是直接干预生活,它以文艺的方式“拨乱反正”之后继续关注社会改革。它固然因此使得文学为全社会所关注,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光彩,但就文学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完全正常。尤其是在那样一个阶段,离政治太近往往也就为其所累,政治上的一点风吹草动,文学状况就会大受影响。1983年上半年对《苦恋》等一系列作品的批判、下半年对诗歌界“三崛起”的批判、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让一些作家受到严厉批评,虽然严峻的态势很快结束,但对文艺界影响很大。就当时的情况看,文学好像无法继续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了。那么,文学应该如何继续就成了摆在许多作家面前的问题。虽然现代主义同样受到了冲击,但坎坷之后,似乎这样一种“超越政治、淡化现实”另起炉灶式的创作之路在1983年一连串的事件过后就成为文学唯一可能的出口。在介入现实或者说追求“写什么”的创作与当时的社会氛围发生了紧张关系的时刻,回避“写什么”而尝试着“怎么写”的一批青年作家可以说十分偶然地获得了一个破土而出的机会。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存在着一个显性的“1985”和一个隐性的“1985”。前者当然是在文学史中被迅速经典化的先锋文学等,后者则是从70年代末延续过来的文艺政策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显性的“1985”作为80年代一种不安分的文化力量,固然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紧贴政治的写作思路构成了强有力的消解,对更早的文艺规范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后来在心有余悸的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一整套的80年代情结和话语合作中,在特定情感期待和理性与价值选择下,自然而然地分享了对80年代理想化的叙述果实。但是,从隐性的“1985”所呈现出的8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冲突来看,显性的“1985”无疑是回避了当时激烈的文化对垒与现实的经济、政治矛盾,一方面是被1983年以来的文艺状况所迫,另一方面也是顺水推舟地走向了一个所谓“去政治化”的新领地。而作为隐性的“1985”,它对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矛盾的反映与挖掘在被一种更新潮的文学潮流所掩盖的同时,也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继续深入和拓展。虽然寻根运动、先锋文学、民俗市井小说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但在隐性的“1985”止步的地方,被文学提取的那些现实矛盾愈演愈烈,而这一切也在之后1987年1月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动中得到了印证,甚至直到今天,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时常使不断推进的时代肌体隐隐作痛。
三篇小说及其引发的争论如今已被人们遗忘,但它的存在却证明着一个隐性的“1985”,证明着历史的复杂与多面,证明着一个风光无限的文学潮流背后隐匿的坎坷之路,证明着文学史叙述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既有的文学史叙述在此不断显示着它的傲慢,它可能来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整,来自文学史叙述在一个“新潮滚滚”的时代处理此类问题的难度,甚至仅仅来自文学史叙述者单纯的审美偏好。因此,这些作品与争论的价值可能并不完全存在于它们自身,而是为之后还原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与历史场景提供了重要参照,映衬着时代荣耀背后的江湖险恶,呈现出文学转折期与新局势下历史的惯性与持续的意识形态纷争。
【注释】
①吴亮、程德培选编:《新小说在1985年》,1、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②吴雪恼:《主人》,载《鸭绿江》1985年第1期。
③王洲贵:《水与火的交融》,载《朔方》1985年第3期。
④马本昌:《不平静的柳河渡》,载《青年作家》1986年第4期。
⑤中耀:《写什么人、怎样写?――对〈主人〉的思索》,载《鸭绿江》1985年第3期。
⑥贾捷:《关于〈水与火的交融〉》,载《朔方》1985年第7期。
⑦汪宗元:《悲剧的终结和喜剧的开端――读〈水与火的交融〉》,载《朔方》1985年第7期。
⑧田志伟:《不以一眚掩大德――简评短篇小说〈主人〉》,载《鸭绿江》1985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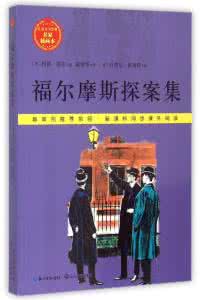
⑨李作祥:《有点酸、有点甜、有点苦、有点辣――杂议〈主人〉》,载《鸭绿江》1985年第3期。
⑩李书磊:《新生活新主人――〈主人〉读后漫笔》,载《鸭绿江》1985年第7期。
11熊笃诚:《现实与思索――为〈主人〉辩》,载《鸭绿江》1985年第6期。
12张有仁:《荡荡君子意 拳拳小人心――读〈主人〉,话巴咸》,载《鸭绿江》1985年第5期。
13李作祥:《有点酸、有点甜、有点苦、有点辣――杂议〈主人〉》,载《鸭绿江》1985年第3期。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