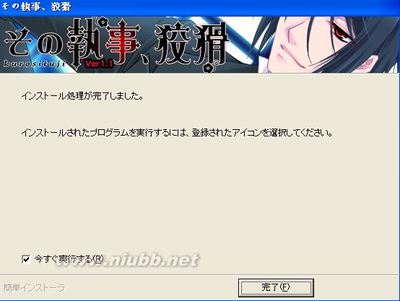生于3月,死于3月,卧轨,谈了四个女友无疾而终,写诗,崇拜太阳,玩过气功,这些还不够,海子是写了“我有一间屋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个 人。这是他的名片,正如“I have a dream”是马丁·路德·金的名片,“哪管洪水滔天”是路易十四的名片,“自由,多少罪行假汝之名”是罗兰夫人的名片一样。
房地产商拿 “春暖花开”做文案,国产文艺片里的少男少女争相吟诵“春暖花开”,证明了理想主义的折翅,它没了本质,剩了一个logo。海子的理想主义属于1.0版 本,目前,那些还未更新自己的系统的人大概只能遁迹乡野或躲进深山。在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身上寻找商机是合法的。假如有人在山海关兜售海子卧轨时带的四本 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并不会被视作亵渎诗人的行为——你去看个教堂不还得买点十字架挂件?你排队请明星签名后把东西拿去拍卖,是遵循市场经济“价高者得”的原则,没人能指控你不是出于真爱而收藏一样留有名人痕迹的器物。
让海子被更多人所知、所崇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于1989年3月26日的死。人的大脑有个常见的思维误区,就是前后脚发生的事之间有因果关系,像“我老婆是我充50元话费送 的”之类的段子都是利用这一误区编的。他的死导致朦胧诗的终结;他的死宣告了“文化热”寿终正寝,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着手一统江湖。海子自杀之日的特殊 性,使人忍不住要把他封圣,要么是先知,要么是殉道者,像安徒生的天鹅,像王尔德的夜莺。一些老派的评论家,比如朱大可,用了从“文化热”时期汲取来的一 些宗教术语,嘉封海子为有宗教情怀的诗人,为了一种精神而壮烈献身。对这些人来说,“纪念海子”等于是高举异见的大旗。
西川,海子的同行和忠实友人,很清楚从纪念到消费只有一步之遥。他把对海子之死的评价收拢在括弧里:“关于他的自杀,我一直不愿意说得太多。在我看来,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有资 格去谈论他们的死亡的(我们顶多只能谈谈我们对自己的死亡的猜测),而一个握有死亡这枚大印的人,甚至可以蔑视恺撒这样的强权。”“蔑视”是海子自己的事,扯一张海子的肖像做成旗帜,举着四处张扬的,就是在利用他了。
有幸认识两个在九十年代初读大学的不幸的人,他们在远赴山区长途拉练途中都带着油印和手抄的海子诗作,那时“地下”、“民间”都还是带有些许神圣的词。什么样的心境读出怎样的诗,海子的句子对他们而言都是有关逃离与超脱的呼 唤:“我觉得自己像尸体一样飞翔/也已经将五脏倒入这路途”,“我们一同登程/那时风和日丽高原万里无云”,“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在强制性的苦旅之中宽慰人心,这个时候的诗是最了不起的。
诗人和批评家联手为海子制造神话,一个胡子拉碴、戴着眼镜、两臂伸成V字扑向天空与太阳的诗人、殉道者。也许海子神话寄托了一些人的幻灭感,对消费社会的隐晦批判,对诗歌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化的哀悯。他们暗中为 海子设置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集合所有文人之力也无法撼动,反过来,只能合作或加入的敌人。但是,这个敌人也不把海子当作塞尔维特、布鲁诺或其他异端分 子,必欲除之后快。政府主导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看上了他,要把他纳入自己的版图。
那本创下了销售奇迹、正版被盗版彻底淹没的《中国可以说不》,声称要吸纳一切能维系“龙魂”的卓越的中国文化产品,来同霸权主义的美帝对抗。它的主力作者还攒了另一本知名度略逊的书《第四代人的精神》,其中有 一篇文章叫“春天,无数个海子”,当然,这是从海子那首名诗化过来的: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为了什么?
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
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
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
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
它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
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
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十个海子全部复活”,这个意象指向了万物生长的感觉,“低低地怒吼”作意气风发状;随后从高调进入沉吟,海子成了“野蛮而悲伤”的“最后一个”,仍然沉浸在冬天、黑夜、死亡里面,蜷缩在乡村,谷物成堆的农舍里,不知道“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个孤独的“海子”,到了“说不”诸公的笔下却成了星火燎原的象征,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在我的故乡,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大雪山周围,有无数繁星般闪烁的海子,实际上就是很小的涌泉和湖泊。它们慢慢从地底渗出,或是由阳光溶化的雪水流积而成,此后满溢、汇流,成为小溪,在向下流淌中又汇聚成小河、中等程度的河流,最后形成著名的黄河和长江。”
对于启蒙派、自由主义派和地下诗人们而言,“十个海子全部复活”意味着“变天”——今天我们说的“逆袭”,海子以身殉道,又像耶稣一样在春天翩然而至,“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 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西川语)但在大声疾呼民族精神的“说不”者们眼里,“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却仿佛“千万个雷锋站起来”的意思。
两种人都在消费海子,跟在他们之后的是房地产商。在被传播和被挪用之中,海子的诗经历了一个被简单化——如果不说是庸俗化的话——的过程,他和大自己六十多岁的徐志摩被放在了同一个篮子里,变成了一枚英年早逝、浪漫至极的符号。
这 两天,又见人叹息“又到了消费海子的时候”了。我却没那么悲观。海子其实比其他八十年代走红的诗人都更容易去政治化(或去刑事化)。1995年的公开出版 物《海子的诗》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海子走出了地下状态,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六年之后,官方还嘉奖了他一个人民文学诗歌奖,他的诗被采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这 个时候,助推海子成名的“地下诗歌”概念已经趋向失效了,“地下”和“地上”的对立关系在不知不觉地消散,十年前那些远走西土,靠着基金会接济度日,时而忙着更换丈母娘的诗人们,十年后都陆续得到了大陆高校或其他研究机构的教职。感慨诗歌被边缘化、怀思理想主义1.0版的任务,身为“有机知识分子”的他们担任起来有点尴尬,也不太顺手。
一些早早下海的前诗人,后来绕开出版管制,把钱投入到了诗歌出版和组织诗歌活动之中,让诗歌的曝光率升高,尽管读者的数量一直在下滑。市场经济确实把海子变成了符号,不过,它如果想为诗歌做点什么,也就是做到这一步了。“汉语写作”这一文化概念一直在扩大它的 疆域,这才是海子应有的归宿:母语。让一个文人成为世界公民的,不是浪迹天涯,也不是他的死,而是一张有地方色彩的名片。比起理想主义者、爱国诗人、朦胧派还有“诗人—殉道者”,海子更应该是“汉语诗人”,他拓展了汉语书写的边界,他使用的语词和意象扩大了汉语表达的可能性。
一个好现象:有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诗是用来享受的。读诗的人不必为了如何阐释一首诗、如何衡量一个诗人的地位而争斗,一首诗,有一两句话能打动你,就是好诗。海子的诗有一 大半都是如此。周云蓬改的《九月》,有一度我每天要听个两遍,理想主义的1.0版,不再是“只身打马过草原”这么一个孤寂的形象。(作者:云也退)
-------------------------------------------------------------------------------------------------------------
编 者注:前天(3月26日)是诗人海子去世25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海子诞辰50周年。25年前,25岁的诗人海子躺在铁轨上,远处阳光刺眼……他把“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的梦想留给了后人。海子的死曾被过多阐释,值此,更多的人选择无声但充满诗意的悼念。诗人麦冬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海子,晚安,春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