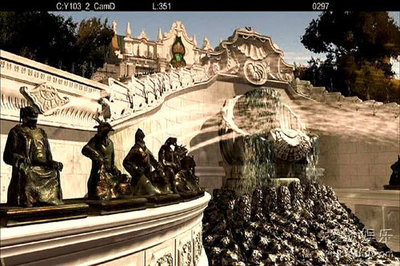四
苏东坡与赤壁的因缘是这样的: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初到黄州的苏东坡,在儿子苏迈的陪伴下第一次奔向赤壁。对于此行在文学史乃至艺术史上的意义,或许连他自己也未必了然。那时,他只将这行当作一次普通的造访,他后来在给辩才和尚的信中写道:“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上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天,云涛际天……”
尽管此后,苏东坡常常来此,然而,到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写下流传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那块石头才真正与人的血肉筋脉相连。
公元1082年,“七月既望”,苏东坡不知第几次前去朝拜赤壁。那一晚,这位名义上的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的职业农民,结交了几位友人,乘月泛舟,前往赤壁。那一次的同游者,有一位是四川绵竹武都山的道士,名叫杨世昌,他云游庐山,又专程转道黄州看望苏东坡。他善吹洞箫,《前赤壁赋》说: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这吹洞箫者,指的就是杨世昌。
那一晚,人世间的所有嚣嚷都退场了,他们的视野里,只剩下了月色水光,还有临江独立的赤壁。此时,在江风的呼吸里,在明月的注视下,对人世的所有愁怨,不仅多余,更杀风景。当年的战阵森严,马嘶弓鸣,都早已被这无尽的江水稀释了,化为一片虚无,连横槊赋诗的曹操、羽扇纶巾的孔明、雄姿英发的周瑜,都连一粒渣也不剩了。
不久前,他在这里写下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词,在中国几乎人人会背: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
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
苏格拉底说:“未被反省的生活是无意义的生活。”天高地远的黄州,使得在政治绞杀疲于奔命的苏东坡有了一个喘息和自省的机会。长风的呼吸中,他第一次松驰下来。面对赤壁,面对那些转眼成空的所谓基业,苏东坡对自己从政的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报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对功业的欲望与渴求,而那个被他报效的朝廷,却始终拒绝任何改变。到头来,改变的只有苏东坡自己,在小人堆里穿梭,在文字狱里出生入死,人到中年,就已经白发苍茫。
我想起周扬先生在“文革”之后开过的一句玩笑:“你不断地去干预政治,那么政治也就要干预你,你干预他他可以不理,他干预你一下你就会受不了。”
在黄州,苏东坡给李端书写信。他说: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那时的他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虽与王安石政见相左,骨子里却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患上了“圣人病”,觉得自己就是那根可以撬动地球的杠杆,但他看到的,却是一根根的杠杆接连报废,连他的恩师欧阳修,历经忧患之后,头发已经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个,眼睛也几近失明,自况“弱胫零丁,兀如槁木”,出知亳州、蔡州后,以体弱为由,不止一次地自请退休,从此不再在政坛上露面。而自己,自以为才大无边,最终却几乎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政治的荒谬,让那些在儒家经典的教唆下成长起来的书生陷入彻底的尴尬:他们想做天大的事,却连屁大的事也做不成。因此,在苏东坡看来,自己一根筋似地为皇帝写谏书,全是扯淡。他以为话多是一个优点,以为话多就可以改变世界,但他所有的辞语,要么在人间蒸发了,要么变成利簇,反射到自己身上,让自己遍体鳞伤,体无完肤。
在赤壁,由奏折,策论,攻讦,辩解所编织成的语言密度,被空旷的江风所稀释。在去除语言之后,世界显得格外空旷和透明。
在这样的时间纵深里,那些困扰他的现实问题,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时间带走了很多事物,谁也阻拦不住。
五
他明白了,比铭刻的文字更沉着,也更有力量的,是石头自身。
它不需要镌刻,不需要政治权威的界定,因为那石头,本身就是超越了文字的纪念碑。
就像他《咏怪石》诗里曾经描述过的当年疏竹轩前的那方怪石,丑得无法雕刻,百无一用,没想到那石头不服,来到苏东坡梦中,阐明自己的价值:“或在骊山拒强秦,万牛汗喘力莫牵。或从扬州感庐老,代我问答多雄篇。”庐老,是指唐代诗人庐仝,写过许多关于石的诗,像《客赠石》《石让竹》《石答竹》《石请客》等,因此才被那方怪石引为“知己”。
它告诉苏东坡:“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以是赠子岂不伟,何必责我区区焉。” 意思是,它完全可以作为气节与人格的象征,又何必以区区琐细之事相责呢?
这让我想起贾平凹散文里的那方“丑石”:“它不是一般的顽石,当然不能去做墙,做台阶,不能去雕刻,捶布。它不是做这些玩意儿的,所以常常就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这让贾平凹从丑中看到了美,“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
透过赤壁,他看到的不只是历史,而是天高地广,是有限中的无限。
《赤壁赋》里,苏东坡慨然写道: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苏东坡将此称为“无尽藏”。他想要什么,都可以随时来取。
比朝廷给予他的多得多。
终于,他学会了区分生命的有意义和无意义。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因此,他不再受所谓理想的骗。他既不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也不像这世上不得志的文人那样看破红尘,以世外桃源来安慰自己。他爱儒,爱道,也爱佛。最终,他把它们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既不远离红尘,也不拼命往官场里钻。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他无论当多么小的官,他都不会丧失内心的温暖。他灭蝗,抗洪,修苏堤,救孤儿,权力所及的事,他从不错过,他甚至写了《猪肉颂》,为不知猪肉可食的黄州人发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横流的东坡肉。它的烹食要领是:五花肉的肉质瘦而不柴、肥而不腻,以肉层不脱落的部位为佳;用酒代替水烧肉,不但去除腥味,而且能使肉质酥软无比……
他不再像范仲淹那样先忧后乐,而是忧中有乐,且忧且乐,忧乐并举,乐以忘忧。
他已无须笑傲江湖,因为他已笑傲时间,笑傲历史。
像李敬泽笔下的张良,在那个夜晚,他“痛彻地感受着历史的宏伟壮阔和生命的微渺脆弱,那时他可能真的情愿物化黄石,超然于时间之外,看云起日落”。
当年赤壁大战的三个主角,在历史中各得其所——周公瑾爱情事业双丰收,曹孟德(后代)得了天下,诸葛亮则全了人格。
所以,相比之下,他更爱诸葛亮。
此时的苏东坡,早已“尘满面,鬓如霜”。每当日暮时分,他从东坡的农田荷锄回家,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东坡都泰然自处,有时还跟着他们开玩笑。
还有一次,他跑到夜店里喝酒,被一个流氓一样的人撞倒在地,他气得想骂那人,但爬起来后,他竟然笑了。后来他在给友人马梦得的信里讲了这件事,说“自喜渐不为人识”,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这并不令他感到沮丧,而是令人感到高兴。
“自喜渐不为人识”的卑微感,是与“天下谁人不认君”的狂傲绝然相反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更强大的自信。艺术史家蒋勋曾把这句话写下来,贴在墙上。他认为“自喜渐不为人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态,“不是别人不认识你,而是你自己相信你其实不需要被别人认识”。
那时的苏东坡,已经从忧怨与激愤中走出来,走进一个更加宽广、温暖、亲切、平坦的人生境界里。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微渺、坦荡、绵长。
那是一种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像海明威所说,对于一切厄运,都要“勇敢而有风度地忍受”。
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他貌似草芥,却不是草芥,而是一块冥顽不化的石头,被遗弃在荒野上,听蝉噪蛙鸣、风声鸟声,看日月流转、人事纷纷。
历史如江河,汇流在赤壁前。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与辽阔。
六
无论苏东坡是否画过赤壁,赤壁这块非同寻常的石头,被苏东坡“开光”以后,竟然成为后代书法家和画家反复表达的经典形象。
在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我们仍然可以目睹这样一些著名的法书:南宋赵构草书《后赤壁赋》,元代赵孟頫的行书长卷《前后赤壁赋》,文徵明61岁书《前赤壁赋卷》、78岁书《前赤壁赋卷》、89岁书《前后赤壁赋》,明代祝允明草书《前后赤壁赋》……
绘画方面,至少从南宋马和之开始,画家们就开始痴迷于这一题材的绘画创作。用巫鸿先生话说,“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激发了视觉艺术表现中的‘赤壁图’传统”。所谓“赤壁图”,一般包括两类构图。其中一类是多联的卷轴画,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女使箴图》《洛神赋图》那样,把苏东坡的文本转译成一个连续的叙事;另一种是单幅绘画,聚集于苏东坡泛舟赤壁下的时刻。
好玩的是,苏东坡看不上眼的院体画家,也就是宫廷专业画家也来凑热闹,加入这场宏大的视觉叙事中,马和之,就是南宋宫廷画院中官品最高的画师。院体画非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受到刺激而益发蓬勃。新的精神渗入到院体画中,像日光刺透寒林,让它变得强韧和尖锐。那新的精神,就是挣扎与反抗,用徐复观先生话说,就是“在顺应画院的传统中,更含有强烈的反画院的精神”。在歌功颂德的背后,“他们在大小环境的压迫感中,有他们的人格上的挣扎,有他们在精神自由解放中所建立的另一形式”,有缤纷华丽背后的浩大苍凉。
苏东坡是看碑者,是解读赤壁的那个人,有朝一日,他自己也成了古碑,成了赤壁,被后人追怀和讲述。马和之之后,南宋李嵩、乔仲常,金代武元直,明代仇英等都画过《赤壁图》。其中仇英,至少有三幅《赤壁图》存世,一藏辽宁省博物馆,一藏上海博物馆,一律绢本短卷,画面上断岸千尺,白露横江,东坡与客泛舟中流。还有一卷是纸本,略长于前两卷,增加了苇汀浅屿、石桥曲涧、秋林霜浓、云房窅深的夜间景色,2007年在嘉德公司秋拍会上创造了当时中国绘画拍卖成交价的世界纪录,以7952万元人民币成交,也使中国绘画作品的拍卖成交价首次超过1000万美元级别。
《赤壁图》的传统,一直渗透到20世纪。1941年,张大千初到敦煌,就画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两件画轴。74年后(2015年),亦成为嘉德的拍品。《前赤壁赋》轴采用倪瓒的一江两岸式构图,但视角却是从赤壁俯瞰的,这个视角,在以往的赤壁赋图中极为少见(一般以赤壁为背景),赤壁之下,江天幽远,一叶扁舟在水面上飘浮,苏东坡与两位友人,安闲地坐在舟中,饮酒欢叙,陶醉于清风明月、江天美景中。《后赤壁赋》轴构图更加奇特,赤壁从画轴的左侧突然穿入,呈头重脚轻的倒三角结构,危崖顶上还站着一个人,那人就是苏东坡。他居高临下,怅望远方,而舟中的伙伴,全都抬头仰望着他,似乎暗示着,他看风景的同时,他自己正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于是,在赤壁原有的空间之外,画家们又开辟了一重重全新的空间。图像的空间,从此覆盖了物质化的空间。从后来的绘画史中,我们“目睹”的,既不是三国鏖兵的“武赤壁”,也不是苏东坡的“文赤壁”,而是画家们创造出来的“画赤壁”。由此,我们发现了记忆在这块顽石上的反复涂抹与叠加。赤壁于是成了一块容积无限的石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尽藏”。为了表明这一点,画家们不约而同地夸大了赤壁的体积,它挺拔、高峻、陡峭。在无限的江水和时间中,苏东坡的身影,还有那一叶扁舟,都显得那么微小,像他笔下的“千古风流人物”一样,渐行渐远。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