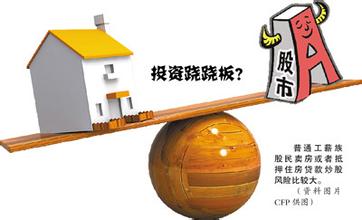(文/Dr. Jennifer Harman)
“解脱”,一次又一次地,我从生活里听见这个词,但却一直无法理解它的正确含义。我的朋友达芙妮,在电话里结束了她的异地恋。她告诉我她为了“解脱”,横跨了大西洋从纽约飞去伦敦,找到前男友当面把话说清楚。然而即使见了面,她却仍然无法释怀,并不觉得事情真的结束了。在面对我自己过去的一段感情时,我也一直在纠结解脱的含义。为了对那个人死心,10年间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也尝试过种种方法,从写下长文论述为什么我们的感情没有走到最后,到亲身与他讨论——这都是为了能与他做最终的告别,然后转身离开。
因为所尝试的方法都没有奏效,我开始努力查找的心理学研究,试图对“解脱”的含义有更好的了解。令人失望的是,并没有太多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解脱”这个词从来没有被真正下过定义【1】。我找到过一篇调查感情破裂的论文研究。研究者采访了一部分正在经历失恋的女性。当被问到如何描述解脱时,她们将之形容为一种能理解为何感情会破裂、不再感到依恋或痛苦的状态【1】。而这这恰恰也是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但还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困惑不已:为了减轻痛苦和对前任的依恋,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深究这段感情到底为什么会曲终人散?

我把目光投向社会心理学领域,试图寻求答案。依恋理论者主张只有在消除了对过往恋人那份模糊不清的情感时,才能得到解脱【2】。当一段感情终结时,人们最先会有抵触情绪,之后是绝望,最后认同并离开【3】。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改变“自我概念”来摆脱旧恋的羁绊。加里·莱万多斯基(Gary Lewandowski)博士研究过失恋时人们如何改变自我认知。他发现,我们在感情中的“自我扩张”得越多,即因亲密关系造成的自我概念加深得越多,在感情结束时我们失去的自我就越多【4】。从依恋的角度来讲,恋人都会因为对方而改变自己,而“解脱”正意味着还原这些改变,消除或远离恋爱状态时的“自我”。比如,在我和那个人相恋时,我们都喜欢一起听Coldplay乐队的歌。他们的歌曲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我们的感情。然而在分手后,听Coldplay的任何歌对我来说都是煎熬,失去恋人的痛苦刻苦铭心。我要么选择回避音乐,要么选择听着音乐思念他,无论哪一种做法,都真的称不上是解脱。
对解脱的需求【5】是一项从基础知觉研究中借用过来、并应用到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主张人们寻求解脱的目的是为了以更简单化的方式来感知人际世界。换句话说,渴望解脱的人,他们期待得到关于生活和恋爱中,更简单、直接、明确的答案(比如我需要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分手)。虽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需要解脱,但是也有人能在一份感情行将逝去时做出更迅速、更果断的决定【6】。研究者发现,当一个人想要得到解脱,却又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时,他就会陷入较差的心理健康状态(例如抑郁症)【7】。我想这可以解释为何当初那几年我努力想要忘记那个人却终究无法放手释怀,为何达芙妮跨越了整个半球却依然解不开心结。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怀疑,通过抹去上一段恋爱的记忆和感情来寻求解脱,是否真的可行,又是否健康?
有些治疗师把解脱看成是不可达到的理想化状态。诚然,有很多人都经历着重负的失落,这种失落含糊不清却又无休无止。治疗师的建议是,与其去寻求不可能达到的解脱,倒不如去寻找这其中的意义,就算无论怎么做,都不会有“终点”一说【8】。所以,就算不知道“为什么”感情就断了,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并不非得知道所有答案,与其追根刨底,不如坦然接受。这种态度能够促进更深层次的个人成长,因为它可以提升我们对于负面情绪或不确定因素的容忍能力【9】。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弄清每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所有原因,然而坦然地接受事实、面对事实(即使有时候这十分艰难),能使我们能更轻松地对待生命中的其他不确定因素。
所以,如果真正的解脱并不存在,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法也许便是调整自己对那份悲伤和失落的预期。想一想失去的这段感情意义何在,肯定这段感情的重要性,再之后,要做的便是去追寻成长,追寻其他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和感情。当我终于立下决心,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途时,我遇到了我新的爱人。曾经对“解脱”的需求至此几乎消弭无形。我是否还爱着之前那个人?当然,我们的感情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是否爱着我新的爱人?当然,每一天都爱。我想,这就是解脱的含义吧。至少,对我而言是的。
参考文献:Wilson, T. A. (2009). The experience of closure defined by women after the loss of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9, pp. 7156.Mikulincer, M. (1997). Adult attachment style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uriosity and cognitive clo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1217-1230.Bowlby, J., & Parkes, C. M. (1970). Separation and loss within the family. In E. J. Anthony (Ed.), The child in his family (pp. 197–216). New York: Wiley.Lewandowski, G. W. Jr., Aron, A., Bassis, S., & Kunak, J. (2006). Losing a self-expanding relationship: Implications for the self-concept.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3, 317-331.Webster, D. M., & Kruglanski, A. W. (199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1049-1062.Roets, A., & Van Hiel, A. (2008). Why some hate to dillydally and others do not: The arousal-invoking capacity of decision-making for low and high-scoring need for closure individuals. Social Cognition, 26, 333–346.Roets, A., & Soetens, B. (2010). Need and ability to achieve closure: Relationships with symptoms of psychopatholog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8, 155-160.Boss, P., & Carnes, D. (2012). The myth of closure. Family Process, 51, 456-469. Melnick, J., & Roos, S. (2007). The myth of closure. Gestalt Review, 11, 90-107.编译自:“I Need Closure!” Why It Is Not Possible To Get It. Science of Relationships原创人员:Dr. Jennifer Harman文章题图:downwardspiralintothevortex.com
本文由 Science of Relationships 独家授权果壳网(guokr.com)编译发表,严禁转载。
Copyright ? 2013, www.scienceofrelationship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A production of Dr. L Industries, LLC.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