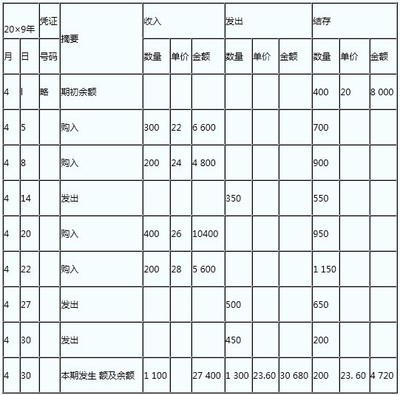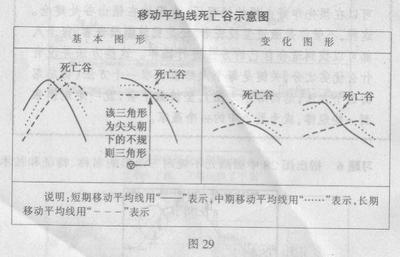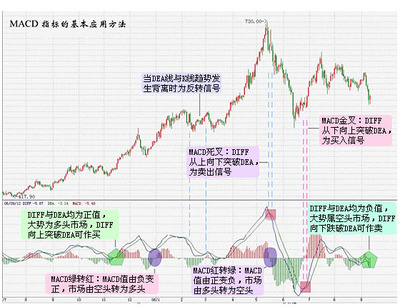摘 要:1950年代茅盾的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双语”“复调”色彩,在趋从时代文化主潮与权力话语的基础上,在既定文学规范的框架内,对种种肆意践踏文学本质的行为作了竭尽所能的质疑与修正。茅盾文学批评的话语修辞不仅体现了一代文豪在泛政治化语境中,竭力维持文学发展命脉的良苦用心,更淋漓尽致地展露了政治高压与话语霸权对人的自由精神与高贵心灵的折损。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茅盾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主要在1949年以前。新文学初期,茅盾作为“人生派”最有实力的批评家,“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是他批评的基点与归宿,这种社会功利性的批评理路奠定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石。左翼文学时期,茅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注重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社会意义作“本质”性的抽绎与定位,确立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典范。建国后,茅盾身兼文化部门多个要职,全心全意地宣传党的文化政策,自觉维护“政治—文学”“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与规范。然而,根深蒂固的文学自觉意识和潜在的主体化批评经验,使他竭尽所能地维持着文学的发展命脉,在他大量趋从时代主权话语的批评文本中,满贮着对新中国文学的深厚关切与忧虑。与黄金时期相比,解放后茅盾的文学批评也许缺乏个性与卓见,却十分难能可贵,“具有耐人寻味的历史内容和研究价值”。本文以茅盾1950年代的文学批评为中心,力图从一个侧面探寻在时代强权话语的裹胁下,一代文豪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并进而透视政治高压与主权话语对人的自由精神与高贵心灵的折磨与销损。
一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者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会议确立了新中国文学的根本发展方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文学的“共同纲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根本方向。文学作品是政治、伦理教育的形象性手段和工具。作家的政治立场、世界观的正确与否,是创作成败的关键。题材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表现重大政治运动是主要目标。乐观的理想主义和明朗确定的表达方式是标准的风格。虚构的“工农兵读者的”反应是批评的最主要根据。高度政治化、组织化是当代文学的显著特征。“文学批评不再是一种讲究科学性并富于个性特征的创造性活动,而是直接体现政治意图、维护规范,径直对文学现象予以‘裁定’、‘定性’的工具。”
应和着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开国气象,茅盾相信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自己始终倡导的现实主义以及自己大半生追求的人民解放事业是一脉相承的。他自豪地宣称:1950年代是“人民的世纪”,“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至于如何塑造工农兵的高大形象,茅盾的话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特有激情和关于美好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今天我们写工农兵,就一定要写他们正像初升的太阳面向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情绪高昂,精力旺盛,充满自信,我们一定要在作品中把它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这赫然是茅盾的严明选择,也是当时文学批评的风向标。然而问题接踵而至,艺术性与政治性、真实性与典型性、思想性与目的性、个性与党性、典型化与概念化等等纠缠不清的问题不断困扰着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很少在学理范围内自由展开,往往由高层领导的权威话语最后裁定,若有不同意见,种种“帽子”便纷纷扣压下来,轻则思想落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重则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右倾、反党、反社会主义。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使茅盾自觉与权力话语保持一致。那些大而无当、空洞乏味之词在他1950年代的批评文本中随处可见。如关于“写真实”的问题,始于延安文学的只能“歌颂”不能“暴露”的传统在建国后畸形发展,被推至极端。茅盾亦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写真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艺术的真实,就是生活中本质的东西。……这一片光明的气象,就是我们生活中本质的东西”。若表现生活中的“阴暗”就是对新中国心存不满,是仇视社会主义。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公式:真实=生活的本质=光明,这种对现实生活片面化、简约化理解正是当时的主流导向。面对公式化概念化泛滥,茅盾讳言党对文艺的专制领导以及教条主义批评对文学的束缚与伤害,只一味强调作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学习马列主义,深入生活,加强艺术实践,三者反复进行,是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不二法门。”由于对文艺“大跃进”的盲目趋从,他甚至认为“《红旗歌谣》三百首就比《诗经》强”。如何使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结合,茅盾在几千字的长文中绕来绕去,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最后只好以流行口号草草收场:“我以为学会两个主义的结合的问题,也就是加深马列主义修养、培养共产主义风格的问题,也就是要善于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的问题。”在批判胡适、胡风、丁玲、冯雪峰、反右等运动中,他先后写了《良好的开端》《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改造思想》等应景表态文章,并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体”特征与“修辞”风格。
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路》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引起热烈讨论。茅盾以五十余万字的长文《夜读偶记》参与谈论。这是茅盾1950年代篇幅最长、最富于学理性的批评文章,可惜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夜读偶记》显示了茅盾作为“资深”批评家的丰厚学识与清明理性。文章秉承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宏阔视野与基本方式,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立场,疏理了中西文学的发展脉络,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发生、发展做了他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的阐释,其中的精见卓识如暗夜的繁星,熠熠生辉。如:对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言文分离原因的考察、从韩愈到李梦阳的文学革新运动的意义与局限的分析、对“历史的局限性”与“艺术的特殊性”的看法以及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深入剖析、对西方古典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进步意义的肯定等等,这些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不刊之论。然而,茅盾终究难脱时代文化思潮的窠臼与长期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简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把今日中国文学(包括世界文学)格局分为界限分明的两大阵营:一边是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抽象的形式主义;另一边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断然否定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被当作颓废、没落、色情、荒诞的同义词。”在茅盾看来,“现代派”的各种文艺流派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哲学基础上的唯心主义、非理性,创作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对现实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态度是颓废没落的,思想内容是贫乏空洞的。在这里,茅盾不仅不再表现出一代批评大家“取精用宏”的博大胸襟,相反,时代文化主潮所追求的“纯粹化”“正典化”冲动表露无遗,由此必然带来理论视阈的褊狭与短视。
二
茅盾把自己1950年代的文学批评集命名为《鼓吹集》,暗含“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之意。然而,纵观他195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们发现具有高度文学自觉意识和个体批评风格的个人话语往往与主流权力话语潜流并行,对既定文学规范不断进行质疑与修正,犹如平静海面下的急流与旋涡,使这一时期茅盾的文学批评曾现出鲜明的“双语”“复调”色彩。人们看到了茅盾建国后文学批评的许多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却不知道正是这些“矛盾”,体现了一代文豪在特定时代对文学本质的可贵坚守,展露了他竭力维持文学发展命脉的良苦用心。这首先表现在对文学新人的发现与提携上。对文学新人的态度是考验所有批评家使命感、责任感和人格精神的试金石。鲁迅当年就十分痛恨那些在“嫩苗花地”中“驰骋”的“恶意批评家”,希望批评家能够成为长养花木的“有灵魂”的“泥土”。茅盾就是这样的泥土,许多文学的幼松嫩苗正是在他的辛勤培育下茁壮成长。他以宽厚慈和之心、欣喜宝爱之情、谨严明敏之态为新人们呐喊助威指点迷津。《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关于〈党的女儿〉》《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怎样评价〈青春之歌〉》《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上的讲话》《一九六零年短篇小说漫评》等文章中涉及的新人新作多达六十余篇,王愿坚、王汶石、茹志鹃、林斤澜、胡万春等人在创作中表现出的才华使茅盾在欣慰之余倍加珍视。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王愿坚以小小的“七根火柴”写出了革命战士的坚贞信念,唱出了无名英雄的赞歌,从而在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之外开拓了“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他对《百合花》的激赏与推重早已成为文坛佳话。“文革”后茹志鹃重回文坛时说:“《百合花》在我创作历程中,是关键的一个作品,是使我鼓起更大的勇气走上了创作这条道路的作品。更准确地说,是茅盾同志对这个作品的鼓励,使我产生了勇气。”当人们对《青春之歌》颇有微词时,又是茅盾指出“《青春之歌》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并进一步上升到评价文学作品的方法论高度——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作品,否则就会犯主观性片面性的错误。
对文学艺术性的强调是1950年代茅盾文学批评又一个显著特征。温儒敏先生在分析茅盾的“作家论”时指出:茅盾作家论的重点始终放在作品内容的评析上,所注重的是作品的思想观念,而不是想象力、艺术创造力,即使在作形式批评,也很少真正进入审美的层次。然而,建国后茅盾的作家作品批评恰恰相反,对思想内容的评析总是一笔带过,他津津乐道正是作品的艺术风格。他说:“不要小看技巧,没有技巧的作品,本身就不能行远垂久。”他强调短篇小说要有节奏感和意境美,表彰王汶石的峭拔简练与茹志鹃的清新俊逸,《百合花》因其独特的抒情风格为他所钟爱,在坚定维护《青春之歌》的同时,也不讳言作品结构的凌乱、次要人物形象的模糊和语言的缺乏个性等缺陷。并写了《关于艺术的技巧》《谈描写的技巧》《谈文学的民族形式》《关于人物描写的问题》等专门探讨文学形式的文章,在“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化约为“政治性唯一”的时代语境中,茅盾深知他热衷“技巧”的现实危险性。然而,艺术家的良知使他无法忍受无视文学创作规律与作家艺术个性的文化政策,使他不能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恶性发展袖手旁观。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说:“批评的高层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学生的作业,而是抛弃毫无价值的作品,理解杰作,理解其自由的创造冲动所蕴涵的有朝气的、新颖的东西。”1950年代茅盾的文学批评不愧是“高层次的批评”,他以特有的审美感知力和可贵的艺术良知坚守着新中国文学的审美之维。
对重大(尖端)题材的质疑与修正是茅盾1950年代文学批评的又一亮点。“题材”始终是茅盾文学批评关注的中心之一。然而,当代文学把“题材”上升到衡量作品意义与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只能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表现重大社会事件,日常生活、个人情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情趣受到排斥和打击。题材问题因此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主要病源之一。茅盾对题材的单调与狭窄深表忧虑。1956年6月在《文学艺术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一文中,茅盾有一段关于题材问题的意味深长的话:
我们认为:反映社会重大事件,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当是文艺作家们努力的主要方向。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排斥了其他的题材。只要不是有毒的,对于人民的事业发生危害作用,重大社会事件以外的生活现实,都可以作为文艺的题材。
茅盾先肯定文学表现重大题材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然后委婉指出“重大社会事件以外的生活现实”都可以作为文艺的题材。他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主流话语的范畴和框架之内,即在肯定当代文学规范与前提的基础之上,对题材做了尽可能的拓展。1957年在《杂谈短篇小说》中,他进一步指出:“短篇小说取材于生活的片断……所谓生活的片断,是在你所熟悉而且理解得透彻的生活海洋里,拣取这么很有意义的一个片断。”明确提出短篇小说的题材应来源于自己熟悉而且理解得透彻的生活,来源于个人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悟而不是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社会重大事件。在《六0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茅盾甚至说:凡是清新可读的儿童诗,都是抒情式歌咏农村日常生活的小诗,而大主题的,如歌颂三面红旗、水利网、电气化之类的作品,大都缺乏新的意境,也缺乏新的语汇。最糟糕的是个中标语口号的剪接。茅盾对当代文学重大题材规范的质疑与修正,实际上是对文学承载过多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的反拨,是对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感情空间的开掘,对个体生活、情感价值与个体独立性的维护,这在运动频仍的1950年代尤其难能可贵。
三
纵观1950年代茅盾的文学批评,无论在主观动机还是在现实效果上,都构不成与主权话语的直接对抗。如上所述,他的文学批评是基于艺术家的良知与批评家的慧眼对文学本质的自觉坚守。他总是试图在主流话语的框架之内,在当代文学的既成规范之下,向种种肆意践踏文学的行为提出质疑与修正。所以,在政治与文学、兴趣与需要、权力意志与自我观念、时代主潮与个体独立意识之间他取舍艰难,摇摆不定。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一个又一个曾经的权威被打倒,不能不使茅盾心有余悸,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力求与主流权力话语保持一致。然而,根深蒂固的文学自觉意识,终究使他无法忍受泛政治化语境对文学的肆意践踏,他真诚的声音穿透层层乌云直抵我们的心底。
研读1950年代茅盾的文学批评,他有两种话语修辞特别值得关注。一种是“肯定……否定”式,一种是“附加解说式”。前者如:“如果政治性好,艺术性不好,我们是不是欢迎呢?我们的回答是欢迎,我们的评价是肯定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欢迎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欢迎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我们仍然要批评它。”又如上文提到的那段关于题材的意味深长的话,都是典型的“肯定……否定”式。这种话语方式意在不触犯主权话语与当代文学规范的基础上,对主流权力话语做出尽可能的修正与补充。这类话语往往形成内在的冲突与强烈的反讽效果,因而具有巨大的张力。后者如:“我在这里宣传要懂技巧,正为的要使技巧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不必再重言以申明了吧?”(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又如:“不要小看技巧,没有技巧的作品,本身就不能行远垂久(请不要误会,这里丝毫没有不重视思想的意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以上例句中加点的句子都是对前边句意的进一步解释、说明或补充,其目的是要淡化或转移人们的政治嗅觉,使接受者更好地理解领会自己的意图。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一种话语修辞的选择总是与特定的语境、主体潜隐的目的密切相关。解读1950年代茅盾为自己的批评话语所选择的修辞策略,真真令人扼腕叹息。一代文豪、新中国文化部门的高层领导讲起话来却如此吞吞吐吐瞻前顾后模棱两可,他曾经的气魄与胆识早已荡然无存。由此,政治高压与话语霸权对一代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折磨与销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作者简介:沈文慧,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程光炜.建国后茅盾的文艺理论和批评[J].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2]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 茅盾.1950年代是“人民的世纪”[J]. 新世纪(创刊号).
[4] 茅盾.茅盾评论文集(上)[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 茅盾.夜读偶记[A].《茅盾评论文集》(下)[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6] 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7]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A]. 鲁迅论文艺[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8] 茹志鹃.时代的足迹——〈百合花〉后记[J]. 光明日报,1978年9月17日.
[9]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 [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