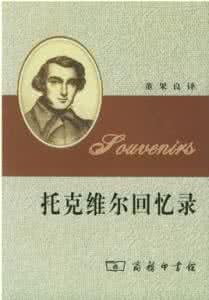
托克维尔说:“在中国身份是非常平等的,而且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经过科举,可以由一个官职升迁到另一个官职……我读过一本中国小说,男主人公终因金榜题名而触动了女主人公芳心。”
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至少有三次提到中国。第一次是论述“美国的行政分权的政治效果”时的一条作者自注:“在我看来,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说: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虽然也在天天前进得相当好,但决不是甚好。我认为,中国一旦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就会从它那里找到世界上现存的最好的行政集权的典范。”(《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一版第101页。) 托克维尔结识的那些旅行家在中国的考察大概不会很深入,能够蜻蜓点水地看一点表面现象也就很难得了。《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于1835年,这个时候,大清国内本身也处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状态,国门还没有被洋人打开,能走进中国旅行对洋人来说多少有点冒险,自由地深入观察了解中国当时社会又有多大可能性呢?没有到过中国,似乎也没计划到中国转悠一圈写一部论中国的什么,托克维尔仅凭几个旅行家浮光掠影的描述,就以为中国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好的行政集权的典范”,这显然不像批评,应该也不是恭维大清帝国,不过,即使不算赞美,也表示一种正面的肯定。嘉庆道光治下的行政制度有这么迷人值得欧洲人来有兴趣地探究吗?我只能说,法国人还真够浪漫的。第二次是论述“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时,托克维尔用了大半页的篇幅对中国大发宏论,其中有这么几句:“征服中国的外族采用了它的习俗,那里的秩序依然井然,一种物质的繁荣依然到处可见。在中国,革命极其罕见,战争可以说闻所未闻。”(同上,下卷第566页)托克维尔知道大清帝国每个男人都必须拖着一条辫子吗?听说过“留头不留发”的故事吗?知道“文字狱”的恐怖么?血腥镇压而换来的“秩序井然”或者“物质的繁荣”不过是“有安宁而无幸福”,托克维尔自己好像也不向往,否则,为什么他选择去美国考察民主而不来中国探讨“行政集权的典范”?虽然他对美国的民主并非全盘接受,但是,假如他到中国来访,我认为他绝对写不出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民主经典。“革命极其罕见,战争可以说闻所未闻”,这是中国吗?这是陶渊明的桃花源,或者也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中国梦”,连望梅止渴的功效都不具有。
第三次是论述“为什么美国人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大志”时,作者说:“在中国,身份是非常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经过科举的考试,就可以由一个官职升迁到另一个官职。……我读过一本中国小说,其中的男主人公虽经多次挫败,但终于因金榜题名而触动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同上,下卷第793页)我估计托克维尔读过的中国小说不会太多,而且还可能都属于满清朝廷允许公开刊印的。他所提到的那本中国小说明显是烂俗的才子佳人“大团圆”式小说,这类作品在中国一向比较流行。“中状元穿红袍”,国产话本小说以及戏曲里,状元故事多得叫人不能不怀疑,中国历史上果真有这样的传奇吗?习惯浪漫的法国人却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浪漫故事,他们并不知道,在中国,浪漫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想象一种“精神鸦片”。科举制度本身固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等”,但能够有机会享受这种“平等”的中国人并不广泛,“学而优则仕”不断在制造新的特权阶层。或者说,皇权之下,所有臣民都是“平等”的,皇帝拥有对每个臣民生杀予夺的至高无上特权,无论贵为宰相还是一介草民,命运都可能系于皇帝一句话。但皇帝之下,各级都在复制这一模式,官员对下级对平民的随意侵害司空见惯,“土皇帝”遍地都是。在托克维尔访问美国观察美国民主想象中国“平等”的那个时候,满清的王公大臣们还在把探头探脑想跟中国打交道的西方称作未开化的“番邦”,一如既往地夜郎自大,满朝文武的脑袋里还充斥着“中央大国”或者“泱泱大国”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良好感觉,眼前还一派万邦来朝的幻象,哪里懂得什么叫“平等”!坐井观天却又担心风水被洋人破坏的某些清国臣民更是费尽心机妖魔化金发碧眼的洋人,即使后来出访欧美的几个人物好像对人家的民主和自由也不感兴趣。中国在托克维尔那里只是一个想象,他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信息很不够用。在他离世100年后,中国也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书还有他对中国的想象,当然也无从知晓民主的美国如何蒸蒸日上。很多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并不比拖着辫子的祖上知道得更多,一边狂喊“赶超英美”,一边却又摆出一副同情的样子,可怜着英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看了几部香港警匪片,就以为香港是一个天天打打杀杀的恐怖之都。读了几页报纸听了几天广播看了几回电视,就想象着美国满大街枪声不断、每个角落都藏着一个杀人犯,甚至因而对“民主”“自由”也心生恐惧而坚决抵制。假若托克维尔后来有机会知道他误读了中国,他会想些什么呢?倒是他没有明确指出属于“世界上现存的最好的行政集权的典范”的一段,却叫人不由自主浮想联翩:“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君主国家,……领取薪俸的官员人数极多,他们的生活有充分的保证,以致人人都想找到一个官职,并要象享用父母的遗产那样安安稳稳地把官当下去。”(同上,下卷第796页)这场景好让人眼熟啊,好像也属于一种很具国情特色的有悠久的历史的“梦”,很多人挤破脑袋也想圆一回这样的“梦”,这是否可以做“身份是非常平等的”一句绝佳的注脚?在什么地方,公民们允许官职像父母的遗产那样任由某些人抱着专利似的安稳享用?太多的人都在做那样的“梦”,独木桥上千军万马,“平等”地做着一步登天青云直上的“梦”,仅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梦”的存在本身,已经无法接受“享用父母的遗产那样安安稳稳地把官当下去”的状况了。但是,很多做“梦”的只是不能接受别人享用那样的“遗产”,却想给子孙留下那样的“遗产”。一切好像没有多大改变,而那样的“梦”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噩梦,不能在那样“梦”下去了。这,或许正是今天我们重温托克维尔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