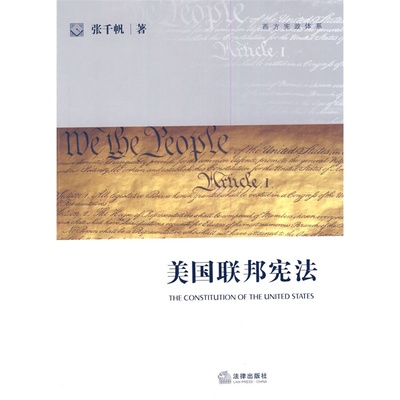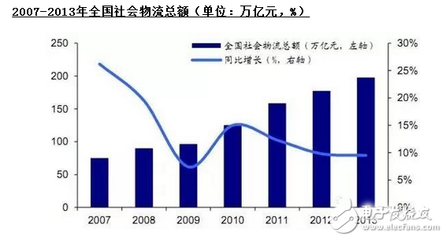如果匈牙利学者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r?s, 1784-1842)可被称为欧洲藏学之父的话,那么或可被称为美国藏学之父的应该是卡尔梅克蒙古喇嘛格西旺杰(Geshe Wangyal, 1901-1983)先生。格西旺杰生于居住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卡尔梅克蒙古部落之中,少年出家为僧,后随布里亚特蒙古喇嘛德尔智(Agvan Dorzhiev,1854-1938)入藏,在拉萨哲蚌寺学法九年,获“格西”学位。后到北平学法、营生多年,曾随中国藏学之父于道泉先生学过英文,也曾短时间为钢和泰先生创办的中印研究所工作过,还充任过英国外交官Charles Bell(1870-1945)爵士的翻译。自二战爆发至五十年代初,他往返于西藏和印度两地。1955年,往美国新泽西,为被安置于此的卡尔梅克蒙古难民社团提供宗教服务。很快,在他身边聚结起了一批来自大苹果和大波士顿地区的白人佛教发烧友,其中烧得最厉害的即是日后美国最负盛名的藏学研究权威Hopkins和Thurman二人。他们都于1963年从哈佛退学,住在格西旺杰于新泽西建立的那座小喇嘛庙中随他修习藏传佛法。
1965年,格西旺杰带Thurman去了印度,介绍他皈依,使他成为第一位受剃度出家的白人藏传佛教僧人。一年半后,Thurman还俗,在格西旺杰鼓励下回哈佛完成学业,1972年博士毕业后先在Amherst学院任教,后于1989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法主宗喀巴”讲座教授,并于此创立了“美国佛教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成为迄今全美最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权威和发言人,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最耀眼、最具魅力的藏传佛教代言人”。在他身边围绕着一批信众和粉丝,同时也培养出了不少从事印藏佛教研究的优秀弟子。Hopkins则于新泽西随格西旺杰学法多年之后,进入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美国第一家佛教学博士研究生班深造,随出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Richard Robinso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71年,Robinson不幸英年早逝,Hopkins便往印度学法,撰写博士论文。1972年,Hopkins以“观空”(Meditation on Emptiness)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翌年即受聘于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研究系。于此,Hopkins新开炉灶,建立起了一个藏传佛教博士研究生项目,培养出了迄今于北美大学数量最多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今于北美诸大学内担任藏传佛教教职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的学术方法和成就代表了当代美国藏学研究的主流传统。
《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和西方》书封
199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和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一书,作者是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的西藏和佛教研究教授Donald S. Lopez Jr. 先生。这部著作不只在藏学界,而且也在整个世界宗教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Lopez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手法,对历史上和当下西方世界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误解、挪用和歪曲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清算,特别是对当下西方神话化、精神化西藏,将西藏与香格里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幻想所创造出来的乌托邦——等而视之,以至于普遍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这一现象做了振聋发聩的批判。
《囚徒》一书分别从名称(喇嘛教)、书(《西藏生死书》)、眼睛(《第三只眼》)、咒语(六字真言)、艺术(唐卡)、领域(美国藏传佛教研究)和囚牢(香格里拉)等七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侧面,揭露和剖析了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历史过程及其背景,从而解构和颠覆了西方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知识与话语体系。其中“领域”一章,专论美国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以作者自身的经历,将Hopkins在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系组织、开展的藏传佛教之教学和研究项目作为典型,对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美国藏传佛教研究传统做了颇具戏剧性的描述、分析和批判。
Lopez对美国藏学主流传统的批判分别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首先,他将自Thurman和Hopkins开始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北美藏传佛教学者统称为“拜倒在喇嘛脚下”的一代,他们一反西方学界过去的传统,不再将藏传佛教看作是佛教最不忠实和最堕落的一种传统,相反将它视为佛教最直接和最权威的传统,将喇嘛视为佛陀再世,是现世佛教最权威的解释者。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自己看作是一种行将灭绝的宗教传统的保护者和继承人,他们之所以远涉重洋、匍匐在喇嘛脚下,为的只是能够记录下喇嘛们历经千年口耳相传下来的佛语,由此给北美藏传佛教研究赋予了崇高和迫切的宗教史和思想史意义,也给西方藏学家赋予了崇高的使命感和神圣感;Lopez将Hopkins在弗大建立的藏传佛教教学制度与格鲁派寺院僧人所必须接受的历时近二十年之久的传统教学法进行了比较,揭露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机械的模仿和缩减。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Hopkins所主导的这种藏传佛教教学更接近于佛教的“神学式”教学和研究,缺乏现代学术必须具有的批判精神,与当代宗教学研究的学术宗旨和规范不相符合。
此外,在讨论《西藏生死书》于西方流传历史一章中,Lopez还以Thurman翻译的《中阴闻解脱》一书为靶子,对Thurman的学术作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认为他对当代西方神话化西藏之传统的形成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正是他借助其藏传佛教权威的身份,通过对《中阴闻解脱》这部藏传密典的富有创造性的翻译和解释,不但把藏传佛教宁玛派所传的古老的“中阴”仪轨改造成了一种“科学的死亡技术”,使得藏传密教的成就者(持明)变成了“英雄科学家”、“心灵宇航员”和“非物质文明的最核心的科学家”等等,而且最终还使藏传佛教演变成为一种与现代物质技术一样精致的“关于精神技术的古老传统”,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金字塔。总之,Thurman的藏传佛教研究从现代学术意义上来说是不合格的,从佛教义理上来说是不究竟的,同时他还必须为他借助其个人魅力推动了西藏的精神化和藏传佛教的神话化负起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囚徒》出版后一度好评如潮,却也引发了不少争议。美国宗教学会曾在其2000年年会上设专场讨论这部作品,受邀参与讨论的专家对其毁誉不一。受到Lopez批评的Thurman教授很不买账,愤怒谴责Lopez“责备受害者”,并动情地说,若读了这本书,“世上还有谁会对西藏和藏传佛教产生任何的好感呢?”他一语中的,道出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一个通病,即在泼掉洗澡的脏水时往往连带把婴儿也一起泼掉了。他们在解构西方精心建构起来的有关东方的知识和话语体系时,难免也会把东方及其文化一并解构掉。
Lopez自我感觉写作这部作品时始终站在西藏一方,批判和揭露的只是于西方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下构建起来的西藏话语,但其客观效果却对西藏和藏传佛教之整体形象产生了莫大的损害。他成功地采用了“一种对立的游戏”(a play of opposites)来探讨欧美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之知识和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在这种话语中西藏只是一个密码,或者无可挽救地成为西方价值的魔鬼式的颠倒,或者是一个可以治疗其自身价值已经被颠倒了的西方的天使般的资源,所以,他们时或妖魔化、时或神话化西藏和藏传佛教,似乎就不可能对它们产生任何正常的兴趣和正确的理解。
Lopez明确表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揭穿那些隐藏在我们最珍爱的观念背后的真相,从而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的实情作出更加精确的描述,而是为了要说明为何这些西藏神话能够被保持下来,并不受挑战地在我们中间流传”。可是,在全书的叙述过程中,他很难一贯地保持超然、价值中立和讽刺的态度,难以将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和话语仅仅作为一种建构起来的话语来对待,而不时会不自觉地转入一种“事实性”的叙事模式,不由自主地引导读者相信他所揭露的西方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叙事和话语反映的恰恰正是西藏之过去和现在的实相。
在对《囚徒》的各种批评声音中,时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助理教授的青年学者Christian Wedemeyer先生于2001年第2期《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书评显得最为独到和尖锐。他认为“Lopez在他的书中处理了一些值得所有像我们一样关心对他者的表述的宗教学者认真和持续地考虑的重要议题。[本书]有些部分对其主题做了很好的处理,为我们理解西藏的表述史作出了不错的贡献。遗憾的是,这本书在很多方面远没能够对其主题提供它应得的较好的处理。在其最后的分析中,《囚徒》既没有前后统一地坚守其学术方法,也没有达成其预定的目标。所以,它或许应该和Evens-Wentz(《西藏死书》的第一位译者)、 Blavatsky夫人(灵智学会创始人)和Rampa(《第三者眼睛》的作者)的著作(皆是于《囚徒》中得到讽刺和批评的作品)并排排放在书架上,让那些带着相同兴趣的[读者],[希望]也带着同样的谨慎来阅读它”。
具体说来,Wedemeyer觉得这本书的前四章还不错,但讨论死书、领域和囚牢的最后三章实在问题多多,不论是其学术方法,还是其实施都有重大失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Lopez的“批评”经常不直面交锋,而是拐弯抹角,以暗讽、影射的方式展开,有些讨论则明显不够诚实,有失厚道。例如,“囚牢”一章的讨论,不过是对David Jackson教授发表的“有关新近藏传佛教艺术目录”一文的发挥和引申,却不如后者的见解细致和深刻。顺便说说,对从第一部英译《西藏死亡书》问世以来西方人对它的误解,旅居意大利的宁玛派上师南喀诺布活佛很早以前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囚徒》中对《西藏生死书》的讨论,与见于John Myrdhin Reynolds先生的《直指本觉裸见自解脱》(Self-Liberation through Seeing with Naked Awareness, New York, 2000)一书附录中的相关讨论亦颇多相似之处,从佛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后者更为专业和深刻。
Wedemeyer认为《囚徒》一书中野心最大,但写得最差的是“领域”,亦即讨论“作为北美大学中的一个学术领域的藏传佛教研究之发展”那一章。这本来是很有价值的一项研究,可是作者未能为这个领域提供一个不偏不倚的,哪怕是大致真实的图像。显然Lopez自己于1970年代中、晚期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的个人经历被当作了北美佛教研究之整体的一个转喻。而任何对这个主题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这样的一种学术进路不适合于表明所涉议题之复杂性,遗憾的是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十有八九对这个领域完全陌生,故很容易被Lopez误导。
Wedemeyer觉得读者在这一章中更能体会到的或许是Lopez对他所受到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对他自己的导师的深刻的不满。在这一章中,我们没有再见到“对立的游戏”,而只是作者对这个博士研究生班的不加掩饰的谴责,认为“它所给予的不过是一位十二岁的小喇嘛所要求掌握的资料的部分而已”。对此,即使是Lopez在弗大的同门也极不认同,他的师弟Guy Newland教授曾专门对他将弗大宗教系的藏传佛学研究生班的训练与藏传佛教寺院的对学僧的训练相提并论进行了批驳。再说,美国藏传佛教研究并非独此一家,弗大宗教系的藏传佛教研究项目不足以代表这个研究领域之整体。
上述这篇书评发表时,Lopez已是行内大腕,而Wedemeyer还是学界的一张新面孔。可他敢于无视权威,发表如此犀利的书评,与其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倒不如说是他有足够的学术底气和自信。确实,不管论对理论的敏感,还是论语文学的功底,Wedemeyer都不逊色于Lopez。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天的Wedemeyer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史学的教授,与Lopez一样名满天下。其实,尽管以学龄来算,Wedemeyer比Lopez晚了将近二十年,但从学术辈分来说,他们却可以说是同辈学人。Lopez是Hopkins在弗大培养出来的众多弟子中最早、最知名的一位,而Wedemeyer则是Thurman在哥大培养出来的一批弟子中最知名的一位,他们都是美国藏学主流第二代传人中的佼佼者。
可是,他们对美国藏传佛教研究这一学科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从他们的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术传承与学术评价之间的微妙关系,而理清这种关系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藏学主流传统之形成、发展和进步的轨迹。毋庸置疑,上述Wedemeyer的书评非常学术和专业,他对Lopez书中出现的学术方法之贯彻前后不统一和许多具体细节的讨论有失诚实等问题的批评十分犀利和独到,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但不得不说,这篇简短的书评用辞之犀利异乎寻常,或会令人猜测可能是Lopez书中对Thurman的激烈批评和讽刺令Wedemeyer不爽,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毫不留情地对Lopez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Thurman十分情绪化的反击相比,Wedemeyer的批评针针见血,更具学术杀伤力。但愿这只是以我小人之心,度Wedemeyer君子之腹。
日前,Thurman的弟子推出了庆祝他七十诞辰的颂寿文集——《维摩诘的丈室》(In Vimalakirti's House,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Robert A.F. Thurman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New York, 2015),主编之一就是Wedemeyer。在这部文集的导论中,他对其尊师的个人品格、社会影响力和学术贡献都做了高度的评价。他援引学界诸大佬对Thurman多部作品的赞美,来证明其师尊之学术成就的伟大。说Thurman那本以宗喀巴大师的《辨了不了义善说藏》之翻译为主体的对印藏佛教中观哲学的研究是“藏传佛教哲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而他翻译的宗喀巴大师的《密集教王五次第教授善显炬论》则是对密集体系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对藏传密教无上瑜珈部之研究的优秀作品;他翻译的《维摩诘经》也是所有这部佛经之译本中最流畅、通顺,并充满了喜剧天赋和幽默感的一种。此外,他所撰写的有关佛教诠释学、佛教伦理、社会思想和比较哲学等方面的许多短文也都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启发和推动意义。当然,最值得称道的是,Thurman以其非凡的个人魅力、雄辩的口才和不知疲倦的能量,为藏传佛教于西方的传播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对此Wedemeyer做了充分的肯定,而丝毫没有像Lopez一样把神话化西藏的责任加到他的老师头上。虽然,他也承认Thurman的翻译风格确实十分大胆而富有创造性,这一点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同,就连他自己也曾对老师将“持明”译作“科学家尊神”不以为然,但他依然坚信,总体而言,Thurman的译文既灵动而富有诗意,又具有哲学家的严谨,丝毫不认为他有借助翻译而篡改文本原意、夹带私货的问题。对自己老师的学问,Wedemeyer显然没有像对待Lopez一样表现出极其犀利的批评精神。
Wedemeyer批评Lopez把“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的个人经历当作了北美佛教研究之整体的一个转喻”,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自然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Lopez对弗大藏传佛教研究生班之教学,和对Thurman之学术方法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于此,我们甚至应该对Lopez敢于对老师和自己的学术道路作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赞扬。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幻灭的一代,Hopkins和Thurman最初对藏传佛教的兴趣本来就与学术无关,而是为了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令精神走向成熟解脱的道路,他们是美国嬉皮时代和新时代运动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代激进的东方发烧友中的典型。虽然为了安身立命,并为藏传佛教更好地在西方传播开创一条便捷的途径,他们都在格西旺杰的鼓励下重返曾被他们遗弃了的校园之中,并成功地走上了一条学术的道路。但是,即使他们最终都成了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他们最属意的依然还是教法而非学术,最关心的是如何在西方大众中传播他们所领悟了的藏传佛教之甚深密意。他们的藏传佛教研究基本背离了欧美的佛教语文学传统,他们的著述也基本上徘徊于面向普罗大众的法本(dharma books)和面向专家的精深的学术著作之间。
从这个角度而言,Lopez对这一学科领域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由于《囚徒》一书的着力点并不是学术史,而是西方如何表述西藏的历史,它只求典型而不求全面,所以,作者既没有对他的老师辈学者的这种介于教法与学术之间的治学方法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质疑和批评,也没有对Thurman众多著作于传法之外的学术意义予以肯定。为了突出Thurman如何为神话化西藏推波助澜,便不得不忽视其著作的学术意义,而这引起了Wedemeyer的强烈不满。从佛教语文学的角度来看,Thurman和Hopkins的大量以藏文著述的译文为主体的学术著作都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包括Lopez书中加以褒扬的Hopkins的成名之作——《观空》一书,由于其预期的读者群显然更应该是广大的修法行人,而不是象牙塔中有数的几位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它的写作方法不符合基本的语文学学术规范,难说它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同样,Hopkins翻译的觉囊派祖师朵波巴的名著《山法了义海》虽乃皇皇巨著,但它备受佛教语文学家的诟病,因为其中的译文不但有很多的错漏,而且还通过翻译语词的选择和译者带有倾向性的诠释,使得其原作面目全非,其中之微言大义也全都变了味道。遗憾的是,对此类学术毛病,Lopez反而没有提出尖锐的批评。
不得不指出的是,Lopez虽然对包括Thurman在内的诸多西方学术名流的批评通常都是嬉笑怒骂、不遗余力的,然而对自己的老师Hopkins的批评却是点到为止,非常留有情面,看来他并没有如Wedemeyer推测的那样“对自己的导师怀有深刻的不满”。事实上,Hopkins与Thurman一样,都必须对神话化西藏这一现象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条道路上他有时走得甚至比Thurman更远。例如他将根敦群培的《欲论》翻译、改造成了一部同时适用于异性恋和同性恋者的性爱技术宝典,并将这部原本与佛教无关的性爱指南书说成是一部藏传佛教的传世经典,将既能享受身体的喜乐,又能获得精神的解脱说成是藏传佛教之精华等等,都是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利用其藏传佛教研究权威的身份,如此曲解藏传佛教,误导受众,真是匪夷所思。然而,Lopez对此竟然视而不见,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像针对Thurman那样尖刻的批评,难怪Wedemeyer会有如此深刻的不满了!
Thurman和Hopkins是二十世纪美国藏学研究的双子星座,尽管两人风格迥异,于大庭广众之下Hopkins远没有Thurman那样雄辩和耀眼,但他们都是极具个人魅力的上师型学者(guru),各有各的卓越。凭借着上个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于北美大众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他们作为北美藏传佛教研究最著名权威的声望,在他们身边集结起了一大批弟子,渐次培养出了一批藏传佛教学者,后者今已成为北美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内最主要的一支生力军。
Hopkins从1973年开始就在弗大宗教系任教,迄止2005年退休,三十余年间于此培养出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生。据不完全统计,在1980和1990年代,Hopkins门下培养出的藏学、佛学博士有十四位之多。Hopkins早年的弟子中有多位是当今西方藏传佛教学研究领域内大名鼎鼎的人物,如Lopez、Anne Klein(莱斯大学)、Georges Dreyfus(威廉姆斯学院)、John Powers(堪培拉国立大学)、Guy Newland(中部密西根大学)和Elizabeth Napper等等。而他于新世纪培养出来的弟子中,如Bryan Cuevas(佛罗里达大学)、Trent Pomplun(Loyola大学)等也已分别成为佛教死亡学和藏传佛教与耶稣会士等专门领域内的顶尖学者。而他的早期弟子中,有的自己也已在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培养博士生,故其再传弟子不少今天也已成为这个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了。例如Lopez在密西根大学培养出来的弟子Jacob Dalton和Andrew Quintman如今已分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耶鲁大学的佛教学教授,是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内引人瞩目的后起之秀。
Thurman虽然于1972年就取得了哈佛的博士学位,但其后长期在Amherst学院教书,1989年才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故其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起步比Hopkins晚得多,直到1993年才培养出第一位博士,即日后以研究拉卜楞寺而知名的Paul Nietupski先生(John Carroll大学)。但迄止2013年的二十年间,他也已培养出了十九位藏学博士,在数量上不逊于Hopkins,其中如Wedemeyer(芝加哥大学)、David Gray(Santa Clara大学)和John Pettit等人也都已在学界崭露头角,成为印藏佛学研究领域内的知名人物。另有部分弟子则成为“美国佛教研究院”的中坚力量,继续追随Thurman从事印藏佛学研究和藏文佛教文献的翻译工作。
由于共同的师承关系,Thurman和Hopkins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学术团体,共同组成了美国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的主流传统。作为开山祖师,Hopkins和Thurman都赢得了其弟子的尊重和推戴。由亲密的弟子、朋友和同事随喜撰写论文,为年满六旬(或六五、七旬、八旬等)或者即将还历退官的老师编集、出版一部“颂寿文集”(Festschrift)本来只是欧洲学界流行的一个传统,在今天的美国学界不甚流行,而Hopkins和Thurman两人却都获得了这样的殊遇,由此可见师承关系于美国藏学研究领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为Thurman七十寿辰颂寿文集撰文的有十六位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培养出来的博士。而Hopkins则于六十岁时就得到了其弟子和朋友奉献的一部颂寿文集,题为《变化中的心识:向Jeffrey Hopkins致敬佛教和西藏研究文集》(Changing Mind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Buddhism and Tibet in Honor of Jeffrey Hopkins, New York, 2001),收录了十二篇论文,作者也都是其直接的弟子或朋友。
如前所述,Hopkins和Thurman最初都是格西旺杰喇嘛的弟子,不管受过还是没受过正式剃度,他们都是佛门的入室弟子,都具有极好的藏语文能力,接受的也都是传统藏传佛教寺院内专为出家僧众设计的教学训练。他们的学术风格十分类似,都是以翻译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等藏传佛教大师留下的重要著作为其学问之根本,分类诠释藏传佛教精义,介绍藏传佛教的修习等等。他们的学术生涯多半是在西方替藏传佛教代言,尝试用当代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解读和传播这些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和深奥的藏传佛教教法。而且,他们也以同样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方法来培养他们的弟子,首先要求他们有足够好的藏语文能力,能够流利地解读和翻译藏文佛教文献,为此他们常常把学院外的喇嘛带到他们的课堂。于接受了过硬的语文训练之后,弟子们通常会被指定一个古典藏文佛教文本,要求他们先准确地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利用这个文本的一部相对后出的释论,在喇嘛之口耳相传的帮助下,解读这个文本及其释论,最终给这个文本所包含的微言大义做出正确的解释,并确定自佛陀直至Hopkins的传承谱系,追溯这个文本的传承轨迹,确立这个教法传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例如,Hopkins曾将十八世纪藏族学者绛阳协巴所造《大宗义书》(Grub mtha' chen mo)中有关自续部中观和经量部中观的章节分别分配给Lopez和Klein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题。重视文本,通过对文本的读解、翻译和注释,来培养弟子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能力,这不失为一种十分可取的教学方法。然而,是将手中研读的这个文本当作一种绝对真实、不可怀疑的教条,将记录和保持这个文本所传教法之传承作为首要目标,或者不惜曲解其本意以逢迎当代人之宗教需求和热望,还是将这个文本放回到它原有的语言、教法语境中去细致考察,以批判性的态度来观察和分析这个文本所传达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对它作出正确的解读和诠释,这是区分宗教和学术、神学和比较宗教学研究的一个分水岭。正如Lopez所批评的那样,以Hopkins和Thurman为代表的美国早期藏传佛教学者常常模糊和混淆这种宗教和学术的分野,乃至造成藏传佛教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宗教化、神学化的倾向。
Hopkins仿照藏传佛教寺院训练学僧的方法在弗大培养出了一批具有极好的藏语文能力和对藏传佛教有深刻了解的弟子,后者的学术风格或多或少与Hopkins类似。但是,随着藏传佛教研究与作为整体的北美比较宗教研究在学科上的整合越来越深入,这种具有明显的宗教化神学旨趣的学术取径渐渐被扬弃,而代之以选择与美国主流学术传统更接近的学术方法,选择与美国主流学术关心更相关的课题。前述Lopez从研究中观哲学、《心经》等,转而采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手法来考察西方表述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历史就是这种转型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他对中观哲学等藏传佛法的研究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Hopkins的影响,而他那些可以归类于“文化研究”领域的著作,则转而成为对Hopkins之学术的反省和批判了。而像Dalton和Quintman等Lopez的弟子的学术风格和学术著作,则明显减弱了Lopez和Hopkins所代表的两种学风之间的冲突和紧张气氛,其中虽有Hopkins之传统的影响,但更接近于被美国藏传佛教研究主流所遗忘的佛教语文学传统,也与美国主流学术传统中的宗教研究的大趋势更加切合了。
由于Thurman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此时那股于六七十年代之嬉皮和新时代运动中迸发出来的对藏传佛教等东方宗教传统的狂热已开始减退,尽管Thurman本人作为藏传佛教于西方世界之代言人的影响力日增,但他并没有像Hopkins一样把藏传佛教寺院对学僧的训练方式完全照搬到哥大宗教系内,而是基本上传习了哥大已有的学术训练传统(Thurman的前任是著名印藏佛教学家Alex Wayman教授;优秀藏学家Matthew Kapstein教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曾长期在哥大任教)。与Hopkins的弟子基本上只利用藏文佛教文献从事藏传佛教研究不同,Thurman的弟子大部分兼通梵藏两种佛教语言,多从印藏佛教研究的角度从事藏传佛教研究,他们的语文学功夫似乎比Hopkins的弟子扎实,而且他们也更注重比较宗教学的训练,不专注于对藏传佛教进行神学式的研究。Thurman在哥大最优秀的作品或就是Wedemeyer,他身上不乏其尊师式的个人魅力,而其佛教语文学的功力和对宗教学理论的掌握均更胜其尊师一筹,他的有关圣天《摄行灯论》的研究(Aryadeva's Lamp that Integrates the Practice (Caryamelapakapradipa): The Gradual Path of Vajrayana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Esoteric Community Noble Tradition, New York, 2007)和他的《为密乘佛教正名》(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 : History, Semiology, and Transgression in the Indian Tradi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这两部著作,分别反映出他于佛教研究的两个方面的功底和成就。自然,他对Lopez对美国藏传佛教研究这一学科之形成和发展之历史的描述和批评根本无法认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