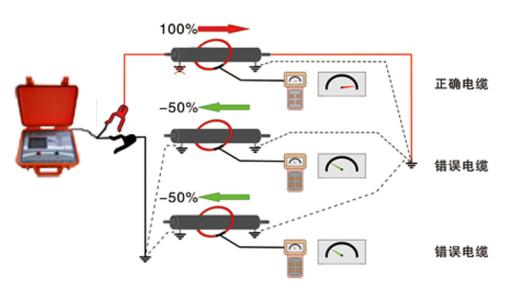来源:文汇报 作者:记者 于颖
由于近代以来的学科分野和细化,除了艺术史、考古学等领域善用图像外,历史研究的主体叙事中往往图像缺位——史界重文轻图,图像资料只是“辅助”“帮腔”“陪衬”……时下,伴随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也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
这无疑是个读图的时代。如果有机构做项调查,统计下都市里每人每天平均拍多少张照片、打开多少幅图片、看过多少块广告……结果应该非常有趣又惊人。图像早已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交和视觉传播的必需品,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影响着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方式。
回首昨日,翻翻微信好友圈便能清晰重现;遥望更远的人类历史,除了文字材料,图像在接近和还原历史中也大有作为。但由于近代以来的学科分野和细化,除了艺术史、考古学等领域善用图像外,历史研究的主体叙事中往往图像缺位。时下,伴随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也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两只眼睛”关于图像,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在一次演讲中作过一段精彩而机智的陈述:“上帝为什么给我们两只眼睛?我要既严肃又开玩笑地说,这是因为上帝要历史学家用一只眼睛看文字,另一只眼睛看图画。”他还指出,所谓图画,不仅指画家的画作,而指一切视觉性、非文字的资料,“用两只眼睛同时考察历史留下的文献和图画,应该可以见到比较‘立体’的历史”(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
究竟什么是图像?邢先生的回答也只是一家之言。这个问题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不言而喻,不同学科有各自的科学定义,即使在历史学里面,根据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不同,也会有所区别和侧重,难以完全统一。
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图像证史》中就明确表示,“图像(images)”不仅包括画像(素描、写生、水彩画、油画、广告画、宣传画和漫画等),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邓菲也赞同“图像”概念的广泛性:“它指代了与图像艺术形式相关的各类视觉文化材料,包括传世的书画、器物,也包括墓内装饰、随葬品等考古资料,寺庙、石窟内的壁画、造像等物质遗存,以及地图、天文图等一般性的图像资料。”
“很多人认为图像是平面的。我个人的理解是,‘图’或许倾向于平面,‘像’则既可以是平面也可以是立体的。”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李星明看来,作为历史研究基本资料的图像,是同文本、文字并列而言的,主要靠视觉感知进行表达和传播。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仲丹坦言,图像当然可以将实物囊括其中,小者如钱币、奖章,大者如器物、建筑,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不过,受纸质出版物影响,图像史学里常以二维形式的平面图像为对象,而有些文字实质上也是图像,比如中国古代的书法、现代宣传海报上的夸张字体就属于图像类型的文字”。
图像史学的主要推动者、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认为,历史研究中的文字、图像、实体(景观与器物)、口述四类史料形式,最终可合并为图像、文字两种,“文物、古迹等通过现代的载体可以转变为图像,口述也可以转变为文字,所以图像应主要指载体上的形象,与载体上的文字相对应”。四种史料的获取方式也不一样,文字、图像通过阅读获取,实体通过现场观察获取,口述通过倾听记录获取。他特别强调要区分“图像”与“形象”:“‘形象’一词词义复杂,往往指一切有形状的、具象的、可视的东西。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语境中,与‘形象’相对应的都是抽象、无形的概念。文字当然也是一种形象,是一种符号形象,图像则是一种图像形象。如果用‘形象’一词容易造成史料逻辑体系的混乱。”
无论外延的宽窄,一般认为,作为历史证据之一的图像,是与文字相对应而言的。蓝勇指出,早期的文字和图像都很简约,但当时的文字“言简”却不“意赅”,所以才会令后人苦心注疏,往往还众说纷纭;图像也多粗略写意,同样引来臆测不断,永远有盲人摸象之感。后期的中国文字发展较为完备,传神达意到位,讲述事件全面,表现因果也更明确直接;同时,图像也变得愈发精准丰富。
图像不只是补充、印证文字 图像和文字作为史料各有长短,图像明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而文字材料蕴含的信息则更为丰富。邓菲认为,图文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图像跟文献可以互证;二是文本与图像信息有矛盾,但指向了同一个研究对象;三是图像呈现的内容是文献完全没有涉及的。
图文互证的例子很多,李星明随口就可以举上好几个。他在研究唐壁画时,看到两座墓的屏风画中都有同样的形式——画面当中放置金花银盆,盆的口沿立着鸟或鸽子。“后来我在《宣和画谱》中看到,五代时期黄荃、黄居寀父子的花鸟画题目就有叫‘金盆鹁鸽’的,即金盆银盆里盛着水,鸟儿们在旁边喝水,通常描绘皇室、贵族家庭。”据李星明介绍,“金盆鹁鸽”为当时花鸟画的一个格式,从文献和图像的对照中便可以看出来。
再如,几年前陕西潼关县税村前发现一座隋代大墓,后来根据列戟的数量,推断出墓主人为隋太子杨勇。“戟是一种武器,也可作为仪仗器、礼器使用。唐代列戟制就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力。”李星明介绍,《唐六典》中有详细记载:凡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施十六戟……“目前除了16戟的墓尚未发现外,其余的发现都跟文献完全对应,列戟形状也一目了然,对还原当时礼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文字只记载事物名称,不反映具体形象,图像则发挥了补充功能。“以前我们发现,《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记有‘滚乾箱’、‘吊神船’的运输方式,但究竟怎么操作,一无所知。多年后研究海外版的乾隆《金沙江全图》时才知道,用木材在水中滩险处搭成旱厢船路,让空船从中滑过就是‘滚乾箱’;纤夫从岩边用绳索强抬升木船,以减少摩擦来配合前面拉船的纤夫,就是‘吊神船’。”蓝勇认为,如果图中这两部分“文本化”一下,可形成几千字的文字资料,价值不可想象。他同时指出,图像有时会无意留存下一些以前不受关注、后人看来却相当重要的信息点。比如一张老照片中的人物呈现可以有主观选择,但不经意进入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在日后的历史研究中可能非常有用。“况且很多情况下,有些问题文字并无记载,只有图像信息,那就更不可替代了。”
图像和文本都能提供特定的历史信息,两者可能殊途同归,或者指向不同的结果。邓菲在研究死后观念时就发现,从墓葬里看到的图像资料与很多志怪或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并不一致:“笔记小说志异求奇,比如洪迈的《夷坚志》等,会记载一些骇人听闻的有关死后世界的设想,一方面为了吸引眼球,另一方面也有宣扬惩诫的作用;墓葬的语境则不同,是将最美好、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有时还可能涉及多种观念,包括佛教净土、道教升仙等等,竭力营造理想的死后世界。”她指出,文本和图像在这里的明显差别,源于研究材料的不同系统与脉络,“不同的材料,制作目的有差异,导向的结论就可能相反,但都是历史的呈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图像或文字都是史料,也都具有史证的价值。”
“视觉资料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证据,但我们不得不问,图像只是充当补充、印证文字资料的角色么?通过图像,我们能不能重新认识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澳门大学特聘教授王笛的研究,长期聚焦在都市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上。“并非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文字描述,这个缺陷就要用视觉资料来填补。要想‘从下往上’看历史,图像是社会底层最直接的呈现。”他介绍自己在研究近代中国街头文化时,传教士、中外游客、记者拍的照片,艺术家的画作,等等,比文字更容易让人体会到芸芸众生之貌、熙熙攘攘之景。“更重要的是,行人、小贩、工匠、茶客、剃头师、算命先生等三教九流,并非都能载入史册、留下文字印记。”
这一点,李星明也非常赞同。他提醒我们,文本资料多为社会精英、士大夫所写,记载的都是些历史事件,主流对象包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烈妇节女……“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的运作、稳定、发展须臾不可少、却又‘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少有文字记载,即便有,也往往不够完整、全面。”
在研究“失真”中接近另外的“真实” 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开篇就表明:“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写作目的有二: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二是向此种证据的潜在使用者告知某些可能存在的陷阱。”这位当代著名的新文化史学家兴趣爱好广泛,著作宏富,《图像证史》便是由其在剑桥大学开设的同名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自2008年中文版发行后,几乎被当成图像证史这一研究可资利用的“圣经”,阅读引用者甚多。
“图像证史”为学界所乐道,这令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艺术史学家理论学家曹意强“喜忧参半”。他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指出“图像证史”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恰当理解:“从已问世的著述来看,目前流行的做法,不是以图像去图解从文献中已获知的历史事件,就是用文字去描述已知的图像,亦即将图像充作文字‘插图’而已。这种‘图像证史’实质失去了实践意义。”(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案例》)他阐述自己心目中的“图像证史”应有三层含义:一是用以概括往昔学者借助图像遗物解释历史的实践;二是肯定图像的“合法”的史料和史证价值——不但是说图像应被视为与文献载籍具有同等价值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图像应当充当第一手史料去阐明文献记载无法记录、保存和发掘的史料,或去激发其他文献无法激发的历史观念;三是从事“图像证史”者,必须具备艺术史家“破译”图像风格与形式密码的功夫,否则只能“望图生义”,陷入图像的陷阱(同上)。
图像真的有“陷阱”!什么史料都不是完全可信的,怕是严谨的学者们心头一刻都不得放松的那根弦。中国传统史学强调文本,或许骨子里认为文本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历史。其实,文本的客观性及其程度如何需要讨论,图像更是如此。“文字和图像记录历史都是他者的存留、理解,不可能完全反映客观历史面貌,造成误差的原因有主客观之分。”蓝勇认为,客观原因主要是不同载体带来的内容、形式差异,如文字话语中的实录、总志、方志、正史、笔记、档案、谱牒等;图像话语中,如中国画与油画、水彩画、水粉画之别,中国画中的写意与工笔之差、西方画中的抽象主义印象派与现实主义写实派之异,等等。主观原因则是由图像作者的社会背景、人生经历、学科积累、主观诉求造成的,“就像中国传统作秀籍田目的的耕织图和作为事功总结的行业志书,并不具备具体技术传播的功能一样”。
历史上,图像所要教化、感染的对象往往是不识字的民众,故而其表现手段也显得特别直露、显豁,其鲜明的情绪表达和宣传气息时常导致信息失真,与事实相悖。“失真”是历史图像的一个明显特征,或许与文字史料相比,它的这一特点更为明显——绘画是作者的再创造,主观意识融入其中自不待言。比如在苏联上个世纪30年代的画作中,一度很有权势的内务部长尼古拉·叶若夫本来其貌不扬,却被画得“魁梧英俊,两眼炯炯发光,神仙般威严”,但不久随着他的失势,其人就从画中的领袖身边消失;照片似乎是如实记录,但仍有诸多问题,比如角度、取舍、解读,甚至后期加工,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就称“照相机会说谎”……
不过,“撒谎”的图像本身也非常值得研究。王笛说:“过去如果发现一个图像不真实,大家可能就避而不用了,现在完全可以寻找一下后面的玄机。”陈仲丹也认为,图像失真给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课题,可以就此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出于完美主义的需要,还是权力意志的表现,抑或是其他原因导致对真实的消解和颠覆,“这样或许就可以在研究‘失真’的过程中接近另外的‘真实’” 。
图像的运用,并不能减轻我们解释历史的难度,如果运用不当或“上当”,反而削弱对历史的判断力。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在《图像及其历史》中,阐述了图像证史必须加以思考的几个方面,涉及图像的品质、图像的多义性和欺骗性、风格的历史意蕴等。除了要识别出“造伪”的图像,更要警惕图像不经意挖的那一个个“坑”。邓菲指出,一些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古画中的服饰去复原当时的历史与社会,“但习俗、风格、传统会延续或滞后,以王朝断代有时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使用哪个朝代的图像资料时,也不能妄断里面呈现的就是那个朝代的情形。比如,宋画中其实有不少是唐画的摹本,里面的服饰体现的是唐代的风尚而非宋代的。”
怎样才能用好图像资料?李星明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核心就是,不同类型的图像材料“陷阱”不一,要区别对待。针对传世的图像史料,如卷轴画、书法等,如果有鉴藏史、流传有序的话,完全可以当作可靠的资料直接使用。万一鉴藏史不明确,首先就需要断代、证伪。李星明再三强调,用到那些争论了很多年都没办法下定论的材料时,务必要将其现在面临的问题交代一下。“比如年代有多少可靠性,学者们的观点有哪些,都应该作为注释放在下面,以降低使用这些材料的风险。”针对出土资料,他告诫我们一定要经考古学方法整理过才行:“考古发掘不是乱挖一气,挖出一个拿出来一个,而是放在原地不动,保留相对位置、空间关系,再进行记录、画图、拍照,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共存关系’。只有解释整个文化综合体,弄清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古人在布置、排列这些东西时,所留下的思想观念方面的信息。”
邓菲把对图像的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研究主要看图像里有什么,讲了什么故事;外部研究就是探讨其社会性、政治性、历史性等。她指出,外部研究经常会呈现多元态势。“以《清明上河图》为例,其中的市井百态、社会生活等,大家谈的都差不多。但为什么要画清明上河图?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不同学者有不一样的结论、观点。有学者就从船和桥即将‘相撞’里看出‘盛世危机’,有学者则从百姓安居乐业里看出政治清明……”邓菲认为,图像不会单独、凭空出现,围绕着它可以延伸到外部更大的范围,比如围绕书法作品的就有书法家个人、社会交游、政治史等多个研究取向,“研究角度、方法不同,同样的材料就会有不同的诠释和结论。”王笛认为,这种图像解读的多元性(文字资料何尝不是?),不但不会增加我们使用图像来研究历史的困惑,反而说明了用图像研究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图像都可能包藏多层含义,不存在所谓“唯一正确的解读”。
“左图右史”图像“无语”却胜千言,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如影随形。但从学术史来看,图像和历史研究的“缘分”一点也不深,两者经历了曲折的分分合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界重文轻图,图像资料只是“辅助”、“帮腔”、“陪衬”……蓝勇一连用了好几个词来描述图像的边缘地位,并为其“鸣不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它可能成为幼儿识读的玩偶,而文字才是成人传魂的游戏。”或许现在,不少人的潜意识中还是认为,对生僻晦涩的文字作诠释咀嚼往往更具学问,而图像给人的感觉是通俗的、简单的、低级的、幼稚的,上不了历史研究的台面。
西方学术界对图像的利用和研究西方直到近代才开始关注图像作为史料的存在。陈仲丹进一步作了解释:“近代,注重抽象推理的理论建构样式在西方发扬光大,学人热衷搭建庞大精致的理论框架,自然影响到图像研究。而且,西方近代文化兴起的文艺复兴,绘画是其中成就突出的门类,加之中世纪宗教文化中圣像学的遗产丰富,都使得西方在图像的研究利用中似乎处于领先地位。”
18世纪中期以前,以某一历史遗迹或者某一实物为材料的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把罗马陵寝用作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证据,将贝叶挂毯作为研究英格兰历史的主要史料……18世纪中后期,西方开始普遍重视图像的价值,同时在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中,进行图像史料的采集。比如,18世纪末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随军带去大批学者,负责测量和绘制埃及文化遗址,搜集和整理文物。利用这些资料,后来出版了20卷的《埃及志》,包括9卷文献、1卷图版说明、10卷图版集,收录图像3000多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善用图像资料的学者同时也是艺术家,比如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前者把图像和历史遗迹称作“人类精神过去各个发展阶段的见证”,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被曹意强视为“图像证史的典范之作”。曹意强评价布氏“审慎地、隐然地‘图像证史’,不但证出了一部震撼世界的意大利文化史,而且建立了以论题为经纬编织有机的文化史的新范式”,他同时强调应正确理解“图像证史”的内涵,“倘若仅仅证出一部艺术史,而非阐明舍弃图像而不能证、不能发之史,如此的‘图像证史’只不过是艺术史的翻版而已,而且往往是蹩脚的翻版”(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案例》)。
当史学家尝到利用图像理解过去的甜头时,便毫不吝啬对图像的赞美。赫伊津哈就宣称“历史意识是一种产生于图像的视像”。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应以图像为先,只有通过图像,才能真正地发现往昔,才能更清晰、更敏锐、更富有色彩、更富有历史感地理解过去(曹意强《图像与历史:哈斯克尔的艺术史观念和研究方法》)。虽然在意识到图像的风险后,晚年的赫伊津哈作了反思,对图像的历史作用持两面态度,但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合法地位已经无法动摇。据邓菲介绍,此时的欧洲各国,广泛收集历史遗存、建立博物馆,以展示各自民族的辉煌历史。而赫伊津哈自己也为倡导建立历史博物馆付出了毕生努力。
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图像的利用逐渐上升到理论层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德裔学者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创立的图像学分析样式。他在1939年写作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中,把对图像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前图像学的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主要关注“自然意义”,由可识别的物品和事件组成;第二层次是严格意义上的图像学分析,主要关注“常规意义”,如图像中的战场是某场具体战役;第三层次是图像研究的解释,关注“本质意义”,即“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图像正是在最后一个层次上成为历史的证据(彼得·伯克《图像证史》)。陈仲丹表示,潘氏的分析样式已成为图像证史的经典解读模式。
《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是英国最具权威的史学刊物之一,彼得·伯克对发表文章使用图像的数量作了统计后发现:从1952年到1975年的20多年间,该杂志没有发表过任何含有图像的论文;1970年代,只有两篇带插图的文章;到了198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14。王笛认为,在西方历史学研究中,198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图像的使用,使大家重新定义了史料的含义,扩展了对历史的认识,丰富了研究方法,也充实了对历史的想象。”他指出,过去在讨论新文化史兴起时,经常会提到“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但却很少意识到,同时也出现了“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图像转向’在建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把重点放到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身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内史学界依然处在“图像转向”中 虽然图像跟艺术不能混为一谈,图像所表达的东西远远超越艺术,但19世纪艺术史学科的成型,无疑使得西方在利用图像解读历史方面的功夫越来越炉火纯青,理论体系也日益成熟。陈仲丹认为,中国学界看似“迟钝”,其原因不在于图像本身,而是中西方文化特征的不同:“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性,偏于对具体事物的归纳整合,少于对抽象思维的逻辑推断。举例来看,先秦时期的《孟子》《庄子》用讲故事的方式说道理,与古希腊《理想国》《政治学》的叙述风格就大不相同。”他强调,不同地域思维方式有差异,谈不上中西方利用图像能力有“高下优劣”。
事实上,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素有“左图右史”的传统。据李星明介绍,先秦时期的《山海经》记录了很多地理、物产、民俗、宗教、山川鸟兽等内容,本来也有图像,只是在流传的过程中日渐遗失,最终只剩下文字。更有研究认为,古《山海经》就是地图,或者以图为主,文字是附图说明,今《山海经》乃古《山海经》亡图而残存的文字说明而已(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当代志书编纂教程》)。这还不是个孤例,民国地图史学家王庸就曾总结过:“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黄苇《方志论集》)
中国古代地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曾迎来一个“图经时代”。东汉时,巴郡太守但望的奏疏中提到《巴郡图经》,为今天所知的最早的图经;东汉顺帝时,侍中王逸还作过《广陵郡图经》,可见,东汉就有图经是无疑的。究竟何谓“图经”?中国古文献学家王重民1950年代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的地方志》一文,就作了明确解释:“最早的图经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对图作的简要的文字说明。”
到了宋代,时人言语中处处流露出对图像的重视,尤以郑樵的感悟为深,经久流传。他在《通志》总序里即言:“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在《图谱略》中又说:“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在《索象》《原学》《明用》里,都能找到相应的阐释,如“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等等。宋以后,文字气场越来越大,在表现思想方面的长处凸显,与此同时,由于传播相对困难、表意欠缺深度和准确性,图像的重要性日渐式微。蓝勇不免感叹:“以前那种以图为主、以经为辅的时代,变成以字为绝对主体、附以插图的时代。”
这之后,出现过一个可以重拾图像地位的机会,那就是形成于北宋、发达于清朝后期的金石学。“这是以器物上的铭文和石刻碑碣上的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李星明指出,金石学除了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清代晚期书法的发展跟金石学密切相关,很多书画名家如翁同龢、金农等,写的字有所谓的“金石味”,就是这个道理。“但它的缺憾就在于,没有将器物本身的造型、位置等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思想观念的表达来看待。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讲,书法也是一种图像,但远远不够,毕竟那些从古代发现的铜器、石刻,包含了丰富的图像和历史文化信息。”李星明说。
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材料的利用还是较偏颇的,总体来讲,较重视文献尤其是传世文献。与传统史学不同,国内现代史学始于20世纪初,可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作为标志。梁启超强调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并推崇史料的价值——“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由于可信、可用的史料难得,就有必要扩大史料来源。王国维、
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呼吁重视甲骨文献、简牍文书等地下史料,王国维还提出“二重证据”说,指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要相互印证,陈寅恪也强调要用不同证据。此外还发现了一批档案文献,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及“八千麻袋”的清宫大内档案等,都将史料利用及史学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陈仲丹认为,这些都是受到西方科学型史学理论方法影响的结果。
虽然在迭出的新史料中,史学大家们也对图像流露过浓厚的兴趣,但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化。郑振铎就如此批评过“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史学家仅知在书本文字中讨生活,不复究心于有关史迹、文化、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之真实情况,与乎实物图像,器用形态,而史学遂成为孤立与枯索之学问。”即便这样,郑氏所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免不了只是个“插图本”。
邓菲介绍,西方的历史研究以欧洲史等为主流,欧洲史、中世纪研究等等,率先利用或开创了新的概念、方法、视角,其他领域、文化的历史学家再学习起来,“在引介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汉学家们无疑发挥了桥梁作用”。

早年来中国考察的西方汉学家基本都是探险家,像法国的沙畹、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等,此外还有日本的常盘大定、关野贞、水野清一……调查了不少中国古代的遗址遗迹,比如庙宇、宫殿、墓葬、石窟、祠堂,留下很多图集、游记。有些集成册子发表了,有些作为馆藏一直搁置在那。1980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内学者开始对这部分内容产生兴趣,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我们现在也在进行着一项类似的工作。”据李星明介绍,常盘大定、关野贞1920年代在中国作了几次探查,汇成《支那文化史迹》,共12册图集、2本说明,“他们拍到的那些石窟和古建筑,很多早已变样甚至消失,《支那文化史迹》便成为还原当时模样的唯一证据。我们争取明年完成出版,以利于更多学者使用。”
在李星明看来,历史研究的选题内容和方法手段往往跟一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关系密切。“在上个世纪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中,中国史学研究频频受到干扰,直到80年代开始有较为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以后,逐渐活跃起来,才可能有新的思考。”他感叹道,中国学术的创新思维不够,缺乏自己的学术话语,“从这点来看,图像与历史的融合交流还应该进一步深入”。
国内史学界目前的发展态势,王笛认为依然处在“图像转向”的过程中:“如果用彼得·伯克的方法做个判断,就会发现国内史学杂志中使用图片的文章比例始终比较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几乎看不到图像,即使有些杂志采用配图,也多半为了活跃版面,图像没有成为内容分析的一部分;而且这样的配图做得很小,就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已。相比较而言,《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或者《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的图像,情况就大不一样。”
邓菲也指出,有些历史学者有意识地不去用图像,“一旦要用,就跨到另一个领域,需要相关的训练,学习如何使用另一种史料——怎么看图、读图,如何读懂、分析,多少会有顾虑。”李星明坦言:“中国的文献资料确实浩如烟海。也正是因为多,传统史家认为光靠文献、终其一生在故纸堆里面找,就足够了。”他认为,对部分学者来说,其研究领域中要解决的问题,或许真的跟图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对文献依赖程度高也能理解,但考虑到整体的历史学发展,就不能这么说了。
虽未成为主流,但趋势已露无疑。可贵的是,很多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图像和文献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看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在上世纪90年代做思想史研究工作时,就已经非常重视地图、传世画作、出土器物等,还就图像资料的使用发表了一些列文章,如《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复旦文史研究院创建之初,作为首任院长的葛兆光就把艺术史、图像研究等部分纳入进来,作为专门的研究方向。这在李星明看来,算是当时中国史学界颇具前沿思想的举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