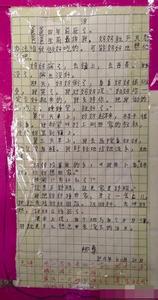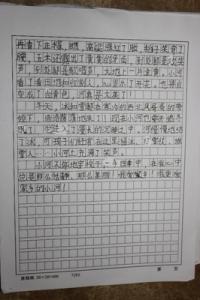□ 福建蓝朵
一滴水,站得高时,是青海湖的蔚蓝。想得远时,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浩瀚。
静坐在一滴水里,像一林竹子端坐在郑板桥的心里一样。竹子扎根深土的蠕动,像监控心跳的曲线,平静中起伏,起伏中趋于平缓。竹子探头时的挣扎,拔节时的喜悦,脱叶时的无奈,返青时的窃喜,全在他的胸中。只需一砚清墨,一尺素宣,不仅能养活一林竹子,还能引来一林鸟语花香,还有一卷诗篇。
站在一朵花上的水,是昨夜走失的一点露。揉着惺忪的双眼,才睁开一个眯隙,阳光火红的箭,就硬生生地穿过他的胸膛。还来不及细想,刚才做的梦里,是否有花的妩媚,花的娇嫩。就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只有才站定的位置,还印着一痕潮湿的脚印,那印痕,是吃奶的孩子看到乳房时未干的泪痕。
以露为镜,映照一朵花的一生,凌寒的傲梅,坚强的底线是春天。暗香的昙花,美丽的终点是黎明。更不用提及那些名不见经传,号不上榜文的无名氏了。
挂在一线麦芒上的水,是农民额上刚刚洒下的汗。这一滴水从春分一直走到芒种。从垄头的麦青一直走到垄尾的麦黄。从播种机的车轮一直走到扬风机的仓口,从来没有间歇过。这滴水握过乡亲长茧的双手,闻过他们臂膀黝黑的气息。也曾跨过他们那张张胴亮的脸上的沟沟坎坎。这滴属于乡村,属于农民的水,在这个夏天,站在麦芒上,掷地有声地落在了乡亲脸上,落在了憨厚的笑声里,走完了他的一生。
住在一节诗歌里的水,是诗人眼中的泪。是一舟载满忧愁的舴艋,一堆山头新添的坟头,也是一座楚王朝宏伟的宫殿……从双溪的源头,从海峡的彼岸,从汩罗江的江心,从诗人的双眸,源源不断地溢,滔滔不绝地涌。

直至装满了一位帝王的词,才汇成一江向东的春水,浩浩荡荡地流进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史册中。而后,又排山倒海地从《长江之歌》,从《我们是黄河泰山》的歌声里,流进一个民族的血液里。无论,你从流沙河,艾青,还是舒婷的诗里,还是从每一寸黄皮肤,每一缕黑头发里,都可以寻到这滴水的源头。
那水还是侠士剑鞘在腰,佩剑在手时,剑尖滑落的血。一滴历经雾,云,霜,雪轮回的水,生机盎然地屹立于高处,足以征服任何顽石。无数个瞬间温柔的撞击,累积成了一种恒心与毅力的表像,烙在每个路人的眼里,每个诗人的心中。因此,还沉淀出一个叫“滴水穿石”的亘古至理。
在一滴水里打坐,禅起见水,禅定见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