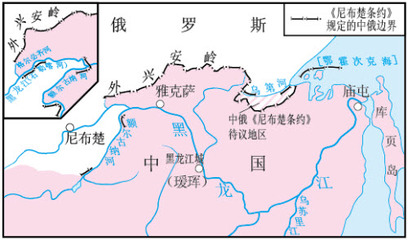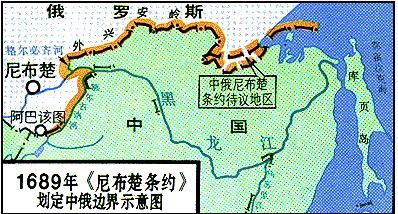“到俄罗斯啦!”陈宇豪兴奋地和同学们分享中国俄罗斯使领馆发来的短信。
这天下午,我们的车来到了买卖城,即蒙俄边境线上蒙古一侧的阿勒坦布拉格城。买卖城跟俄罗斯小城恰克图之间有铁丝网隔开。中国移动在处理信号时误认为我们进入了俄罗斯边境。
“为买卖城战役中牺牲的中国军人默哀!”陈宇豪下令道,9名学生面向北部茫茫的草原,在寒风中低头肃立。北部草原是买卖城旧址所在地,那座繁华的中国商业城市1921年毁于一场战火,2000名中国守军兵败于此。从此,中国通往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中断了。
陈宇豪说,“无论战役成败,也无关北洋军的属性,牺牲在这里的中国军人为国家统一而死,是中华民族的英烈,我们应该向他们致哀。”
“是!”另外8名学生一致响应。
“历史没有记住那些不屈的灵魂,但是我们回到了这里,凭吊英烈,”张智伟说。
边境地带是茂密的草场。蒙俄两道铁丝网之间拉出了近50米宽的间隔地带,中间放有2条军犬。马向阳和王一波背着老师和同学,绕到军犬身后,翻越铁栅栏,穿过隔离带,悄悄地逼向俄罗斯一侧。
“我们在隔离带上行走时有些心惊,怕被蒙古边防兵看到。到了俄国边境,那一侧的铁栅栏很高,我们把手伸过去,各拍了一张照,还拔了一棵草,留作纪念。然后,我们装作若无其事的回到了大巴车上。”马向阳事后承认自己做的错事时说。

在蒙俄边境处,苏赫巴托尔博物馆苍凉地矗立在草原上。这个博物馆是为纪念1921年苏赫巴托尔在买卖城领导蒙古革命党战胜敌人,赢得蒙古独立而建。
“请问你们的敌人是谁?”张进宝突然问讲解员。现场旋即陷入一阵尴尬的沉默。
“是你们,你们中国人。”半晌,讲解员轻轻地说。
博物馆用一副全景沙盘展现了买卖城战役,称苏赫巴托尔领导400人的游击队,击败了2000人的中国守军。一面巨幅油画展现苏赫巴托尔发表胜利演说,牧民欢庆民族独立,戴花翎帽子的清朝官员跪地求饶,两个长辫子的中国衙门官员仓皇逃窜,蒙古贵族坐着马车在一旁观望。
博物馆楼梯正对的墙面上金色大字题写的蒙文赞歌,大意为:“我们打倒了中国军阀,解放了自己的国家。感谢英雄苏赫巴托尔,恰克图的土地上,第一次升起蒙古国旗。”
事实上,苏赫巴托尔的胜利靠的是苏联红军的支持。当时国内正处军阀混战,中国政府坐视蒙古独立。离开博物馆前,我在留言簿上写道“历史已过去,买卖又回来”。
苏赫巴托尔博物馆外不远处,是2006年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里,中国、俄罗斯、蒙古、布里亚特和韩国五国国旗在空中飘扬着。小城路边随处可见红色圆木搭建的俄式房屋,有旅馆、修车铺、台球厅、乒乓球厅、卡拉OK厅、便利店等。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每年都会有10万头骆驼驮着张家口的茶叶经过这里送往恰克图。最早的欧洲电报先发到恰克图,然后再用骆驼送回纸质消息。文献记载,中国政府就是通过恰克图转来的电报得知德法战争的消息的。
傍晚时分下起了小雨。车沿着蒙古俄罗斯边境线行走,这一带生长着茂密的松林和桦树林。传说这一带是苏武北海牧羊处。到了密林深处,车子开不进去,大家拖着自己的行李,踩着湿漉漉的积了厚厚的桦树叶和松针的小石子路走到了宿营地。
每两个同学合住一间小木屋。小屋内湿冷,没有炉火,窄小的木板床上没有被子,只有一个床单。枕头套上一层脏兮兮印迹。木屋的门关不上,好像好久没人住过。树林里的蚊虫不停地冲撞门窗,试图飞进小屋。宿营地只有一个在地上挖了个深坑、上面架了两条木板的简易厕所,男女不分。厕所里没有电灯。其木格说,“大家可以在树林里的空地处解手。”
早起,离我们营地十步之遥的桦树林处,有5名持枪蒙古士兵来回巡视。学生走近他们拍照,1名士兵猛地转过身来,拿枪紧盯着他们,并摆手制止拍照。
出了桦树林,我们回到了草原,去寻访成吉思汗抢回妻子孛儿帖时立下的地标性大石头。汽车在草原上沿着前人压出的两道车辄走。跑了半天,司机忽然停车,说迷路了。一个穿着皮短裤的牧羊少年给我们指了路。我们在布利亚特部落的一片牧地上远远地看见了这块巨石。巨石紧挨蒙俄边境线。
“我在这里找到了我要找的人了,大家在这里休息吧。”在一片平坦无际的大草原上,一块孤零零的巨石上刻着成吉思汗找回他爱妻时说的话。800年前,铁木真在这里夺回了自己的妻子。夺回来的孛儿帖已经怀孕,成吉思汗没有嫌弃,反而高兴地认为自己家里又多了一口人。
“到底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的路就来看这么一块石头呢?”一个学生不解地问同伴。
“来一次蒙古,总要感受下成吉思汗征战天下的豪迈和儿女情长的英气。”曾泽宇说。
“Needfire?”(要生火吗?)17岁的蒙古姑娘抱着一团白棉布走进万宁宁的蒙古包。“Yes,please!”冻得浑身颤抖的宁宁连忙说。漠北草原夏夜里气温只有5摄氏度。
蒙古姑娘笑了笑,在火炉边蹲下身子,挑选了四五根细小的柴木搭在炉子里,再塞进些碎柴屑。姑娘用力扯下一块布塞进炉子里。这时,她的手被柴木划破了。宁宁抽出一张纸巾递给她,她笑着接了过去攥在了手里没有用,用嘴吸了吸流出的血。然后用火柴慢慢点燃棉布周边,盖上火炉盖子。火光透过炉子的缝隙闪射出来。
蒙古姑娘起身走出蒙古包,要帮宁宁把门关上。宁宁走出蒙古包,用刚学的蒙语说了句“Baiyesa(谢谢)。”蒙古姑娘回头冲宁宁笑着说“Goodnight!”
万宁宁关了蒙古包的灯,火炉透出的红光照亮了半个蒙古包。火苗跳动,包顶影影绰绰。“炉火里噼噼啪啪的声音极像我小时候妈妈在家里用火炉烤小麦,”万宁宁回忆说。
这是宁宁和同学们最后一晚住蒙古包。1周来大家多个晚上在蒙古包里过夜。在漠北的夏日寒气中,呼吸着空气中弥漫的膻味,进入梦乡,想象自己是2000年前的细君公主,走进乌孙王大帐时吟诵的名句:“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在另一顶亮着灯的蒙古包,刘哲铭蜷缩在床上读范子烨80年前为《内外蒙古考察日记》写的序:“下午,风雪交加,入晚,风更烈。我们九人,屈促在驼夫的一个小帐房内。……风吼雪飘,益增凄凉,人人相对无言,唏嘘长叹,种种感想,涌现脑际,不禁想见苏武留胡的情况。饭后,大家急拥厚被,和衣挤卧,风声益厉,帐房将拨,人人惴恐。眠既不得,起又不能,这种太古生活,凄凉生活,可说是生平未有。”
当大家都躲进蒙古包里取暖睡觉时,曾泽宇一个人站在湿冷的蒙古包外,她被草原上空低垂的银河震撼了。她没有快门线,没有三脚架,忍住寒冷,手指一动不动地在快门上按了两分多钟,记录下了此生未曾见过的星空。她回到蒙古包,冷风不断从缝隙灌入蒙古包,寒气逼人。
泽宇打着手电筒,走出蒙古包,找人来生火。遇见一个懂中文的蒙古男子,男子带她敲开一间蒙古包,借到了火柴。火着了两小时,又灭了。这时突然有一蒙古青年男子闯了进来,他抬头看见屋里三个女生,发现走错了蒙古包,即刻退出去。泽宇赶紧追出去拦住他说,“您会生火吗?”他没有听懂。泽宇又用英文问了一遍,他还是没有听懂。泽宇只好拉他回到蒙古包,他身后一个拿酒瓶的男人也跟了进来。泽宇指着火炉,蒙古男子看到火灭了,掏出打火机,耐心的又把火炉烧起来,泽宇道谢后,两男子转身离开。泽宇赶紧锁好门上床躺下。
“我躺在铺上,心跳加速,双拳紧握。”泽宇回忆说。
第二天傍晚,我们乘车到了成吉思汗国际机场。机票上没有写登机口,大家以为机票打错了,进去之后发现,乌兰巴托的国际机场只有一个登机口。飞机上有很多西方人,大部分都是去北京转机的。起飞后不到两小时,我们回到了北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