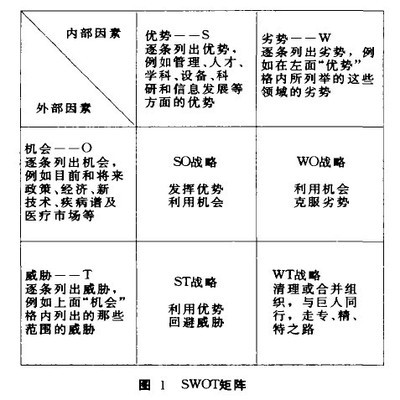汉语“报告文学”是英文“Reportage”的翻译。中国关于“Reportage”的认知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亦称“报导文学”和“特写”。由于“左联”的大力提倡,人们特别强调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和鼓动性,甚至视为能够有力宣传阶级革命的文体。关于这些,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有说明。该书把报告文学放在散文中讨论,指出:报告文学始见于五四时代,如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但有意识提倡这种文体则和30年代左联分不开,左联刊物介绍了捷克报告文学家基希及作品,也发表了很多国内作者的报告文学。接下来列举了夏衍、萧乾和范长江的代表作,并认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纪实性吸引了大批读者①。这也是文学史教材的通常介绍。但通常介绍也存在笼统问题。如思想认知方面,瞿秋白、夏衍的报告文学与萧乾、范长江的报告文学就有明显区别;左联提倡报告文学的战斗性鼓动性,当时也是一种看法。如曹聚仁就认为钱杏�编辑的《上海事变和报告文学》、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宋之的《1936年在太原》缺少新闻性。指出教材介绍问题,不仅因为公共描述缺乏必要区别,还与特定意识形态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称报告文学为“文学轻骑兵”,强调的就是及时反映新社会新人新事新生活和快速传达国家意志。既然是战斗性文体和政治先行的“文学轻骑兵”,那确实不需要什么学术意识。再联系大量文采飞扬的“表扬稿”、组织行为的写作和添油加醋的有偿报告,与学术意识就更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遗憾的是报告文学的不少问题也由此产生。
问题有种种原因,而我以为缺乏学术意识恰恰是重要原因。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或学术性,并非指纯粹学理研究,而是以相关的理论、知识、价值来审视和分析问题。学术意识强调的理性研究、科学方法、探索精神和深入考察,对报告文学更有普遍意义。如报告文学要真实,但“真实”是个复杂存在,包括全面真实、部分真实、现象真实、本质真实等,这就需要科学理性的分析。如此才能揭示事物因果关系与内在根源,也不可能去弄那种片面表面更遑论虚假的报告。有些题材还要求写作者必须了解相关理论知识。如以前我们坚信“人定胜天”,自然只是利用与征服的对象,对现代生态文明几乎没意识。而写生态题材的报告文学,应该以生态系统整体观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指导,这就需要了解生态学理论。“生态盲”就无法写生态。从中外优秀报告文学看,学术意识往往是成功的基本条件。并非说报告文学写作都必须如何强化学术性,但学术意识肯定有益无害。
一、文体本身的包容性
是否允许或说是否需要学术意识,首先要了解报告文学文体状况。而这与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相关。。英文的“Reportage”,基本视报告文学为客观传递社会信息的报道性文体。如1964年版英国《简明牛津词典》对“Reportage”的解释是“给报刊报道事件的典型文体”;1961年版美国《韦伯斯特大词典》解释要详细些:“指这类作品――对于直接观察过,或者有文件资料认真记载下来的事件和场面,给予真实的详细的描述。”这些解释侧重新闻性,视“Reportage”为报道社会新闻和社会信息的新闻通讯类。由于高度概括,词典解释并不周全,很难说明报告文学文体的实际运用及其多样化状况。
中国对“Reportage”的认知始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创作实践发展,人们对其文体认识也有变化。迄今为止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新闻的特殊门类;二是文学的特殊门类;三是文学和新闻的联姻。这三种观点延续多年。新时期后一般也认可报告文学是文学和新闻联姻,报告文学出现在文学教材和新闻教材的双重身份也可证明。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报告文学有如此界定:“文学体裁,散文中的一类,是通讯、速写、特写等的统称。以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为题材,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而成,具有新闻特点。”②将报告文学视为文学体裁但强调了新闻特点,还是认可了文学和新闻的结合。但联姻说也有模糊。虚构是文学本质,将报告文学归为文学就带来虚构与非虚构界限难以把握。即使“适当的艺术加工”也不能加入虚构。事实上报告文学的想象、议论、抒情都要慎重。当年徐迟报告文学的“诗化”倾向和细节虚构就引起过争论。
第四种看法则认为报告文学是综合了多种写作门类的“杂交体”或说“信息系统”,是融合了文学性、新闻性、历史性、学术性等写作特征的综合文体。文学的描写与感受,新闻的真实与时效,历史的考证与把握,学术的研究与分析,都能在报告文学中得到交织性体现,只是具体作品侧重不同。就国内情况看,“杂交体”说法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中国报告文学发生期的杂体互文。当时报刊出现了很多文风新颖议论风生的时评、政论、游记、通讯,将新闻报道、政论时评和文学描述结合起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胡适等文化名人都写过这类文章。梁启超最突出,梁式“新文体”(因与《新民丛报》有关亦称“新民体”)风行一时。杂体“报告文学”固然传达新闻事件和社会信息,但常以时评政论取胜,包括文化分析。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和《新大陆游记》。杂体互文状况一直有所延续。曹聚仁谈到杂体互文时曾指出:“我们这一代的政论家散文家和新闻记者,几乎三位一体,成为不可分的时代产物。”③不过那时“报告文学”与后来有较大差异。20世纪30年代则逐步明确了报告文学的文学和新闻联姻。但孰重孰轻仍有不同看法。如曹聚仁认为报告文学“新闻”是主要的,“而那艺术性的描写,只有加强对读者诱导的作用,并不能代替新闻的重要性”。因此他看重早期黄远生、邵�h萍的通讯,对范长江的《西南行》《中国的西北角》和《西线风云》也非常欣赏,认为范长江是“纯粹的新闻记者”,其社会通讯和战地通讯见解精到而文笔也佳④。当时周立波也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他应当像社会的新闻记者一样的搜集他的材料。”⑤ 第二个时期的“杂交体”说,则源于新时期“全景图”报告文学的蔚为大观。所谓“全景图”,通常解释是这类“报告”是种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审视。如《唐山大地震》《神圣忧思录》《阴阳大裂变》《世界大串联》《温州大裂变》《百万大裁军》《中国的要害》《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体育界》《中国的乞丐群落》《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眸子》《中国铁路协奏曲》《兵败汉城》《强国梦》《西部在移民》《土地与土皇帝》《古老的罪恶》《沉沦的国土》《只有一条长江》等等。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不仅题材重大,而且明显融合了文学性、新闻性、历史性、学术性等综合性写作特征。
上述四种观点由于涉及实践情况,因此应该历史地看待合理与否。况且报告文学也应多样化。不过我还是赞同“杂交体”观点。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从文体理论看,这种界定能涵盖报告文学文体所有特征,是最全面的解释;二是从创作实践看,大量作品也显示了这种杂交体性质,长篇报告文学更为明显。“杂交体”不仅显示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包容性,也给写作主体提供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广阔空间,当然也包含学术的研究与分析。
二、保障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如果说提供学术意识参与的文体包容性,还属文体本身特征,那么就学术意识在报告文学写作的合理性看,能够更充分保障报告文学真实性,则无疑是个首要理由。
人们常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真实”在现实世界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除前面说到的全面与片面、本质与现象、内在与表面等情况,人们的“真实观”更是受到种种因素制约。这当然就需要学术意识强调的理性研究、科学方法和深入考察。报告文学写作显示的学术意识也体现在多方面,包括历史研究、文化分析、心理分析、社会学研究、科学的调查方式和统计方式等。曹聚仁认为范长江的社会通讯和战地通讯“见解精到”,就离不开研究分析,就带有学术意识。不妨举些典型例子来说明报告文学与学术意识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告文学高潮中,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最重要。它们主题高度一致,即歌颂志愿军英勇表现、中朝友谊和痛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政权(南朝鲜李承晚政权)。这些作品激起了中国人民爱国热情,也充分传达了当时国家意识。但这场战争涉及问题复杂,如国际背景、国家关系、交战各方的战争意图、战争过程状况等。由此也会想到一个问题:当抗美援朝题材报告文学成为特定的精神鼓舞和舆论宣传时,客观性能否得到保证?
相较我们的高度一致,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则呈现了多种情况和多种思考。该作既是全面描述朝鲜战争的历史著作,也是全面展示朝鲜战争的长篇报告文学。单是第一章《战争时刻》就颠覆了我们传统看法。从中可知朝鲜战争爆发并非我们认为的是美国发动侵朝战争,而是苏联军事顾问训练的朝鲜军队在夜色掩盖中首先突袭韩国。当时韩国前线司令官们完全蒙在鼓里,还在新开张的军官俱乐部里狂欢。正如托兰说的,这种情形跟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的美军指挥官们寻欢作乐的粗心大意完全类似。

作为史学家的托兰非常注意从历史事实出发。为写作《漫长的战斗》,他阅读了大量文献,采访了散落各地的百余战俘,并宣称“我并非以一个美国人而是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它的”。由于这种世界视野,托兰关于朝鲜战争的思考也很独特,如他认为“朝鲜战争是一部值得纪念的充满人类悲剧和洋溢着交战双方英雄们英勇气概的传奇历史,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世界性的重要史诗”⑥。认为“交战双方”都洋溢着“英勇气概”,这就完全没有“神圣化”或“妖魔化”。他还质疑朝鲜战争的意义:“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各阶层人民来说,它都是一场残酷的、愚蠢的、错误的、判断失误的、种族歧视的、带有偏见的和凶暴的战争。”并且认为“只有各个层次上大量具有人性的事例――战争上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有关战争的著述持久不衰”⑦。相对我们抗美援朝报告文学,托兰的描述和思考简直有些天方夜谭。对托兰“世界公民”立场可以商榷,但《漫长的战斗》的多角度展示、大量资料研究、辛劳采访和史学家立场的分析,无疑显示了学术意识与实际情况的充分结合。而这些显然更能呈现朝鲜战争的真实状况和复杂性。
中文版序言作者告诉我们,托�m是中国人民老朋友,“他对新中国一贯友好,怀有深厚感情”。20世纪30年代,托兰因结识一个中国好友(中共党员)和读过斯诺描述中国革命的著作,他曾想做第二个斯诺⑧。《漫长的战斗》是作者在中国出版的第六本书,用托兰自己话说“很久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对我写的客观历史表示赞赏”,而“本书也因其客观态度及反映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战争中举措的新材料而受到称赞”⑨。托兰写作素来尊重历史。托兰写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时,曾批评罗斯福总统蓄意压下事先获得的有关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此举给作者带来麻烦,受到学术界人士攻击甚至导致老友反目,但托兰坚持己见,体现了学者的独立和作家的求真。
美国著名记者也是史学家的威廉・夏伊勒,其《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是部影响宽泛的世界经典,它既是历史著作又是长篇报告文学。第三帝国兴起前期,夏伊勒作为美国记者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亲眼看到阿道夫・希特勒怎样巩固他作为这一伟大而又茫然不知所从的民族的独裁者的权力,后来又怎样引导这一民族走向战争和征服。”⑩但作者告诉我们这种难得的个人经历还是“不会诱使我尝试写这部书”,促使写书的关键原因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这就是第三帝国的迅速崩溃,使得盟国军队缴获了纳粹德国政府及其所有各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其中包括外交部、陆海军、国家社会党以及秘密警察的机密档案。如德国外交部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藏在哈尔兹山脉的古堡和矿井里,当德国守军奉命正要烧毁时,美国军队已经赶到,档案因此都被美国军队缴获。此外第三帝国大量的发言记录、会议报告、通信以及私人日记等也被收缴。正如作者所说,一个大国即使出现了政权更替,国家档案也是国家自己保存,然后根据需要而公布利于后来统治者的部分档案。而纳粹德国的迅速崩溃则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使得其档案成为记录了其累累罪恶的“世界遗产”。对于研究者,这些历史资料当然太宝贵。夏伊勒收集的资料数量可谓惊人,单是作者采访纽伦堡审判的前半期审讯时,就收集了成捆的油印副本和后来出版的四十二卷证词和文件,还有许多重要文件的十卷英译本等等11。尽管无法全部浏览档案,但作者还是努力翻阅了其中大部分资料。除阅读数量惊人的文献,夏伊勒还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查。如果说纳粹德国机密文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那么作者的丰富学识和严谨态度,也使此书体现了丰富思想和深刻洞察。这部“纳粹德国史”显示的全面和真实也感动了大量读者。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罗珀称赞它为“杰出的研究成果,生动感人的叙述”12。值得一提的还有该书出版情况。由于“部头如此之大,注释如此之多,价格如此昂贵”,作者和出版社起先都以为只有部分读者感兴趣,市场销售情况可能不理想。而“我的演讲代理人曾告诉我,人们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已不再感兴趣”,所以开始只印了一万二千五百册13。但出乎意料的是甫一问世便受到热烈欢迎,引起世界很多国家读者的关注,外文译本不断出来。这就是经典的价值。 当年“中国潮”征文活动的不少作品都体现了上述特征。如陈义风《丑陋的北京人》对“北京人肖像”的文化分析,经由典型事例而概括了“北京人”的文化心理。如论“四合院文化”,归纳出“窥探癖”“跟着哄”“枪打出头鸟”“心嘴不一”“死要面子”五种典型文化现象。关于官员阶层的“紫禁城意识”,概括为四个方面:“唯上而是”的必备品格;“干什么都拿着个劲”的装模作样的官场规范;“国贵民贱”的价值观;“大行不计小节”的纵容和姑息权贵的官场伦理。这类解剖有强劲思想穿透力。陈义风还有篇《来自首都的经济内参》也体现了“深度报告”特征。该作主要揭示农民的“奸商行为”,作品告诉我们:据统计全国发现的伪劣商品大多是农村专业户或乡镇企业生产。如河南巩义市制售伪劣化肥的农民竟达几万人,涉及上百村庄。作者指出“这些伪劣商品都是和农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它告诉我们,自由涣散的农民和自由涣散的农村环境是滋生不法商人的最好的土壤”。刘汉太《中国的乞丐群落》也是典型的“文化报告”。人们对乞丐不陌生,对乞丐组织却很少了解,作品从乞丐群落的形成、丐帮组织形态、生活状况、分配方式等进行了层层剖析。从“乞丐王国”等级森严的“排座次”,从蠢猪式、贼鸥式、田鼠式三大生存方式,从好逸恶劳、玩世不恭、为非作歹等精神类型中,看见了乞丐群落的“中国式”文化心理。西方乞丐喜欢流浪者般独个行动,中国乞丐却能形成森严群体。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推出一套《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精品书系》,包括徐迟《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大雁情》、柯岩《奇异的书简》、理由《扬眉剑出鞘》、徐刚《沉沦的国土》、赵瑜的《马家军调查》、胡平《中国的眸子》、邓贤《中国知青梦》、卢跃刚《以人民的名义》、何建明《根本利益》和陈桂棣《淮河的警告》。实际是十一位报告文学家各以一篇代表作为名的作品集。它们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中虽是沧海一粟,由于时代关系也显示了思想差异,但在不同现实语境中都有代表性。李炳银和袁鹰作的“总序”开篇说道:“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中,报告文学始终伴随着民族前进的步伐和人民的喜怒哀乐。报告文学是一种不断给人以激动、振奋、思考的重要文化参照对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报告文学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中国现实文化的重要表现对象。”14这种关于报告文学文化功能的看法无疑中肯,而文化功能对“深度报告”恰恰非常重要。
四、增强独立意识
学术意识对报告文学的重要,还体现在其通常强调的独立思考能增强报告文学创作的独立意识。这从十七年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教训也可看出。当时报告文学普遍存在“紧跟指示”和“图解政策”问题,带来“主题先行”的主观性、“图解政策”的机械性和报喜不报忧的虚假性。由此出现的多是“表扬稿”“宣传稿”。当时极左思潮和经济冒进等非常需要独立思考。“文革”发生的血统论、长官意志等以往已存在,只是“文革”中变本加厉。巴金曾感叹:“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15所以巴金《随想录》不断反思自己当年的“奴在心里”而提出“全民忏悔”。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不仅逐步改变了报告文学随波逐流现象,也使作家越来越意识到独立思考的必须。
新时期初期报告文学作家中,黄宗英和理由的创作显示了很强的独立意识。稍后出现的“新生代”报告文学家,独立意识则成为普遍特征。“新生代”作家大体分为作家型和记者型。麦天枢是记者型作家代表,而赵瑜、胡平、贾鲁生等则是作家型代表。
独立思考艰难也来自现实原因。黄宗英曾告诉读者:1983年大年三十晚上写完《小木屋》后她流泪了,不是因为高兴而是悲哀,因为作者发现“自己从1978年春天中国科学家代表大会到1983年的这个夜晚以来,所写的报告文学,都是为科学家呼吁,又几乎篇篇获奖,可篇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个转运”16。理由则认为“我觉得报告文学都带有一种对新闻封闭性的挣脱的痕迹,我们写的是一些被淹没了的、歪曲了的、枪毙了的新闻”17。不少报告文学作者有同样感受。麦天枢《西部在移民》在“中国潮”征文活动获奖后,有记者问麦天枢为何写报告文学,他也说新闻报道方式受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知、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写报告文学18。但转向后仍有现实压力。如其《土地与土皇帝》披露了戴满光环的全国劳模李计银的劣迹:明明是凶悍霸道的“土皇帝”,却被渲染成“村民贴心的党支书”;贪污公款却有《拒腐�g,永不沾》的报道;村治保会实际成了他为非作歹的工具。李计银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显然是种现代封建怪象。但作品发表后麦天枢却受到巨大压力,只是没有屈服于“可怕的真实”19。贾鲁生《庄园惊梦》也写了“土皇帝”,所写“中国第一黄金村”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党支书孙良林竟能像管牲口似的将全村人统治起来,村民们见了外人只敢异口同声说“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是多亏有个好书记”。愚怯至此难以思议。不过严峻现实也使麦天枢认为报告文学“在中国这种文化形态下是最便利的启蒙方式”,而且中国知识分子最大弱点是被农民文化浸泡得皮软肉酥,保持独立意识太难20。《问苍茫大地》对农村“民主选举”的揭露同样体现了作者独立意识。
胡平是全景图报告文学代表作家,独立思考也是其突出创作特征。如《中国的眸子》讲述的是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和钟海源在“文革”中因追求真理而被杀害的冤案。这篇反思极左政治的力作摆脱了以往同类题材的思维模式,不再止于诅咒“四人帮”和对极左思潮的表层批判。为了揭示两位热血女子被害悲剧的文化根源,作品对当权者的骄横、群众的麻木、告密者的卑劣、刽子手的残忍等时代疯狂现象作了深刻分析。作者还以中世纪罗马宗教法庭的黑暗历史作比较,李九莲和钟海源从坐牢到被枪毙的过程,显示的法律状况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异端法庭”相当接近,就是野蛮专横无法无天。全景图报告不再兴盛后,他仍以《千年沉重》和《苦难的祭坛:中国1957》继续其历史的独立反思。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