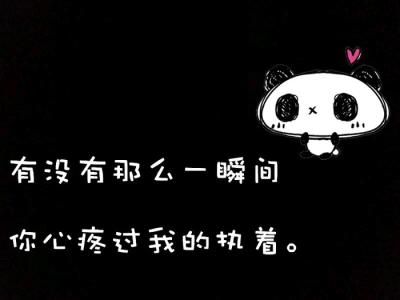在我终于想要好好写一写父亲时,才蓦然发觉,那些稀松琐碎的日子早已固执地干涩在笔尖,无处捕捉,难以成章。
我对父亲的情感一直都很稀薄,甚至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光里,他对于我都是以“可有可无”的身份存在着。从小到大,除了小学时一年一度的“家长意见” 必须要让父亲亲自执笔外,别的任何大事小情,我几乎从不会向父亲主动开口要求。就连“家长意见”这件小事,也是由于母亲的“不会写字”才有了父亲的“用武之地”。每次我都是将提前翻好的档案本怯怯地递过去,听着自己咚咚的心跳声,眼睛紧紧瞅着父亲手中的笔端,在他潦潦几行终于划下句号的那一刹那就迅速抽回纸笔,然后“唯恐避之不及”地躲到另一间房屋里掩上门——是的,曾经的我是十分惧怕父亲的。
尽管无数的岁月流淌而去,尽管儿时的很多种情愫都已经遥不可及且难辨真伪,但是那种“惧怕”却异常清晰地烙在我心底,挥之不去。在很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想起那段“硬着头皮让父亲填家长意见”的小学六年时光,一种莫名的酸楚仍旧会在我心里无边蔓延。彼时年幼无知的我尚未懂得,小学那不长不短的六年,也许会是我漫漫人生几十年中,上帝安排给我的能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最长的时间。
父亲曾经站在光鲜亮丽的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二十余年,那是他无奈放弃讲台后的无数个艰难而卑微的日子 里,唯一还能让他骄傲的事情。也许是迫于生计的心力交瘁,也许是怀才不遇的难偿所愿,记忆中的父亲,那些年总是挂着一张疲惫不堪又鲜有笑容的脸。
我在生活相对殷实的外婆家度过了人生最开始的七年,学龄时才回到父母身边。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正是爷爷刚去世、他又刚失掉教师的工作、人生最为迷茫的日子。我至今都难以想象,一个不惑之年再无满腔斗志的男人被岁月猛然推入到万丈深渊会是种什么感觉。我唯一能记得的,就是父亲那张终日阴沉着的脸和他无数次毫无缘由就勃然大怒的样子。
国家开始大规模推广“加碘盐”的时候,我读小学一年级。学校给每位同学发了一袋碘盐带回家,直到今天我都能清晰地记得老师的原话:“明天记得带两块三毛钱回来,这盐不是白送的。”我捧着一大包碘盐背着夕阳走在回家的路上,浅夏黄昏的日光把我的影子拉得笔直细长,孤孤单单。
我一直没问过别的同学回家都是怎么跟家长要那两块三毛钱的,总之在我开口的一瞬间,父亲忽然一把掳起我抱在怀里的碘盐,猛地扔了出去——那包还带有我体温的碘盐,“嗖”的一声就从我耳边划了过去,带起的凉风微微扇动了我散落在耳后的头发。
“以后不准要,明天把盐带回去!”父亲重重地说的这一句话,像硾子一样砸得我的心砰砰直响。
我呆愣在原地,七长八短的呼吸从胸腔里直直地往外冲撞,喉咙收得紧紧的一声也发不出,全身的每个毛孔几乎都惊恐地站立起来。等到我木然地回过身想找回那包盐 时,发现它孤单地躺在十几米外的狗窝旁边。透过被大黄狗舔了不知道多少遍的透明的包装袋,我看到那包细白如雪的碘盐安静地反射着夕阳的余晖,变得分外刺眼。
最终,我也没要到那两块三毛钱;最终,我惴惴不安地把盐退回给了老师;最终,我被罚在教室外面的太阳地里站了一上午。
那些稚嫩又小心翼翼的岁月里,我曾一度这样描述过跟在父母身边的日子——感觉自己从没做过孩子。不单单是来自“同龄的孩子在田野放风筝,我只能在田里锄草” 的心理不平衡感,而是,在原本应该可以任性的年纪里,我从来没有“任性”过。我见过哥哥小时候要不到钱就会大哭大叫,耍赖撒泼,使尽浑身解数,我从来都不会,或者说,是不敢。我总是倚着门框,漠然地看着哥哥不管不顾地扯着父亲的裤兜,父亲甩开他,他马上又黏上去,再甩开,再黏上去……而我,连抬头看父亲一 眼都不愿意,更别提敢去扯他的裤兜要钱了。
那时候我从没想过,不敢开口要钱的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得再也不忍开口。
站在今天,再次转身回望我的高考,一片兵荒马乱——父亲在船上出海,哥哥在青岛市市北区住院,我回户籍所在地城阳区考试,姐姐回老家帮着母亲收麦子。我5月31号从就读学校来到青岛,当所有同学都在做“最后一搏”的时候,我在医院陪床,四处弥漫的药水味掩盖住了任何纸质的书香。
姐姐的宿舍距医院大约一小时的车程,我每晚要回那里去睡觉。我的考场距医院有两小时车程,公交要倒两次车。高考前一周,我迅速从“一个连转向灯都不会看的农村学生”成长到“一个能在陌生偌大的青岛市来去自如的姑娘”。没有专车接送的待遇,没有精心准备的营养早餐,我一个人,在车水马龙的奔波中仓促地结束了我的高考—— 一场在老师口中“能改变命运”的高考。
如果说,我在走出考场后看到无数家长殷切盼望的眼神时,感觉到的是孤独,那么,当我在医院看见风尘仆仆匆忙赶来的父亲时,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艰难”。
父亲用力推开病房门的那一瞬间,永久性地定格在我脑海里——土黄色的上衣袖子胡乱地卷在胳膊肘上,肩上挂一个瘪瘪的编织袋,满眼的疲惫藏不住心底的焦虑,快速扫视了病房一眼之后,才稍显费力地挤进房门大步向我们跨过来。我好像从没这样近距离好好看过父亲,他掀开帽檐抹了一把额头然后就随意顺手把帽檐一扣,任由它歪在了额头上。父亲的脸黝黑黝黑的,厚厚的眼袋耷拉下来,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长长一截,微微泛白的胡渣占领了他的整个下巴——父亲的胡子都白了,趁着我不愿抬头细细看父亲的日子,它们居然,就那样悄悄地白了。
不知道日子过成什么样子,才能算得上是众人口中的“苦”,像父亲一样年过半百了,还疲于奔命在海上漂,这能不能算得上“苦”。
“我来给你送点钱。”父亲伸过他那指纹里满是污垢的大手,递给我一个方方正正的用旧报纸包裹的小包。这么多年,我终是习惯了在父亲面前沉默又温顺,攥着钱,什么也没说出口。父亲始终没问我一句关于“高考”的事,我考得好不好,感觉有没有把握,来回坐车奔波累不累,中午去哪休息的……我甚至都提前想好了得体的答语,但是,真的一句也没有。
“我先回家看看你妈,住两天就来换你。”父亲说完就背上编织袋走出了病房,我呆滞地攥着那沓钱站在病房门口,看着父亲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向走廊的尽头,拐弯,下了楼梯,没有回头。
眼泪忽然就翻涌上来,我想告诉父亲出门左转有站牌,我想告诉父亲医院门口对面的街上有卖饭卖水的,我想告诉父亲,以后别再出海了。那年,我18岁;那年,我第一次摸到了5000块钱的厚度;那年,是哥哥生病的第四年;那年,我把涂完的志愿卡扔在了城阳一中校门口的垃圾桶里。
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的压力大于同龄人,我干着同龄人都没干过的农活,花着比同学少很多的生活费,能不交的钱就不交,比如多年前的那包碘盐,比如再后来的很多件 “名义上能自愿选择实际上是强制购买的东西”。可是当我在接过父亲靠“出海”挣回的钱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真正抗压力的一直是父母,自己从未真正担过什么。
大学生活太美,美到父亲愿意在海上漂着挣钱供我去读。可是,我不愿意。
父亲送我离家打工的时候,轻描淡写的一句“我知道,你愿意上大学”就让我哭得难以自已——我从没开过口的事,也骗不过父亲。只是父亲却总能骗过我,从“碘盐”到“大学”,我用了很多年才真正明白“父亲愿意为我花钱”这件小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