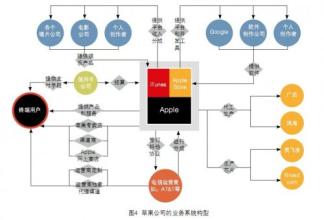叶向真,笔名凌子,是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导演。(资料图)
“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当我们第二次走近诗句中的这座小楼,叶向真已经站在夕阳下等候。73岁的她穿着衣领带花的牛仔衬衫、牛仔裤,外加一件深红色的冲锋衣,显得非常清爽、帅气,有文艺导演的范儿。听闻我们的评价,她迅速做了个抬手动作:“一次拍纪录片,我就是扛着大家伙直接上。”
叶向真还有另一个名字——凌孜。1981年,凌孜就玩电影玩出了名堂。她拍了一部《原野》,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又拍了另一部《风吹唢呐声》,被黄永玉评价为“真正沈从文的风格”的影片。荒诞的是,前一部电影“只准外销”,后一部电影“只准内放”。她玩不下去了,1987年去香港从商。
现在,让拍电影她也不想玩了。2009年,叶向真和先生从香港回到内地,和母亲守着父亲叶剑英住了30余年的老宅,全心致力于推广儒家传统文化。时代更迭,父辈意志带来的沉重使命愈加清晰而紧迫——“你要想不亡国,就得推崇传统文化。”

这位在“红二代”中极具号召力的“向真大姐”跟许多红二代不一样,她发声的支点并无明显的革命传统与红色印记,而是记忆里父亲满屋子古书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
叶帅希望向真学园艺,能对国家有“直接贡献”
这些天,叶帅故居门口几株白玉兰长满白色的小花苞骨,人人都觉得美,叶向真却可惜,“枝杈没剪好,长的花骨都太小”。叶向真对植物的栽培兴趣很大程度上源自父亲。父女俩人曾在这座小楼的院子里,种过各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有一回,向真在院子拾了片枫叶给父亲,父亲隔天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句。父亲希望女儿能学园艺,做对国家“有直接贡献”的人。当时得知向真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父亲一个星期没跟她说一句话。
叶帅故居进门处,是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会议厅。在单调的70年代,跟二女儿向真一起在这个厅里看电影是叶剑英的重要娱乐活动。“那时没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向真回忆,除了看国内一些意识形态正确的影片,他们也看宣传部门从海关中途拦截的“过路片”,“什么题材都有”。
青少年时期的向真性格活泼,文体活动无一不爱。“非常活跃”——她对父亲也有同样的形容。一生戎马的叶帅,精通琴棋书画,不光喜欢跳舞、钓鱼、游泳,有雅兴时也会写写诗。兴趣广泛的他有点担心与自己很像的女儿向真——“蹦蹦跳跳,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不能投入地做一件事情”。在向真首任丈夫、著名音乐家刘诗昆的回忆里,向真拉着父亲到音乐学院的礼堂听他演奏《梁祝》,就此一对年轻男女因为“喜爱文艺”而相识相爱。在这位前女婿眼里,叶帅是个少见的有“人情味、家庭味”的高级领导人。
向真的秘书周小姐告诉记者:“叶老师从不发脾气,性格温和。”这种性格特质,其实也源自父亲。向真记忆中,在饭桌上常开玩笑的父亲,对子女从未有过真正的打骂。在叶帅生前的卧室里,正对床的墙上挂着叶帅母亲的照片。周秘书说:“叶帅希望随时都能‘看见’母亲,他很讲究孝道。叶老师也是,她对她母亲很孝顺。”从2009年起,向真为照顾母亲,内地、香港来回两头跑。这些年来,兄弟姐妹中唯有她守着宅子。“没有家哪有国。家是一个民族的细胞。”向真说。
故居办公厅里有一张旧败的灰黄色斜躺椅,边上一张小桌,摆着两部电话。我们建议向真坐在椅子上拍张照,她摇摇头:“那是老人家生前坐的,我们从来不坐。”她记忆中的画面,就是父亲经常坐在这里读书,读古书。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在牢房里养过蚂蚁
在红色家庭长大,向真跟其他高干子弟一样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向真担任了中戏的学生会主席,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反对老红卫兵搞“血统论”的向真成立“信仰论”的少数派组织,轰轰烈烈地“绑架”彭真,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
如今的向真坦然承认当时的思想有点激进,她认为这更多是时代大背景造就的激进,“所有的大学生都满腔热血,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谁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渐渐地,她发现事情闹得开始不像话了:“很多人没有理智,拿开水浇人家头。思想上的争论可以有,刑罚和体罚再怎么都不应该有,那是流氓行为。”“我们应该承认,‘文革’是错的。”谈起陈毅之子陈小鲁公开为“文革”道歉的事,向真的回应是:“小鲁这样做是对的。当时他们很多中学生失去理性,做出了伤害人的举动。”
涉及自己的反思,她迟疑了会儿,表示:“我们当时还是比较理智的,只写大字报展开思想上的讨论,没有伤害人的举动。当时很多自杀的人,医院不抢救,认为他们是反人民的‘敌人’,我们见到了就赶紧把人送去医院,并以红卫兵的身份去说服医院必须抢救。”
1967年2月,叶帅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发火猛击桌子。之后,因“二月逆流”问题,他不再担任军队重要工作。向真清楚父亲当时的想法:“军队不能动,军队如果垮了就等着别人宰割,再闹就亡国了。”很快,视叶帅为眼中钉的江青将叶家6个子女都关进监狱。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想法子找些新鲜玩意解闷。比如培植扫帚上的苗,把头发扯下来绑在牙刷上当毛笔练字;她还养过蚂蚁,让它们搬东西。在监禁的日子里,她最反感的是一举一动时时被门上的洞眼监看着,睡觉不能关灯,脸要朝外……“这段经历实在太不好玩了。”
1976年10月6日,仍然控制军队大权叶剑英79岁,按照他的部署,“四人帮”一举被摧毁。“父亲非常有谋略。”向真认为,这个时刻,历史选择了父亲。
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她一生的信仰
1970年出狱后,考虑到在管文化的江青手下做事“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向真没去拍电影,进入北京医学院学医。但她还是放不下电影。1978年,她取了“凌孜”的笔名,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当时大多电影很政治、很说教,向真想拍一部“展现被压迫的人会抗争、有爆发力”的作品,于是她和后来的丈夫、摄影师罗丹拍了一部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的《原野》。曹禺看电影后夸奖:“更凝练了,比原作好。”叶帅看完后理解了女儿:“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1981年,《原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40岁的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入选。她记得在威尼斯一进餐厅,餐厅的演奏人员立刻演奏起日本歌曲,都以为她是日本人。但当时在国内,大家为饰演女主角金子的刘晓庆应该解开一个扣子还是两个争论不休,电影被扣上“乱搞男女关系”等罪名而禁演。“只能外销,禁止内销。”1988年,电影《原野》解禁,万人空巷,人们试图看到传说中的裸体镜头。后来,向真的第二部电影《风吹唢呐声》又入选夏威夷电影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片子又被规定:“不能外销,只准内放。”
“这些领导完全不站在民族的立场考虑问题,这就不好玩了嘛。”向真把“不好玩”三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她最终“逆转”风格,拍了一场“闹得稀里哗啦”的喜剧《三宝闹深圳》,就跟电影说“拜拜”了。多年后,当时尚在世的导演谢晋打电话劝她:“凌孜,你应该拍电影。”她说她不玩了,老了,她要做“该做的事情”。
聊了两个小时,往事一幕幕掀起,在某个瞬间,向真的语调不复平缓,取而代之的是激昂愤怒。“我问你们,你们听国歌什么感觉?听到国歌,我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她眼睛直直地看着记者,一字一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现在许多人觉得:做美国人比做中国人还好。你们怎么想?清朝时那么多留学生都回来报效祖国,现在呢?很多人都有一种奴化的思想,一种卑琐的心态。”继承父辈的理想,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一生的信仰。而传统文化的丧失,在她看来,意味着有亡国的危险。说起因贪污、受贿而被治罪的“红二代”薄熙来,她只有简单一句评价:“家教不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大道理,更多是传统礼节的言传身教。每次家里来人,叶帅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柺棍送客。这次,向真大姐也做了同样的事,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2.叶剑英女婿刘诗昆回忆非常岁月非常事
20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蜚声世界乐坛,成为叶剑英的乘龙快婿;正当他风华正茂、光芒四射之际,却因政治纷争在文革中身陷囹圄,6年后才获得自由。1990年,在国内备受争议的刘诗昆离开大陆,定居香港,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2007年3月14日,“两会”召开之际,作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诗昆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回忆非常岁月非常事非常人,为我们披露当年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与内幕。
非常岁月的“两会”
我有幸作为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亲眼目睹了中国43年来的民主进程。
1964年,我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已经有了“文革”的前兆。与会代表们在大会上的发言都谨小慎微,生怕因为讲错一句话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远远没有今天这样畅所欲言。
那时候,大会上实行举手表决,“赞成的请举手”,工作人员清点举手人数,然后宣布“手放下”,其中间隔只有几秒钟时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走形式。说起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走神,没及时举手,结果大会却宣布全体通过。
过去的大会一般都不公布具体票数,只是宣布通过法定人数与程序。而现在的“两会”确实是越来越透明了。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时,我担任计票员,在大会计票室里,我亲自感受了计票工作的真实可信。
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第三届全国人大只举行了那一次会议。10年之后的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召开,那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回想起来,那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都显得颇为神秘。
当时,与会代表多达2885位。我与部分代表被安排住在月坛附近的北京市委招待所。开会的那十多天时间里,我们住的地方被采取严格隔离措施,封门、切断电话线、里外不允许通信,与会代表就跟“地老鼠”一样被与世隔绝了——
每天早上,一辆辆车窗被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的大客车把我们拉到当时中央军委管辖的北京京西宾馆院内,我们从楼内的地下通道步行走到军博地铁站,乘坐地铁在前门地铁站下车,然后穿过地下通道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
那次人大会议,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佳,那是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发言时间并不长。
直至大会闭幕以后,才将有关消息公之于世。
那时候,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召开时间都是不固定的,随行性较强,不像现在这样相对固定在每年的3月份。也没有规范的提案。
比渣滓洞还残酷的监狱
“文革”开始不久,1967年4月2日,江青指派她的亲信到中央音乐学院召开批斗大会,当场宣布:“刘诗昆是反党、反革命分子,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1967年4月5日晚上11时45分左右,我被限令离开北长街叶帅的家,到中央音乐学院接受劳动改造。
1967年9月3日下午,正当我背着箩筐打扫学校厕所的时候,来了几个警察,不由分说地将我推进吉普车,拉到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零9个月的监狱生活。
在监狱里,我受尽了折磨,几乎病得死去。对比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监狱,还不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残酷的监狱,还有更残酷的,那就是纳粹德国的集中营。
入狱后,我们被囚禁在一个个小单间里,与世隔绝,饱受精神摧残,每天与外界的惟一沟通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和收听监狱广播。
记得在半步桥自新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时,曾连续5个月不给放风。而人的精神活动是多面的,如果思维只是单一地针对自我,就很容易思维疲劳。所以很多在监狱里呆过的人,出来以后变得痴呆、傻愣,甚至神经功能紊乱,患抑郁症。
从1967年9月3日被关进监狱,到1973年5月3日被放出监狱,我的人生从28岁走到了34岁,这是一段令我一生难忘的岁月。因为营养不良,再加上精神抑郁,出狱的时候,我的头发都白了。
往事不堪回首。在监狱里,每顿都吃不饱。一天两顿饭,每顿两个小窝头加一碗菜汤。窝头是馊面做的,烂菜叶子或烂萝卜头做的菜汤。到了夏天,菜汤表面上经常漂着一层虫。就是这样,我们还是每天都吃了上顿盼下顿,一顿盼一顿。如果三天不吃饭,人还可以忍受;可是如果让你三年都吃不饱饭,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与饥饿相伴的是口渴。因为盐放得多,菜汤表面总漂着一层白霜。饭后,口渴难耐,但是每天只发两碗水,根本就不够喝。更不用说洗澡了,一年也洗不上三四次澡。有一次,好不容易有洗澡的机会了,结果水烫得根本就没法洗。
然后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持续地受冻。功德林监狱是清朝修建的监狱,囚室里只有一块睡觉的木板和一床被子,没有褥子。冬天没有暖气,木头窗户呼呼地漏风。我是9月份就关进监狱的,没带棉服,监狱里不给发棉衣,持续3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只有单衣、夹衣穿,冷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披着被子度日。
睡觉也变成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晚上睡觉时,100瓦的大灯泡却不准关。为了方便狱警夜查,还规定犯人睡觉时脸要朝外,不许翻身。
在监狱里,我没有坐“老虎凳”,但却被施以变相刑罚。记得在自新路看守所时,我曾经连续53天“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早上,从囚室被带到审讯室,面朝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低头90度,腿不许打弯,一打弯就被狱警脚踹。每天持续10小时左右,只是在中午才被放回去吃一顿饭。到了晚上,腿肿得动都动不了。
类似种种磨难,有的人受不了,自杀了。但我不愿就这样死。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熬到活着出狱的那一天。
出狱以后,我在《红岩》中看到被称为“活棺材”的重庆渣滓洞,相比起来,那里的犯人待遇算是太好了,犯人不都是住单间,可以串联、递纸条,甚至还可以带着脚链跳秧歌,只有在犯人闹事了以后才不给水喝,而我们却是天天口渴,相比起艺术夸张的电影,我在“文革”中的囹圄生活更为夸张。
1972年12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其在狱中受到的种种迫害。12月18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些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须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当时,我在狱中也知道了这一消息。后来我们的待遇也得到了些许好转。
一天,我在墙角处发现一张信纸那么大的破报纸,马上收起放入怀中。打了一夜的腹稿,然后从每天送来的报纸上用牙签一样大的扫帚条挖出六七个需要的字,吃饭的时候用口水和窝头当浆糊,贴在那张破报纸上,几个月后终于贴出了一封长达千字的“信”,藏在衣服的棉花里,只等伺机送出。
1973年3月的一天,狱警通知我说有人探监,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一看是我的前妻叶向真。(1967年4月,我被定为反党反革命分子后,为不牵连家人,我与叶向真办理了离婚手续。)乘狱警不留神之际,将那封信交给了叶向真。
信很快经由叶帅交给汪东兴,转交了周总理。周总理又把信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下令:“立即释放。”这样,我突然间就被放出来了。
作为目击证人为于桑洗脱“李震案”罪名
我的案子归口中央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中央专案二办”,都是军口的案子),与彭德怀、罗瑞卿、贺龙等人的案子列为一组,专案组的人企图逼我以叶剑英亲属的身份揭发叶剑英。
我获释后,公安部成立了一个复查小组作了一个平反结论,给我和叶向真平反。1973年10月,复查报告出来了。我和叶向真的案子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其目的是妄图打倒叶剑英同志。”上面有周恩来“拟同意”的亲笔批示,并有叶剑英等10位国家领导人的亲笔圈阅。
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找我和叶向真在北海旁边的三座门(注:当时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谈话,询问我们有无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签字表示同意。巧合的是,就在我们细阅案子纪录准备签字时,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红电话机突然响了。
当时,中央的红电话机是保密机,这种电话是加密的,不能拨号,只能接听。红电话机那边称:“公安部部长李震已经失踪24小时了。”于桑接了电话之后,立即就给平时与李震来往密切的陶鲁笳等三人打电话。然后,就匆忙乘坐一辆灰色苏联产汽车走了。
后来我听说1973年10月21日中午,在地下热力管道的地道里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李震死后,江青一伙咬定李震死于谋杀,想除掉于桑、刘复之。10月23日至25日,政治局几次分析李震死因,多数人认为李震是他杀。但是,为了有利于案件侦破工作的开展,对认为李震是“自杀”的于桑、刘复之两位副部长采取保护性隔离审查措施。
当时主管中央政法委工作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叶剑英将我和叶向真当天在三座门所目击的情况告诉了华。华后来找人在三座门召集我和叶向真谈了两个小时,反复追问我们于桑在接听红电话前后的反应以及当时的细节。
结果,于桑先获释。刘复之后来才获解脱。
与江青之间的“交恶”
当时,对我的事情,毛主席发了三句话: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注:这是原话,东西指的是钢琴音乐作品。)要让他继续演出。
那时候,主席一句话就敲锣打鼓,连夜游行,连发三句指示可见规格之高了。作为主管文艺口工作的江青没有一点表示怎么说得过去?
1973年10月的一天下午,江青让吴德(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打电话给叶帅的秘书,说当天晚上在钓鱼台接见我。在一旁的叶帅笑了笑,说:“看来这回是好意了”。
我被告知在三座门等候。吴德的司机开车拉我去钓鱼台。实际上,在此之前,我是见过江青的。1964年,我在毛泽东驻地为他弹琴时,江青曾请我跳过舞。
当晚,专业演员出身的江青,在我面前上演了一出政治戏。我刚到大会议厅,江青就很热情地迎了上来,说:“刘诗昆,我们都等着你。主席对你很关心。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要让他继续演出。你的案子都是整叶帅的,是林彪和四条汉子(注: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搞的。他们不仅搞叶帅,还搞我呢,中央二办很坏,他们不但给叶帅立专案,还给我立了两个专案,我不怕。去年,我去看叶帅,见到牛妞(注: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小名),都怪我不好,当时忘了问起你。”
说话间,她拿了一些白兰花(注:花很小、很香的那种),交给一个穿军衣的护士,让她先放在冰箱里,让我走的时候带给牛妞。
当天在座的有姚文元、王洪文、吴德、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李德伦、殷承宗,加上我和江青,共10个人。江青坐中间,我坐她右边,姚文元坐她左边。那天晚上,江青为我安排放映了一部电影《红袖倾城》。(注:那时候不许看外国片,内部看电影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
那是一部美国电影,讲的是一个西班牙斗牛士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弹钢琴的镜头。江青很舒服地躺在椅子上,为表示亲近,她让我帮她拿着她的玻璃缀面的大皮包。“文革”时期规定不许用皮包,一律都用军挎包。
看完电影后,江青问我:“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志婉的人?”
我说:“认得,她是我父亲的同学。小时候,我还叫她徐姑姑。”徐志婉是我父亲当年在山东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江青当时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当馆员,与黄敬同居。徐、江二人一直有来往。
“那你父亲现在哪里?”江青问。
我说:“我父亲现在还被关在上海的监狱里。”在我被抓进监狱后不久,我的父亲刘啸东也在上海被抓,1973年还被关在监狱里。
江青拖着腔调说:“真奇怪!”然后,她扯着嗓门喊“洪文!”王洪文立马来到江青面前。
江青用手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说,“你们上海怎么搞的?刘诗昆的父亲现在还关在你们上海?告诉春桥,就说我说的,立刻释放!”
王洪文说:“是是是,我立刻传达!”
几天之后,我的父亲就被释放了。
文革后期,我曾整过三份揭发“四人帮”的材料。其中一份是揭发江青在大寨时期的讲话的。那时候,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
江青曾窜到大寨发表讲话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中央有人架空主席,你们知道这个宋江是谁吗?”到处散布类似这样的风声,来攻击叶剑英、邓小平、周恩来。新华社摄影部杜修贤因为工作关系,亲耳听到很多江青个人召开会议的讲话,他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我。
另一份是吴祖强(注: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中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告诉我的。当时。有一部美国电影《鸽子号》,讲述一位美国青年独自驾驶鸽子号环游世界的故事。全片以孤舟航海为经,爱情波折为纬,突出勇气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主题精神。其中有女主角不顾一切跳入海中,男女主角在水中拥抱的场面。据说江青在看了《鸽子号》后说,如果是她,她也会跳进水里扑向自己的爱人。
另外,还有王心刚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我也把它整理成了一份材料。
我将这三份材料交给了叶帅,叶帅把它装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专用的牛皮纸信封里,起笔写上“专人专送邓副总理”,警卫参谋马西金立刻坐着汽车送去了。
一个星期后,邓小平告诉叶剑英事情的结果是,张玉凤告诉邓小平说,“材料主席已经看了,主席很生气。”我后来得知,当时邓只送了江青在大寨讲话的材料。
结果后来邓小平又挨批了。叶剑英被逼请假。中国的政治真是风云莫测。当时我也很紧张,如果材料落到江青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巧的是,当时新华社的朱穆之也写过一篇江青在大寨讲话的材料,结果,当时就被打成反革命,而我则逃过了这一劫难,幸免二次入狱,恐怕直到江青集团覆灭也不知道当年毛主席看到的那份揭发江青的材料是我写的。
人物资料:
刘诗昆,中国著名钢琴家。1939年3月出生。3岁学钢琴,17岁荣获“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19岁在世界上最顶尖的国际音乐大赛──“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上荣获亚军。1990年定居香港。除继续从事钢琴演奏外,还在香港和内地多个城市开办刘诗昆钢琴艺术中心、音乐艺术幼儿园,至今已近80个。与此同时,创办乐器公司生产钢琴,集钢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企业家于一身。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