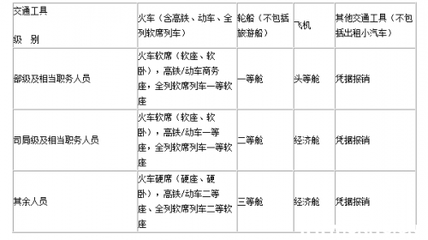原载《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作者系前《中央日报》记者

要说明国共和谈破裂原委,不能不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说起。犹忆,天皇刚要日军放下武器,在当日察、绥地区,国、共两军便同时发兵,竞相接管日军驻地。一方面,国府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所部,自绥西向东出发,八月十五日接收包头,十八日进入归绥(今称呼和浩特)。另一方面,延安也下令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与贺龙的晋绥军区占据平绥线上的张家口、宣化一带城镇,从此之后,双方即在此一地区对峙。制宪前国共彻底分裂翻过次年(一九四六年)春天,傅自重庆领回大量美式装备后,即与陈诚密计进攻共区,傅当时为迷惑共方,一面派其亲信周北峰潜赴共区谋和,一面积极备战。九月初,傅军即与自北平出发的第十一战区李文兵团,分头沿平绥路东西并进,企图打通该线,并解大同之围。在此役中,由西而东的傅部进展得比较顺利,除在攻击集宁时打了一次硬仗之外,很快地支解大同之围,继在十月十一日打下了塞上重镇张家口。此役使傅氏继战前百灵庙抗敌之役及战时克复五原之捷后,再度取得又一次喧腾全国的大胜。但傅作义的大胜,却促成了国共和谈希望之完全破灭。先是,当国军开始在平绥线上采取行动之初,早已避居上海的共方代表周恩来即向马歇尔特使提出备忘录,指出:“如政府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之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已公然宣告(和谈)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对此,国府翌日的反应是,把颁布国大召集令的日期,自十月三日延至十二日。再隔一天,国府请求各方提出即将改组的国府委员名单,仅青年党提出,共方拒绝,民主同盟则存观望。同时,周恩来代表在沪宣示,在炮火声中,中共将不参加国大,并谓如无美援,中国内战便不致扩大。此后的发展是双方各走极端,两边在战场上各不相让,在政治上对立加深。终于在国府正式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也终止谈判飞返延安之后,双方便完全诉诸战争。再翻过一九四七年一月,美国召回了调停使者马歇尔,闹了两年的和谈也就由此终止。遭逢制宪国大盛会于是,举世的目光再度转向南京,而制宪国大的大戏遂由此登场。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国大召开之前,国大秘书处一面聘请央报的采访主任担任大会新闻组副组长,一面通知我们派四位记者参加采访。当时我们压根儿不曾想到,政府聘任记者兼司发布是否会影响到新闻报导的独立性和新闻自由的大原则。事实上,大家一致关心的是:召开国大制宪是千载一时的大场面,哪四位同仁会幸运地被选中进入会堂,具名撰稿亮相?终于名单公布,可一头一尾却都爆出冷门。事先,大家一致认定要闻记者祝修麐和首席军事记者朱恒龄两兄必因资深入选,可是就不曾料及时任社长室秘书的吴俊才兄在临时“下放”之余竟名列班首,更没有想到入社不足半年、试用刚才期满的在下也忝附骥尾。
人选决定后,主任召集我们四员“大将”,开了一次分配工作的小组会,会中原决定在全体大会召集期间,我们四人逐日轮流主跑,并具名撰写当天综合新闻。第一天,轮到俊才兄,他当仁不让写了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一连五天下来,他依然一路挺笔,就是写个不停,尽管修麐、恒龄两兄不断抗议,亦无效果。此后,他们两位也相继来了个萧规曹随,一上来便不肯放手,轮到我上场已经是十二月五日,议程上赫印明的是“分组讨论”开始。三位大哥一个个好心语我:“老弟,今天要看你独力表演啦!”那天进得会堂,一见集会牌上所列十五个小组议题、场所,便头昏眼花、莫知所措。所幸自己曾是个法科学生,还能在诸多议程上分得出一个轻重。当天稍一考虑,便选择了几个重要审查会场,抓住了几个主要议题,当晚再参照大会发布稿件,写了几条综合性新闻缴卷。可是这是正规新闻,不能算是特写,龚选舞这三个字当然便挤不上报啦。这样一连几天,炮制如仪,除了主任称赞我理路颇为清晰,综合工夫还算不错之外,报端扬名之事,便只有让三位老兄专利于前了。不过有失亦有所得,还不等到大会闭幕,傅作义将军那边来电邀请京沪记者组团往访张垣,大约是主任为了要给我点补偿吧,竟破格让我出次大差。此是后话,暂且不表。土豪劣绅因反共而死末了,我还得费点笔墨,附带记下当日在国大会场的一次巧遇。记得早年我念中学之际,在四川崇庆故乡,曾与县城里的首席土豪施德全紧邻而居。有天,我们兄弟在自家院子里玩球,不提防失脚竟将皮球踢过了垣墙。后来球是讨回来了,但是我这名肇祸者却被那位担任团防局长的施先生好好地教训一顿。想不到多年后,我在采访国大新闻时,竟在一处审查会上碰到了代表青年党出席的施先生。记得当时他一见到我,便有点结结巴巴地问:“你、你就是隔壁龚家那个淘气的孩子,怎么你也赶来开会?”我连忙告诉他:“我不是代表,而是到场采访的《中央日报》记者。”“记者、《中央日报》,巧得很,施伯伯今天代表青年党在一项重要问题上发言,你可要好好替我记下来登上报去。”当天,我耐心等着,轮到他照着一张稿子发言时,觉得他说得颇有道理,因此在审查会照他所代表的青年党意见通过之后,也据实酌为报导。这本是我分内该做的事,可他在次日再度相遇时,却一个劲儿地向我致谢,还说我小时好动而具冲劲,长大了果然能在“中央”做事。敢情,他还记得几年前我踢球过界的糗事。不过,他也许没有搞清楚,我只在《中央日报》做个小记者,可不是在“中央”做什么样的大事。事后我得到家信,说是这位施先生回家之后,还一个劲在县城里为我吹嘘,说是一个人“从小看大”,我这人自小调皮而具活力,长大了果然能在京城报馆做事,随便摇摇笔杆便能让他的名字登上大报云云。我得信后,不敢在报社提起,生怕报社负责人怀疑我写消息兼做人情,其实我写那段新闻,仅因他是代表青年党提出修正法条建议,而审查会也顺利加以接受,如斯而已。这位施先生,也说得上是大时代里一个小小的悲剧人物。他出身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毕业后先在家里闲居,继在刘湘部下担任采买处长,赚了些钱,便回老家做起绅乡。青年党这时在四川极为活跃,到处吸收党员,施在地方既饶有家财、复颇具势力,乃为该党吸收,先后出任县清共委员兼捕缉科长,进而升充名列士绅之首的团防局长兼征收主任,在县内擅设关卡,滥收商税路捐。记得我们两家比邻而居之际,便常见他穿着中山装、大摇大摆、神气活现纵横市上,背后总是跟着两三个腰悬盒子炮(指手枪)的保镖,路人为策安全,无不退避三舍。
及政府决定召开制宪国大,邀请中央及各路民主党派补提国大代表,这位在地方上有财有势的施先生在报效、争取之余,更被青年党遴选为新科国代,穿着一身宽宽大大英国毛料裁制的西装晋京参与庙堂议事盛会。那天,居然还拿着党部交给他的发言要点,当场战战兢兢照念如仪。他本来是个彻头彻尾土里土气的土豪劣绅,自从捐班弄了个制宪国代,再打从京城里镀银(非金,因仍未远渡重洋取经也)归来,据说完全变了一个人,往日的长袍马褂早已封存箱底不说,即使是当团防局长时穿着的中山装也被弃置一旁,成天招摇过市之际,穿上的全是上海师傅裁制的时兴合身西装。不过穿着西装并不表示他变得更为“文明”,在县里,他越发地恣意横行,枪杀政敌固然无人敢置一词,县中招生让他女婿落榜,也居然强迫校长举行复试,破格录取。大约是在县境里做土皇帝,自我膨胀得弄昏了脑袋,以为自己掌握一群持枪执械的民团,便足以宰割一方。一九四八年共军入川,他未能权衡轻重,竟与我县另一世袭豪绅黄鳌(润泉)、黄润琴兄弟共组反共救国军,负隅顽抗。可是连胡宗南的五十万大军都不中用,他们那批乌合之众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结果兵败逃亡之后,终于两年后在外地被捕,再押回老家与黄家兄弟一同在公审之后当场枪决。从小在家之时,便耳闻目击黄、施两家在乡横行霸道、违法不义的种种情节,由于他们一直与官府勾结,而且更不时出入官场,因此全县百万乡民只有忍气吞声,任其宰割。前面提到施某曾捐班出任国代,但势力更大的黄家老四黄鳌在川军干了一阵旅长、路司令后,竟也获得国民党提名,在成都选区,当选行宪后首届立法委员,事实上一般老百姓并不曾亲自投票给他,而他所得选票只不过是在县府大堂上一箱又一箱地趸计出来罢了。另外,我的一位赵姓姨妈早年嫁给后川县的一位索姓土司,后因夫死子幼,而国府复规划为川中少数民族的藏族保留一个立委名额,结果我们这位汉族姨妈,也就当选为代表藏族的立法委员。可是由于她与前述黄鳌同染阿芙蓉癖,赴京上任既然不便,两人只好待在家里享福啦!我没看过别的地区的国代、立委选举,但就我所知,我们家乡的民意代表便是这样选出来的。我常想,国府当日为了还政于民、实施民主,原是天经地义之事,可是实际付诸施行之际,在外面却出了这许许多多的毛病,特别是在我们家乡,选出来的竟是施、黄一类的角色。无怪有人说过,国府不实施民主诚然遭人诟病,但实施这个样子的民主,到头来却加速远离民意,造成分裂,终致提早离开大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忆昔国共战争末期,正途出身军官们领导下的正规军队,在共军势如破竹的追击扫荡下,不是弃甲曳兵、成千上万地望风而降,便是乘坐杭船,近走台湾,远遁海外。一个个逃之夭夭,像施、黄之辈留了下来,敢以少数乌合之众而与气势方盛的共军顽抗者,殊不多见,如果当日国军官兵也能如此,国府纵不能起死回生,在大陆多拖一些时日,恐怕也有其可能。这样看,执着的土豪劣绅在这一点上,也不见得比不过统军大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