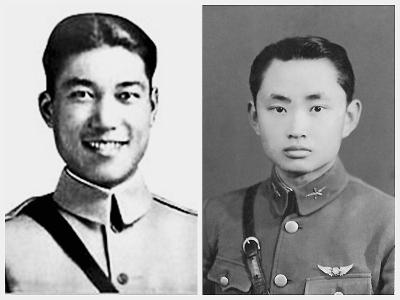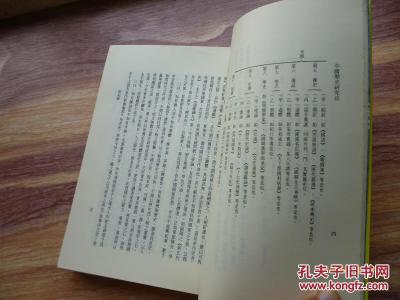《小说月报》

《我对于梁任公先生逝世的一点感想》,左舜生撰,载《长风》 1929年4月3日第4期。
康孙严王(康有为、孙中山、严复、王国维)各努力于政治与学术的一方面,所以他们只能各表现中国近代三十年来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而不能代表全体;梁任公则始终对于政治与学术是双管齐下的,且于政治则主唱君主立宪而并不反对共和,能助袁世凯统一中国而决不能容许袁世凯做皇帝;于学术则除对于史学始终维持他较浓厚的兴趣外,乃驰驾于各方面而茫无际涯,并且毫不愿以老辈自居,常常是和许多青年一伙儿竞走。所以他对政治主张的彻底似乎不及康孙,对于学术某方面的精湛似乎远不及严王,但整个儿代表这个时代的,却除梁任公外更找不出第二个!梁任公算是在这个中国政治与学术的过渡时代充分的尽了他的天职的一个人。
《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缪凤林撰,载《学衡》1929年第67期。
然以当时民智之闭塞,士风之委靡,号称智识阶级者,下焉者日治帖括,上焉者鹜于训诂词章。而梁氏日以维新、变法、新民、少年、自强、救国之说大声疾呼。复以其间灌输世界智识、阐发先哲绪论。凡所著述,大抵气盛而文富,意诚而词达,加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故一文之出,全国争诵,老师宿儒犹深翘仰。清末士气之奋发,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传实与有大力焉。虽其主张开明专制,拥护清帝。言立宪而不言民主,言政治革命而不言种族革命。与国民党为政敌,其言论之攻击国民党者无所不用其极。然时务、清议、新民诸报之出世。皆在《苏报》、《民报》之先。梁氏固不愧为新思想之陈涉,即后此民族民权之说风靡全国。亦以梁氏温和之理论与夫暴露满廷之失败及维新之绝望,为间接之助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