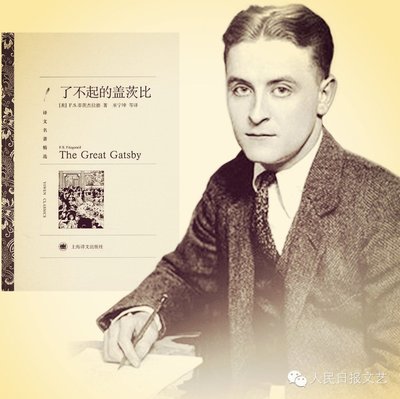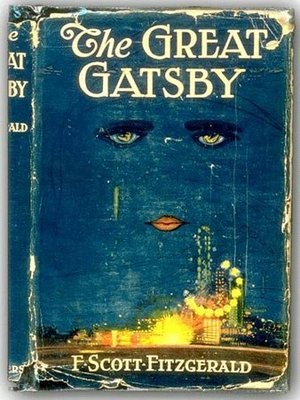有一天,听一位朋友提到自己的父亲,说他收藏了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国产蒸汽机火车头,还特地在郊区租了一块地,请了一位当地的农民看着。她的父亲一辈子因兴趣而活,做一件事之前先问自己,这件事是不是“有趣”。如果够“有趣”,即使明知麻烦,明知不赚钱也会去做,因为乐趣是无价的。
这让我想起了戴西,一位总把“有趣”放在嘴边的女人。她是当年上海最大百货商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真正的大家闺秀,也是位会在肩膀上放两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儿。她有个很多人没有的本事——总能找到坏事情中“有趣”的一面。
当时追求她的人很多,一位家境富裕的男人在送她美国玻璃丝袜时说:“这袜子很结实,穿一年都不会坏。”她却说:“我不能嫁给一个和我谈丝袜结不结实的男人,真无趣。”她最终选择的丈夫吴毓骧出身清贫的书香门第,但她说:“和他在一起很有趣,有很多话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事件,戴西的身份让她没能躲过劫难。49岁时,她被送到农场劳动。

在艰苦的环境里她想的依然是少女时代,长辈教她的趣事。她会取出一个铁丝网,在煤球炉上烤喷香的面包。她依然有喝下午茶的心情,包括在煤球炉上用通体乌黑的铝锅做许多个彼得堡风味的蛋糕,用洋瓷缸喝一杯滚热的下午茶。她有微小而郑重的坚持。这才是真正“有趣”的事。
就像后来的日子,当她无意中提起当时只吃得起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时,还会轻轻吸一下鼻子,像回忆一朵清香的玫瑰。“它那么香,有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部吃光。”那时,她刚从老式宽敞的花园洋房搬出来,住在平房里。阳光能从屋顶的破洞照进来,冬天的早晨,眉毛上总能结出冰霜。
直到80岁,她还是挺着笔直的背,优雅地走在春天的树影下,穿着平跟的黑色麂皮靴子,样子是清香洁净的。她上街买东西,还有很绅士的老先生叫住她,希望和她做朋友。而她的神情则像一个闺中女孩儿,有一点儿被冒犯的恼怒。
她的孙女提到她说:“奶奶是特别的,她从不和别人站成一堆说闲话,也从不忽视自己的美。她总是兴致勃勃,充满了情趣,就连上餐馆点餐,上菜的青年都会多看她两眼。”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是精致的女子,见人都会化妆。而我们这一代人则粗糙得多,只把化妆当成一种目的,一种取悦他人的方式,而她则是出于礼貌。记得陈丹燕写到过一个场景:老戴西坐在窗前,秋天的黄昏里,风徐徐吹进来,在旧的绿窗帘前,她仰起脸来,半闭着眼睛很享受地说:“你闻到空气中的桂花香了吗?”这个女子,随时随地都在寻找生活的趣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