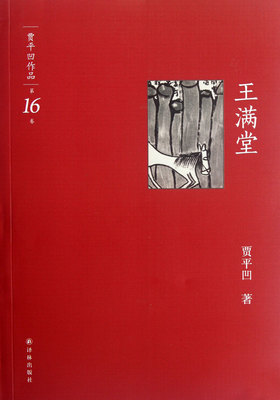贾平凹作品评介
写给作家贾平凹(2首)
祝贺贾平凹获奖
鬼才作家贾平凹,小说散文均称佳。
商洛丹凤蕴灵性,省会西安育贤达。
江南乌镇聚儒星,茅盾故里奖名家。
平凡世界白鹿原,秦腔三部震华夏。

洪文旭 2008-11-02
祝贺贾平凹馆开馆
平凹开设文学馆,安家大唐芙蓉园。
古朴雅致创作室,清静远尘绿盎然。
存放版本书画品,收藏石雕手稿篇。
去年秦腔获大奖,今朝古炉将出版。
※ 于2010年10月16日开馆,同天《文集》21卷签名发行。
洪文旭 2010-10-17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秦腔》授奖辞
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这声喂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
贾平凹获奖感言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能授予我,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当获奖的消息传来,我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那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心情也好,给屋子里的佛像烧了香,给父母遗像前烧了香,我就去街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
在我的写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也是我最费心血的一部书。当年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要写的这本书将会是什么命运,但我在家乡的山上和在我父亲的坟头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而立一块纪念的碑子。现在,《秦腔》受到肯定,我为我欣慰,也为故乡欣慰。感谢文学之神的光顾!感谢评委会的厚爱!
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遇到了桥,是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有幸生在中国,有幸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像,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 谢谢!
贾平凹艺术人生
贾平凹,陕西丹凤人,生于1952年。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美文》杂志主编。著有《贾平凹文集》二十巻。《满月儿》获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腊月。正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爱的踪迹》获首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贾平凹长篇散文选》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和2006年香港首届“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
他从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达300余种。著有长篇小说《商州》、《妊娠》、《逛山》、《油月亮》、《浮躁》、《废都》、《白夜》、《土门》、《病相报告》、《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等;中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天狗》、《黒氏》、《美穴地》、《饺子馆》、《艺术家韩起祥》、《兵娃》等;散文集《月迹》、《心迹》、《爱的踪迹》、《走山东》、《商州三录》、《说话》、《坐佛》等;诗集《空白》以及《平凹文论集》,《太阳路》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越语、日语、韩语等多种语言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传播。国际上获得的大奖主要有,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1987)、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废都》1997)、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2003)等;国内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满月儿》1978)、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腊月正月》1984)、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爱的踪迹》1989)、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2005)以及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5)、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秦腔》2006)、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秦腔》2008)等。
【代表作品】
《秦腔》
《秦腔》通过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小说采取疯子引生的视角来叙述。清风街有两家大户: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败,因此夏家家族的变迁演便成了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象征。夏家老一辈的天仁、天义、天礼、天智四兄弟是清风街最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天义、天智两人:天义从土改时期就是村委会主任,几十年公允持正的工作让所有人在他退休之后都依然敬畏他三分,天智也因为是几十年的学校校长而成了智慧的化身,何况他的大儿子夏风还是省城很有影响力的作家。清风街的人们爱听秦腔,认为它特解感情的渴。清风街出了一个唱秦腔的美人白雪,她也是引生的梦中情人。
《白夜》
这是一部非常切近现实的作品,写的是九十年代西京的现实生活。书中人物涉及到各个不同阶层,有该市最高层的行政领导,也有得意或失意的其他行政官员;有以房产条件在商海中浮沉的老户市民;有从农村进城来闯世界的打工仔、菜贩子;有考古专家、警察、演员、剪纸艺人、服装模特;有暴发户、遗老、贵族后裔等等。小说以平易灵动的笔墨,经纬于西京的各种生活场面和生活角落中,再现了上述各种人的生存状态指欲追求,以及他们之间的相恨、相爱、相欺、相助。这里有游侠与贵族的苦恋,有鬼戏班的游走活动,有官场上的上下其手,有贫民窟的赌博和幽默。
《高老庄》
《高老庄》写了大生命、大社会、大文化三个空间,又溶入最底层、最日常、甚至有些琐屑的生活流程。用感觉提升生活,用民间视角全知生活。寻访民间碑版编织于人物爱好和情节发展之中,给高老庄的当下生活一个悠远的历史纵深。几十成字不分章节,如生活原脉浑然而下,碑版的插入便起到了分切、隔离作用,欣赏有了间离效果。宏微、古今、文野、畅涩于书中两极震荡,在文化姿态和艺术策划上,亦系合题。
《怀念狼》
怀念狼:这仍是商州的故事。关于商州的故事我已经很久的时间未写了,可以说,岂止是商州,包括我生活的西京城市,包括西京城里我们那个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人人事事,任何题材的写作都似乎没了兴趣。这些年里,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样子确实有些滑稽了,穿一件红格衬衣外套上缀满了口袋的马甲,戴一项帽子,是帽檐又硬又长的那一种,而且反戴,胸前便挎着一个或两个相机,似乎要做摄影家了!其实我心里明白,……
《高兴》
《高兴》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写进了城的农民——城市中的拾荒人的命运。作品采用口述体的第一人称,语言幽默,流畅,易于阅读,是作家近年创作的最好看的小说。 刘高兴等来自农村、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同时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种人群,有乞丐,有民工,有妓女等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而且,作品在描述他们生活困境的同时,着重关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高兴》是对城市底层人群的生活记录,作家揭开城市灯红酒绿的面纱,直视他们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活着,竟然还无比艰难。他们被生活的艰辛压得无暇反思自己命运的悲剧本质,甚至会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这样的快乐和高兴的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凉。贾平凹在创作上达到了“含泪的笑”的高度和深度,作家对底层人群的关注显示了一位职业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古炉》
《古炉》的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叫“古炉”的村子里,这是一个偏远、封闭、保持着传统风韵的地方,但是这份宁静却从1965年冬天开始动荡了。古炉村里的几乎所有人,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被迫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时间一直发展到1967年春天,一个山水清明的宁静村落,在“政治”虚幻又具体的利益中,演变成一个充满了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作者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浑然一体的陕西风情,把当时中国基层“文革”的历史轨迹展示在我们面前,是作家对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生动写照。
《天气》
贾平凹已很久没出过新散文集,本书是贾平凹近三四年里的最新文字,由其亲手选编,内容丰富,不仅尽心袒露所行所思 所爱所痛,且篇篇可见其大情怀、大智慧,可见其古朴的性灵和古雅的趣味,文字朴素而有韵味,老到精粹,从容不迫,已臻炉火纯青之境。
【报道评说】
吴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
去年末,《秦腔》夺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奖,使一度与此奖无缘的贾平凹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作为一个身在小城的小女子,我除了从心底向他由衷的祝贺,再有就是想写写十年间与他的交往。我这倒不是攀他什么大名,只是想让贾平凹从神秘走向阳光。
第一次见贾平凹是在1996年。这一年的贾平凹很郁闷。一切都是因为《废都》的出版。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让贾平凹走出秦川来江浙考察。于是,有了贾平凹的高邮之旅。
高邮是扬州的一个县级市,那里有处名胜古迹叫文游台,乃当年秦少游、苏东坡等一帮文豪雅集宴乐之所。贾平凹为此留下了一幅字:文游游心。何为“游心”?如何“游心”?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10年过后,2006年。因为《美文》杂志的一个写作赛事,贾平凹分别在5月和8月两次再到扬州。因为《美文》主编的身份,免不了要在各种场合发表或长或短的讲话。他讲话时,听者无一不竖起耳朵凝神屏气。这一方面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一口商洛方言。陕西话之于扬州人,除了张艺谋的电影、郭达的小品,似乎没有其他可亲近的路径。所以,除了不时出现的“俄”(我),贾平凹的讲话对于听众来讲,基本就是“外语”。同来的毕飞宇说,他跟老贾面对面时,老贾的话能听懂80%,而到了公众场合,则只能听懂20%。这当然有个语境的问题。更主要还是老贾一开口,就是地道的秦腔——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
有一则关于他的方言轶事。一次在南京,与汪曾祺一起讲演。贾平凹慢条斯理、极为投入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想起问听众:我说话你们听得懂吗?会场上数百张嘴巴一齐喊:听不懂!结果是汪曾祺给他当起临时翻译,他讲一句,汪老翻译一句。
面对这种尴尬,贾平凹会幽默一下: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俄(我)就不用说了吧。这当然是玩笑,也是一个机智的借口。
贾平凹常说,“我是个笨人”。不会说普通话,笨。不会用电脑写作,也是笨。
有段时间,他下决心要用电脑写作。机器搬回来了。可这字没法打。用拼音吧,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哪里还谈得上拼音?用五笔吧,就是把字根贴在墙上,也记不住。试试手写板吧,还是不行,电脑不认他的字。勉强写了200来字,就发狠再也不用电脑了。他从小爱音乐,想拉二胡,可到现在也学不会,指头特别硬。他对此解释为:我可能是很笨的那种人,就好像一条狗,你给它开了再大的门,它还是从小洞里钻;就好像一只鸡,你把它放在粮堆上,它还是扒着吃。
贾平凹家里有车,但他不开。因为他当年骑自行车还摔跟头呢,摔断过腰,还撞过不下5个人。贾平凹也用手机,但除了接打电话,手机的其他功能于他而言基本上是聋子的耳朵。有一次,他说,我这手机怎么没有来电储存功能?别人拿过去一看,好好的呀,是他不会用。指导了半天也教不会他,怎么办?只好找张纸来,用最明白浅显的语言写下:手机来电存储功能操作方法一二三……这就是他自己所谓的“笨”了。
果然笨吗?你听说过哪个笨人能像他这样,写出几十本散文、小说?据说他年轻时,有一年竟创下了每周发表一篇作品的奇迹。这不但与“笨”丝毫联系不起来,而且简直可算得上天才了。用汪曾祺的说法,贾平凹是个“鬼才”。《美文》执行主编穆涛是河北人。一次车过秦岭,穆涛说:你们陕西人真谦虚,那么大一个山,叫个岭。老贾反应很快:你们河北人更谦虚,那么大一个省会,叫个庄。这段经典对话,都被老贾写到文章里了。说自己“笨”,老贾这是自相矛盾呢。
对于他自嘲的“笨”,也许叫“拙”更精当些。“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拙和讷是贾平凹给人的外在印象,而巧与辩才是真实的他。
在公众场合,贾平凹常显现出他的“弱项”:不善言辞,说话对他是一种负担。他自称对外界有一种胆怯心理,社交不行,讲话不行。他说这是遗传自他的父亲。
贾平凹的父亲是教师,“文革”中翻档案翻出他是“特务分子”“敌特分子”,被打成了反革命。事实是这样的:胡宗南在西安举办一次报告,各个学校把参加报告人员的花名册报上去了。那天贾父偷偷跑出去看秦腔了,并没有参加报告会。但是资料报上去了,在档案里装着,后来“文革”的时候把那场报告定为“特务训练班”,他父亲就这么被打成了“特务”。
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以后,不敢说什么话,每天还教育子女:出去以后必须对谁都恭恭敬敬。贾平凹说,慢慢地,说话、社交的能力就减弱了。
那天从扬州去高邮一所中学,参加一个活动。车上聊天,我问贾平凹: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到西安以外的城市,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你最愿意去的可能是哪些地方?他想了一下,说:我最愿意一个人呆着,哪儿也不去。怕见人哩。
说着说着就见识了他的“怕见人”。车到高邮那所学校的门口,贾平凹忽然一声惊呼:怎么这么多人?不是说就搞个座谈会吗?我往车外一看,校门两边,数十位学生穿着整齐的校服在列队欢迎呢。下车,献花,跟当地领导拍照,看得出来,贾平凹始终紧绷着神经。这种场面是他最怵的。西安方面同来的人说,今天可把老贾吓坏了。
离开扬州的前一天,到富春吃早点。出来是得胜桥。小巷两侧一溜儿排开小铺子,卖扬州三把刀和暖壶、耳挖等别处难寻的老物件。
贾平凹走得极慢,边看边问,这是扬州的古玩市场吗?我告诉他古玩市场在天宁寺,鼓动他抽空去一下。后来一想,西安是什么地方,地下宝藏可以算得上世界之最,随便找个地方挖一锹,就能找到宝贝,扬州的古玩市场他哪看得上啊。
在一个卖烟斗的摊位前,贾平凹站住了。他拿起一只小巧的木嘴烟斗:多少钱?摊主要12元,他听不懂,我翻译了一下。“10元吧!”成交。看起来贾平凹对这只小烟斗还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木嘴有点瑕疵。据他自己说,他收藏的烟斗有数百只,最贵的值五六千,这次买的是最便宜的一只。他说:“我不喜欢弯把的。”难怪单单选中了这把破了相的。那些漂漂亮亮的,只因为是弯把,就入不了他的法眼。这一直一弯,其实也可看出贾平凹的品性来。
许多人都知道贾平凹爱收藏。据说他的工作室内,奇石、陶罐、字画、拓片、佛像各得其位,甚至还有几张狐狸皮和老虎皮。
他收藏的第一大门类当属奇石。他家里到处可见石头,包括厕所。我想住在他家楼下的人一定患有失眠症,担心夜里楼板吃不消,石头掉下来砸自己身上。
“姓贾的都与石头有缘。贾宝玉就是青峰埂下的一块顽石。”嘿,他还找到依据了呢。到了山区,贾平凹的眼睛就像粘在了石头上,在沟沟坎坎里到处逡巡。有一次,他还真的在河滩上捡到一对石头,上面的纹路正好是“平”“凹”二字,也算是机缘巧合了。
贾平凹早期曾写《丑石》自喻。贾平凹还自称“长安第一丑人”。这些平凡的石头是不是让生在农村的他有惺惺相惜之感呢?
西安是汉都城,出土的汉罐自然特别多。一般人忌讳这些从墓葬里挖出的东西,贾平凹却说,他不怕鬼,他觉得这带鬼气的东西激活了他无穷的想象力。他想这陶罐都是泥土捏成又烧熟了的圣物,那汉罐里该有司马迁吧,唐罐里该有李白吧?他因此也希望自己百年之后化为泥土了,也变成陶罐被人收藏着。
该说说贾平凹的书画了。贾平凹的书画确实不好说,也说不好。其实,文人书法、文人画,本来就不该拿去跟专业书法家、画家的作品相比较。贾平凹写写画画,挣点家用谁也管不了。愿买愿卖,公平交易。贾平凹自己也说,写字比文学创作来钱快。
当代作家中,有书画名声的不少,汪曾祺是很突出的一个。贾平凹是钦佩汪老的,汪老的文章,汪老的书画,汪老的人品。当年,这一老一少两位大作家是有着一段交情的。
这次在高邮,参观汪曾祺文学馆,贾平凹写下了“到高邮想汪老山高水长”一幅字。写完后,自己很满意:写得好!回扬州的车上,还在想这事儿:咦,今天写的有点像汪老的字。是汪老扶着我的手写的。这十个字,三三四的音步,怎么看都有点像京剧里二黄导板,让人联想到京剧《沙家浜》里的唱腔:“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到高邮,想汪老。他到底想起了汪老什么?肯定想到第一次见面了。他谈起,与高邮的联系源于汪曾祺老先生。他与汪老第一次见面是汪老到西安,那时,他还不是“冒号”,用他的话说,还没有“列支权”,因而,在家里烧了点家常菜,备了一瓶酒。刘心武提醒说,汪老酒性很好,于是又加了一瓶。喝酒时说了些什么?贾平凹没说,大概他也记不清了。不过一老一少的缘分就此结下。
他肯定也想起了与汪老的第二次见面。那是1987年,在桂林,参加漓江出版社的一次旅游文学笔会。就是那一次,汪老送了贾平凹“鬼才”之称,还专门解释:鬼才者,非凡才能之人也。贾平凹则作诗一首,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愿得沾狐气,林中共营生。”
他也许会想起汪曾祺对他的评价:“一个很平易淡泊的人”。1988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获美国“飞马文学奖”。看到自己喜爱的“鬼才”获此殊荣,汪老很开心,并且在给《瞭望》杂志的专文中写道:“平凹确实是一个很平易淡泊的人。从我和贾平凹的接触中,他全无‘作家气’,在稠人广众之中,他总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限度。他很寡言,但在闲谈中极富机智,极富幽默感。”
2000年冬,得知高邮建汪曾祺文学馆,贾平凹寄来一幅字:“文章圣手”。并在信中写道:“知高邮办汪曾祺文学馆,真是高兴!汪曾祺是应该建庙立碑的人物。汪老在生前,我与他有过数次交往,现每一回想,音容宛在,如是昨天的事。为表对汪先生的敬重和怀念,我写了一张字,望接纳。”
贾平凹有过一个著名的“绯闻”,是关于三毛的。
三毛去世之前床头放着贾平凹的《贾平凹散文自选集》。
三毛去世后的第11天,贾平凹收到了三毛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媒体兴奋起来了。媒体一兴奋,什么八卦消息都出来,以讹传讹,弄“贾”成真。传到后来,竟有人说是贾平凹为了三毛离婚什么什么的。一般来说,八卦消息总得有点影子。可贾平凹离婚的时候,三毛已经去世快一年了。更何况,贾平凹与三毛这桩绯闻,还真的没影子。正像我们家乡的一句方言:无影造西厢。
其实,提到三毛,贾平凹的心里,很不好受。两个投缘之人,没来得及见上一面就阴阳两隔,确实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情。
之前贾平凹并不知道三毛对他的书感兴趣。在杭州开会,三毛碰到西安作家孙聪,三毛说喜欢贾平凹的小说:“他用词很怪,可很有味,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眼睛都要看瞎了。”并说,明后年,她要以私人名义去西安,问问平凹愿不愿给她借一辆旧自行车,陪她到商州走动。说她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找平凹别的作品,但没寻到,希望平凹寄她几本,她一定将书钱邮来。三毛还开玩笑地对孙聪说:“我去找平凹,他太太不会吃醋吧?”临分手时请孙聪送一张三毛的名片给平凹,上边用钢笔写道:“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
贾平凹听了孙聪的话,便包扎了4本书去邮局,且给三毛写了信,说盼望她明年来西安,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他就和她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小事。
三毛去世之前床头放着的《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就是那次寄过去的。
信寄出后,贾平凹就盼着回信,盼了20天,等来的却是三毛自杀的噩耗。
2000年底,贾平凹曾到鸣沙山的三毛衣冠冢,点上三支香烟,以烟代香,祭奠三毛。
在贾平凹的眼中,“三毛是个真实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优秀作家”。
贾平凹是那种要么不写,一写就动静很大的作家。动静大得好像满街市都是他的作品,好像他的小说总是泉涌不断地写出、连篇累牍地出版。事实上,他的小说大都是数年磨一剑,《废都》就不说了,光是《高老庄》、《怀念狼》以及《秦腔》这3部长篇差不多费了他十多年的生命。之所以会给人写得多、出得猛的感觉,就在于他的长篇小说一出来,都能引起反响,你评他说,媒体再跟在后面加油添醋,等到渐渐淡了下去,他的新作又出来,又让评论、新闻出版各界人士热闹一阵。对于作家来说,这样一种热劲儿确实令人羡慕。
作家都有代表作,但是老贾说他没有代表作,只有重要作品。《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都算是。他所说的重要作品,就像路转弯处的标志,对他本人具有重要的意义。什么是好作品?贾平凹说,如果50年后还有人在读,就是好作品。不管在它问世时曾经怎样红火,若50年后没有人看了,那就不是好作品。世界上最残酷的就是时间,时间可以消磨好多东西,也可以淘汰好多东西。
人生就像“凹”字,有高有低,这是贾平凹对人生的理解。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处境,也是贾平凹对人生的理解,从“平凹”这字面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一理解。年轻时的贾平凹,相信刻苦、努力、追求,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年轻的贾平凹曾经在好友那里说过一段真心话:“我一个山里娃,凭啥在城里混日月?不就是凭一支笔么?”说得好,凭一支笔,贾平“娃”终于成了贾平凹,山里娃因此打出了自己的天下。 (2009年02月19日;中国文化报)
阎连科:平凹说佛
几年之前。
几年之前的一个笔会,在辽宁锦州。会间大家去锦州辖县参观一个古庙。
古庙本无太多可以记忆,如树木在林地最易让人疏忽一样。况且,我是那种对人文极为无知的人,只是大家都去,也就从众去了。路上,和许多人聊天。到了下车,和贾平凹齐肩,边说边走。因着边走也才边说。说走中,缘于对他写作的敬重,从不敢像别人那样似熟非熟地叫他老贾,也不敢和他勾肩搭背,二人只是那么彼此客气,彼此敬着,彼此有着心距,又彼此很感亲切。就说就走,齐肩踏进了庙的大堂。那庙和他处寺庙并无二致,青砖青瓦,雕梁画栋,佛塑高大,字画满堂。人就拥着进了,扯话和聊语,顿时冷结下来。原来,所有的人都是知道的,在神前佛边只可静默虔敬,不可喧哗胡说。就都在静默中缄脚缄手,屏声屏息,看这看那。我不知道别人都看了什么,如来、菩萨、金刚、匾额、对联,大抵也就如此罢了。而我除了这些,还看到了和佛像不谐的一景:入门正对面的高大墙上,有画墨入木的一幅巨制的菩萨木刻像,像的两侧,是木刻的一副对联。对联的内容,我并未仔细去读,只是看到那木刻对联的右挂,因为老旧,抑或别的原因,从墙上垮了下来,倒歪,下垂,随时都会掉下一样,连带视角的关系,因为右挂欲落,似乎拉得菩萨的挂像也不周不正,不是那么端庄。
从庙里出来,平凹问我:“怎样?”
我说:“最该把菩萨像两边的挂联挂个对称周正。”
他就回头看了。
只看了一眼、轻捷如飞的一瞟,就又回头来说:“连科,不是那挂联和像挂得不正,是我们的眼睛不正呢。”
我哑然悟开。从此记住平凹兄的与我说佛,甚于所有人所有小说中所有的细节与情节,都没有这次说佛让我如此咀嚼意味,入耳难忘。 (2010年03月09日;北京晚报)
阎纲:我说贾平凹研究
我常说:“平凹是我的小弟弟、大作家。”他少有才气,赋性聪颖,《满月儿》出世,我惊呼他是真“作家”,是“关中才子”,很快,声名远播,开一代新风,独步文坛,成了大作家。
王军同志很懂文学,他评价贾平凹说:最乡土又最潮流,最纯粹又最复杂。还有趣地说:平凹“是当代中国文坛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也是西安标志性的文化景观之一”。
希望新建成的“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同样成为西安标志性的文化景观之一。
顷读《古炉·后记》,平凹说他瞌睡少了,老了,我一惊。今年,托尔斯泰逝世整整一百周年,托翁一生反对农奴制、抗议沙皇,写出三大巨著,晚年思想激变,放弃财产和版权,与妻子反目,八十二岁离家出走,客死他乡。平凹多大?五十郎当,敢言老?你这么说,老汉今年七十八,还有脸活下去么?
平凹眼睛向下,是个平民作家,同平民相亲,同读者交心,人们喜爱他。
平凹把世事看透了,把文学看透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与人为善,与世无争,非礼勿动,低调处世,时时刻刻把芸芸乡民、山寨草民、贫苦平民挂在心上,不回避他们的落后、愚忠、狡黠、野蛮甚至残暴,恨铁不成钢。他是他们的儿子,土得掉渣。
平凹是个两只手伸得很长的平民作家,当有人热衷于自我造势时,他读经,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上天入地,打通三才天地人,打通文、史、哲,打通诗、书、画;技法上借助意象叠加的现代派,天人合一,左右逢源,微观可见蚂蚁搬家,宏观可见神话世界,望天遥测生死吉凶,写实更兼写虚和写意,藏禅意于琐细之中。终成鬼才、全才。
平凹从不拿文学训人,而是同常人平等对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所以,他的文字既“关风”又极其平民化,五行八作,个性鲜明,水墨白描却极富色彩,率性而且风趣,成为文坛独立的一体。
平凹成功的秘诀是:说平常话,用形象说话,用感悟传神。
贾平凹开一代新风,爱平凹、学平凹的人全国知多少!《美文》的周围团结的作家越来越多,既当作家,又做编辑,贾平凹的“粉丝”谁数得过来?
平凹灵性十足,细腻从容,俗而雅,巧而奇,色而空,实而虚,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中国文学史上,“平凹风格”自成一家!
“贾生才情更无伦”,贾平凹非常值得研究。 (原载陕西日报)
贾平凹:一个农民的书写
舒晋瑜
贾平凹(速写) 罗雪村绘
“我就这样做一辈子农民吗?”在自家泥楼子上的14岁少年贾平凹发狠说。他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一撮毛儿高高翘起。
他的梦想是上大学。他那么盼望着考试,因为一考试就能显示他的存在。可是“文革”改变了命运。中学毕业后当了农民,下地却连正经农活都干不来,收入还不如妇女。这使他感到屈辱。因父亲“反革命帽子”的牵连,被要求“不能乱说乱动”,当兵、招工、民办教师、代理教师……全都与他绝缘,从此他的性格变得胆怯、自卑,少言寡语。
他发誓要离开,剥掉这个“农民皮”。1971年,偶然的机会,他上了西北大学。他背着被褥,坐上了去省城的汽车。
他以为结束了自己的农民生涯,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到陌生的城市去。可是,20年后他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离开的那一瞬间就开始了。
在贾平凹3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创作素材都来自他的家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村。从《浮躁》、《土门》、《高老庄》,到《怀念狼》、《秦腔》、《高兴》,从土地承包改革到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农村发生的大转折都在他的作品里:《秦腔》写农民如何离开土地;《高兴》则写农民离开土地后的生活;到了《古炉》,他则转向对“文革”这场历史浩劫中的人性的解读,目光所对准的,依然是山水美丽、六畜兴旺、闭塞贫穷的山村。他的笔下有对故乡的无比依恋和怀念,也有对人离开土地之后怎么办的迷茫和追问,更有面对商业化浪潮冲击下人性异化扭曲时充满批判的矛盾心情。“作为一个作家,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们,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只能写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东西写出来。”贾平凹说。
他对家乡的感情越来越复杂。在他的心里,故乡因父母的存在而存在。那时,贾平凹经常回去,愿意早早看到迎在半路的父亲,愿意听熟悉的那一声“平回来了!”可是现在的家乡对他而言,越来越是一个“概念”。故乡所呈现的形态对他而言,越来越陌生。“像是有了疤的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了荷花,愈开愈艳,却不再属于我。”他清醒地发现,自己所熟悉的农村在一步步消失,农村的文化传统在渐渐淡出。他不知是该歌颂还是去批判。他能做的,是用《秦腔》为故乡的过去树了一座纪念的碑子,借主人公夏风,他似乎有意识地谴责自己离开土地后精神上的背叛,也记录了乡村变化中的哀伤。
《秦腔》后来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从1978年《满月儿》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他常常以获奖者的身份出现于各种颁奖典礼。他的头衔越来越多: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协主席甚至于书法家、画家、秦汉文物鉴赏家。他自称不善交际,不会说话,实际上,浓厚纯正的陕南方言,却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熟知,他的作品以英、法、德、俄等文字翻译,走出国门,抵达广泛的阅读领域。
所有这些,于他只是风清云淡。即使获奖,也如“过河遇到了桥,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在他心里,自己就是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他体味写作里边的甘苦,如同农民种田耕作时的欢乐和满足。这些写作之外的爱好,在他看来,“就好像一个人的饮食要大米和白面、水果与蔬菜相互搭配,有时喝咖啡有时喝茶,是一种补充和调剂。”而在他这份憨厚朴素下,掩藏着万丈雄心,那就是剖析这片土地所呈现出的人性的种种缺陷,同时让笔下的世界充满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
贾平凹时常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当年不是偶然地进了大学,不是因为在大学里不知未来去向如何而开始了写作,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一位农民。一个矮小的老农。或许日子还过得去,儿孙一群,我倚老卖老,吃水烟,蹴阳坡,看着鸡飞狗咬。或许,我还得进城去打工。
多年前,村里生产队的公房要处理,他的父亲让他置办一套。他有点不屑:谁还回来再住那个东西!他走得那么决绝洒脱。可是现在他发现,不管走得多远,自己身体里始终流淌着农民的血液,从孩子时起就具有的农民德性,根深蒂固,永远无法真正地褪去。他的视线也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农村。即使现在,也经常有老家人来西安找他,或看病求医,或想办个希望小学,甚至要个修路的资金……家乡人在城里打工的也会到他这里来。
贾平凹接纳并沉浸其中。似乎这样,才更能唤醒自己的农民本色。在他的《六棵树》中有一棵痒痒树,一旦移入城市,就失去了根和生命。他何尝不是这样的一棵树。不过,这棵树虽然深深扎根于生他养他的棣花村,却又超越于此,怀着悲悯之心一次次地回望并反思。他的出生和成长环境决定了他写作的民间视角。正是以这样的身份认同和视角,他探究并关怀着时下的中国,给我们提供着一卷卷不可替代的、厚重朴素的历史记录。
如此,农民贾平凹的书写,是棣花村的幸运,是农民的幸运,又何尝不是读者与中国文坛的幸运?
(2011年03月18日;人民日报) (以上链接文章均来自网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