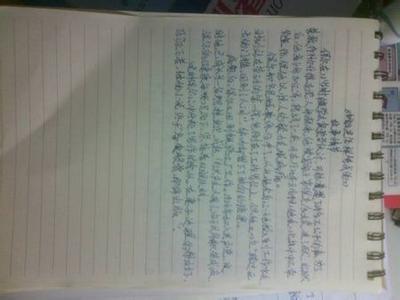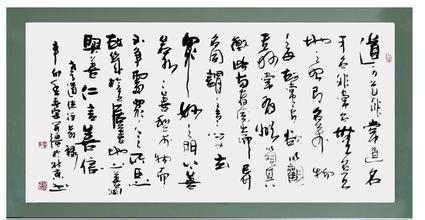选自《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
本文已取得授权
文丨[德]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Richard David Precht)
译丨钱俊宇
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想象以下情况:你到医院去探视一位女性友人。由于你不太确定朋友的病房在几楼,因此按错了楼层。你走出电梯,来到一个部门,在候诊室里等了一会儿后被请了进去,医生给你打了麻醉药,当你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病床上,而身旁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男子,你和他的身体之间连接着复杂的仪器管线。你呼叫医生,得知这名男子是罹患肾脏病的著名小提琴家,让他活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将他的循环系统和另外一个血型相同者的循环系统相连接,而你正是那唯一血型相符的人。
由于那是很有名的医院,他们当然为这场误会深表遗憾,因为他们以为你是自愿捐助者。他们也愿意拆掉你和这位小提琴家的管线,不过小提琴家会因此死亡;要是你愿意与他维持9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康复,而你就可以和他分开,而且不会危害他的性命。你会怎么做呢?
这个故事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女教授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她的答案是:如果你愿意和那名小提琴家分享你的肾脏9个月,并忍受躺在病床上的痛苦的话,那么你真是个好人,不过你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去这么做!这个例子的重点并不在于那虚构的小提琴家,而是一个普遍的情况:你在违背心意、毫无计划,甚至有可能是在暴力胁迫下,必须以身体直接为另一个“人的生物体”负责。而这种状况最常出现的实例,并不是和患肾脏病的小提琴家接上导管,而是意外的怀孕。
汤姆森认为,一个非自愿怀孕的妇女,她的状况与非自愿和小提琴家相连接的状况非常类似。而就像你不会被迫为小提琴家的生命负责一样,妇女也不必为那非她所愿于体内成长的胚胎负责。汤姆森还认为,女人的自主权大于那在非自愿条件下产生的、对另一个生命的责任。这个论点提出后大受欢迎,它启发了女性主义“我的肚子是属于我的!”的口号。
不过,这个例子却有一个重要的思考陷阱:那位小提琴家是个精神智力成熟的成年人,但胚胎或胎儿呢?相对于成人来说,它们是否拥有绝对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三条路可以选择,即康德的“人性尊严”概念、边沁的“功利主义”和豪瑟的直觉“道德感”。
康德的观点
让我们从康德开始吧。在他丰富的著作里,只有一处谈到胚胎,他是在阐释婚姻法时提到的。康德认为,胚胎是一个已经具备所有人性尊严的生物。如果这不成立的话,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也就是必须指出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始于子宫内的哪个时间点。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康德认为,“自然”是不知道何谓自我意识,何谓自由的。那么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尊严又是如何且于何时降临人的身上的呢?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解释康德的回答:胚胎的自由奠基于父母的自由。因为父母是自愿,也就是在自由结合(婚姻)的条件下创造它的!自由结合的果实就是一个自由的胚胎。换句话说,这同时也表示:只有在自愿且有婚姻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胚胎,才是自由和具有人性尊严的人,除此之外的都不是。康德以这个在今天看来有些奇怪的定义来回应他所处时代的问题。
1780年,曼海姆市(Mannheim)的行政专员拉美灿(Adrian von Lamezan)以一个奖金为100个度卡特(Dukaten,14~19世纪欧洲通用的金币名)的问题征答:“什么是制止杀害幼儿的最好办法?”这一征答共收到400封来信,反响非常惊人,因为堕胎甚至更严重的杀害初生儿行为,在18世纪算是普遍现象,而大部分是因为雇主对女仆的性侵害。这在当时是个迫切的问题,因为杀害私生婴儿虽然是个禁忌话题,却又众所周知。康德在他法律学说的另一处探讨了杀害幼儿的行为。由于私生婴儿并非完全的自由,而是(如未经允许的货品)“潜入”了子宫,因此他把杀害幼儿视为和在决斗中将对方杀死一样,是一种“不损害名誉的过失”,并主张减轻刑责。
在今天,用康德的观点来论证是绝对行不通的。康德无法证明在没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位于子宫内的胚胎的人性尊严从何而来,因而不能谴责杀害非婚生幼儿的行为,甚至连非婚生的成年人也包含在内!因此,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康德对于为何应该绝对保护(婚生)胚胎的解释是很牵强的。而在今日对于堕胎问题的讨论中,大概没有任何引证康德的人会认同他对于非婚生和婚生的胚胎以及婴儿的差别态度。
功利主义者的观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条路:功利主义。作为功利主义者,我们首先必须对于“胚胎的价值”达成共识。胚胎是个有绝对保护价值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胚胎是一个“生物人”,因为它在生物学上是属于“智人”(Homo sapiens)的;但是它在完整的道德意义上并不是人,也就是说,它并非一个“位格”(Person)。但“位格”究竟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人才是一个“位格”。晚近的功利主义者将这个观点纳入他们的理论,他们不仅考虑到了生物的基本欲望,而且更重视复杂多面的“人的”愿望。人们称之为“偏好功利主义”;几乎所有边沁的近代信徒都属于此派。功利主义者思及高度发展的偏好(愿望和意图),会认为杀人(包括贝莎姑妈)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当这个人有继续活下去的强烈意愿时。
对偏好功利主义者来说,并不存在一个足以绝对禁止结束胚胎或胎儿生命的理由。当然,胎儿自某个生长阶段起会产生意识,但是猪和牛也有形态类似的“意识”,我们却还是照杀照吃不误。据我们所知,胎儿并没有一个在“复杂多面的意图和愿望”意义上的意识,因此便产生了一个通行的基本准则:胎儿的生命原则上是可以在任何发展阶段予以终结的,尤其是当它能明显减轻母亲的痛苦并大大提升她的幸福时。
以上是功利主义的论点。无疑,这个论点比引证康德对婚生胎儿的绝对人性尊严要来得清楚。不过,这个立场同样也有缺陷。功利主义引起最严重的抗辩其实是:如果“一个胎儿不能获得绝对的保护,是因为它没有完整的意图和愿望,所以不是一个人(位格)”正确的话,难道同样的道理不也适用于刚出生的婴儿吗?毕竟小孩总也得到两三岁才会成为有自我意识的、自由的人(位格)。如此一来,“偏好功利主义”岂不是太极端——除了堕胎之外还允许杀害三岁以内的幼童吗?
事实上,确实有些偏好功利主义者认为一个孩子的绝对生存价值是从两岁才开始的。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赞成在没有重要动机的前提下就可以杀死未满两岁的孩子。但是个中原因并不在于人(位格)自己的价值,而在于社会的后果。幼童对于父母和亲属来说几乎总是有着极大价值的,而就算是生活在孤儿院里的弃婴,也至少都是需要救助者,有权要求社会的保护;然而,偏好功利主义者却很难说明为什么保护弃婴比保护动物重要。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可以说,一个不以关怀反而以轻率的态度面对生物的社会,有趋于野蛮之虞;但这不是幼童生存权的有力论证,而这也正是偏好功利主义在此问题上的罩门。
豪瑟的观点
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条路径,看看豪瑟的观点。他认为,每个正常人都有类似道德感的东西——一个“直觉的”道德。如同我们看到的,功利主义在堕胎问题上有个清楚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带来的结果,即无法解释对幼儿生命的绝对保护,还会让许多人直觉不妥。
直觉在两点上纠正了功利主义。首先,它告诉我们堕胎施行的时间越晚,问题就越大。因此在德国将合法堕胎设限于三个月之内的规定是有其道理的。就算胎儿的生命从第91天到第92天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另一个层次,我们还是可以概括地说,胎儿在三个月后已达到了一个自然的界限,也就是还能使用“不具意识的生命”这个概念的界限。其次,直觉赋予了新生儿及幼童一个绝对的生命权,因为他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直觉上已经是具有相同价值的人的生命了。就算有人没有这样的直觉(即在情感上无行为能力者),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而每一种道德形态都有这样的问题。前面曾提到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公共利益很重要,功利主义者却仍然将这个感受设为前提,虽然“直接的”生物本能应该比“衍生性的”社会本能更可信才对。
我们可以说,关于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的权利,并不源自“生殖行为”,因此我们也看不出为什么在三个月之内不可以堕胎。杀害发展超过三个月的胎儿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则将逐月增加。当父母获知自己可能生出一个有严重智力或身体缺陷的孩子而又没有能力照顾他时,他们很可能会狠下心决定结束其生命。功利主义把父母与胎儿两者的希望、意图以及潜在的痛苦放在天平上比较,虽然很残酷,却是无法避免的。
本期推荐书目

作者:[德]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Richard David Precht)
译者:钱俊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