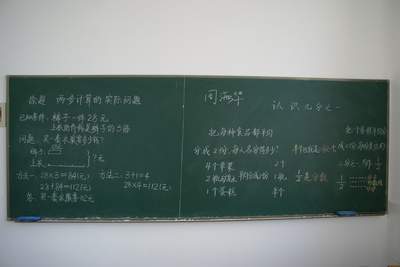《百年孤独》是为中国人写的
□李洱(北京 作家)
1985年的暑假,我带着一本《百年孤独》从上海返回中原老家。它奇异的叙述方式一方面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使我昏昏欲睡。在返乡的硬座车厢里,我再一次将它打开,再一次从开头读起。马孔多村边的那条清澈的河流,河心的那些有如史前动物留下的巨蛋似的卵石,给人一种天地初开的清新之感。用埃利蒂斯的话来说,仿佛有一只鸟,站在时间的零点,用它的红喙散发着它的香甜。
但马尔克斯叙述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有如飓风将尘土吹成天上的云团:他很快就把吉卜赛人带进了村子,各种现代化设施迅疾布满了大街小巷,民族国家的神话与后殖民理论转眼间就展开了一场拉锯战。《裸者与死者》的作者梅勒曾经感叹,他费了几十页的笔墨才让尼罗河拐了一个弯,而马尔克斯只用一段文字就可以写出一个家族的兴衰,并且让它的子嗣长上了尾巴。这样一种写法,与《金瓶梅》、《红楼梦》所构筑的中国式的家族小说显然迥然不同。在中国小说中,我们要经过多少回廊才能抵达潘金莲的卧室,要有多少儿女情长的铺垫才能看见林黛玉葬花的一幕。当时我并不知道,一场文学上的“寻根革命”因为这本书的启发正在酝酿,并在当年稍晚一些时候蔚成大观。
事实上,在漫长的假期里,我真的雄心勃勃地以《百年孤独》为摹本,写下了几万字的小说。我虚构了一支船队顺河漂流,它穿越时空,从宋朝一直来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有如我后来在卡尔维诺的一篇小说《恐龙》看到的,一只恐龙穿越时空,穿越那么多的平原和山谷,径直来到二十世纪的一个小火车站。但这样一篇小说,却因为我祖父的话而有始无终了。
假期的一个午后,我的祖父来找我谈心,他手中拿着一本书。他把那本书轻轻地放到床头,然后问我这本书是从哪里搞到的。就是那本《百年孤独》。我说是从图书馆借来的。我还告诉他,我正要模仿它写一部小说。我的祖父立即大惊失色。这位延安时期的马列学员,到了老年仍然记得很多英文和俄文单词的老人,此刻脸涨得通红,在房间里不停地踱着步子。他告诉我,他已经看完了这本书,而且看了两遍。我问他写得好不好,他说,写得太好了,这个人好像来过中国,这本书简直就是为中国人写的。但是随后他又告诉我,这个作家幸好是个外国人,他若是生为中国人,肯定是个大右派,因为他天生长有反骨,站在组织的对立面;如果他生活在延安,他就要比托派还要托派。“延安”、“托派”、“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反骨”、“组织”,当你把这些词串到一起的时候,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就像芥末一样直呛鼻子了。祖父几乎吼了起来,他对我父亲说:“他竟然还要摹仿人家写小说,太吓人了。他要敢写这样一部小说,咱们全家都不得安宁,都要跟着他倒大霉了。”
祖父将那本书没收了,并顺手带走了我刚写下的几页小说。第二天,祖父对我说:“你写的小说我看了,跟人家没法比。不过,这也好,它不会惹是生非。”祖父又说:“尽管这样,你还是换个东西写吧。比如,你可以写写发大水的时候,人们是怎样顶着太阳维修河堤的。”我当然不可能写那样的小说,因为就我所知,在洪水漫过堤坝的那一刻,人们纷纷抱头鼠窜。
两年以后,我的祖父去世了。我记得合上棺盖之前,我父亲把一个黄河牌收音机放在了祖父的耳边。从家里到山间墓地,收音机里一直在播放党的十三大即将召开的消息,农民们挥汗如雨要用秋天的果实向十三大献礼,工人们夜以继日战斗在井架旁边为祖国建设提供新鲜血液。广播员激昂的声音伴随着乐曲穿过棺材在崎岖的山路上播散,与林中乌鸦呱呱乱叫的声音相起伏——这一切,多么像是小说里的情景,它甚至使我可耻地忘记了哭泣。但是二十年过去了,关于这些场景,我至今没写过一个字。当各种真实的变革在谎言的掩饰下悄悄进行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慢慢集中到另外的方面。但我想,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会写下这一切,将它献给沉睡中的祖父。而墓穴中的祖父,会像马尔克斯曾经描述过的那样,头发和指甲还在生长吗?
毫无疑问,《百年孤独》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是小说中的皇冠。它虽然写的是拉美,但每个中国人似乎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虽然我后来的写作与《百年孤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仍然要对它表示敬意。它最初带给我的阅读体验,至今也仍然清晰如昨,比如现在,我就再一次想起了从祖父的棺材里传出来的声音,听到了山林中的鸟叫。我仿佛也再次站到了一条河流的源头,那河流行将消失,但它的波涛却已在另外的山谷回响。它是一种讲述,也是一种探究;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回忆,也是在空间的一隅流连。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