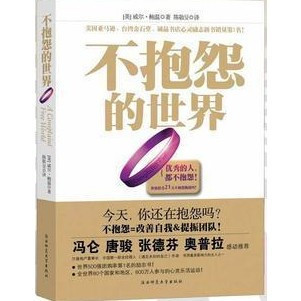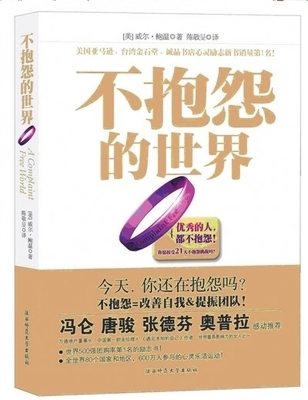一百个写作者说小说可能,一百个写作者说小说不可能。加缪这种二元对立论的涵义,我仅能以母亲为例作一点盲人摸象式的揣摩。
母亲是个贫穷的农妇,养育了7个儿女,活到91岁安然离世。按平均寿命,她可能占有了别人的份额。70多岁,她抚养孙辈。80多岁,孙辈都进了学堂,她不能劳动了,靠子女养活。对此,她心存愧疚,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江山坐江山的理直气壮。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唤》中写了一个失手打破饭碗害怕儿子责骂嫁祸孙子和装死的“爷爷”。那个“爷爷”酷似母亲,读得我泪水盈眶。母亲老成一棵枯芦,一个人在五楼“囚禁”了11年。孤独和无以倾诉的日子,比中年时代因偷窃生产队红薯关进劳教所还难受。子女们偶尔来看她,她就拽住我妹妹的手,要求给她弄一点毒药。有一次,我妹妹就预先在兜里藏了一小袋奶粉,母亲再一次求她弄毒药时,便悄悄掏出来撕开,说,“弄到了,我喂进你嘴里。一点都不痛苦,一场瞌睡就醒不来了。”母亲说,“不!不!还等一段日子吧。还等等。”母亲在等待什么呢?有可能吗?
外公重男轻女,两个儿子都读到了县里的秀才,女儿却只能纺纱织布采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兄弟们能背下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她也能背。我的儿子长到两岁,母亲就教他念《三字经》、《诗经》、《琵琶行》,只是一句都不懂。不幸的是,两个秀才都被日本人杀了,外公后悔得要死,早知如此,不如送女儿读书。母亲出嫁前没有等到外公送她读书的那一天,但她始终在等待。我想,那两个秀才如果活着,肯定是级别不低的官僚,那么,外公外婆晚年就有可能不会咀嚼“五保户”的凄凉;或者如果外公舍弃儿子,送女儿读书,那么,母亲当个女市长未必不称职;还有一种假设,如果满清王朝早垮台50年,中国军事实力堪与美国比肩,日本人打不过卢沟桥,那两个秀才断然不会被杀。作为现实生活,那些假设都没有可能。作为小说,都有可能。
父亲是个识字的农民,兼做小商贩。母亲辛辛苦苦摘一季茶叶,加工烘干后装入木箱。父亲挑着几箱子香气扑鼻去了汉口,母亲就在家里等待。结果,等来的是丈夫两手空空。茶叶肯定是卖掉了,而且价钱不错。钱却馈赠给了汉口的赌场。母亲唠叨,“我辛辛苦苦种一季茶,给你抚养7个儿女,也该给我一点零花钱吧?”父亲说,“遇到土匪,抢了。你又不认得钱,也不懂货币交换,要钱干什么呢?”我们兄妹长大后,对父亲无比痛恨。父亲就说,“假如我赌博赢了一百万银洋,你们就是贵族了;幸好我输个精光,不然土改必然划成地主,那么,一家人就跟着倒大霉!你们应该感激我。”父亲的诡辩虽然荒谬,而放在小说里,都是可能的。一旦解除想像翅膀的羁绊,小说便会丰富多彩,险象环生。恰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的可能,如同索尔仁尼琴,来自于放逐。
父亲嗜赌,常输得家里无米下锅。有一次,武昌某个赌友上门讨债,父亲指着地上一堆儿女说,“钱,委实还不起,挑个儿子抵上吧。”那赌友正愁后继乏人,就挑了一个准备抱走。母亲像一匹凶恶的母狼扑上前,揪住那赌徒拼命,硬是夺回了儿子。那个儿子就是我。我十四岁因“文革”回家种田,父亲抱怨母亲,“你好没见识,若是老六成了大城市人,肯定考上大学做官了。”母亲说,“老六,你要发狠,我等着你……”我爱上小说后,便不要命地写,六月天把双腿泡在水桶里躲蚊子。我深知我和母亲都在等待。等待那种生活中的不可能与小说的可能。等待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月。有时,我也不免循着父亲的思路推演,我若真的成了那个富人的儿子,大学是要考上的,然后呢?――有可能做官当寄生虫;但也有可能插队西双版纳,成为叶辛的素材,欠下某个傣族姑娘的孽债,溜回城里来混个人不人鬼不鬼。命运不可知,惟有小说可能。所以,尤利西斯把小说比作魔方。可能是粘着香饵的鱼钩,有时可能钓上一条大鱼,有时可能钓上密封的魔瓶。
《苦菜花》里有个英雄母亲。假得肉麻。我的母亲倒是个真英雄。叔叔参加地方游击队,常把日本哨兵捅死。日本人几番上我家捉拿。叔叔早就跑了。日本人就在堂屋里堆起晒垫、斗笠、干柴,预备点火烧房子。日本兵一擦燃洋火,母亲就冲上前将洋火捻熄,连续三次。日本兵推了母亲一掌,再次擦燃洋火,还用刺刀挡住。母亲歇斯底里冲上去,又一次捻灭了洋火。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似乎奈何不了一个手无寸铁却不顾生死的农妇,居然放弃了烧屋,悻悻地走了。我看多了写日本鬼子的小说、电影,觉得母亲捻洋火的细节难以置信。母亲却说是真的。村里所有老人都出面证明属实。我对母亲有了敬畏。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母亲也仍然在等待。等待和平与安宁。我进一步思考,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两个秀才舅舅被杀就是明证。而母亲那次,确实震慑住了杀人魔王。那座房子得以活到1958年大跃进,应当与那个日本小队长的禀性善良有关。日本人是很看重勤劳创业的,一个中国农妇如此豁出去保护自己的家产,无疑他被感动了。他不忍下手。就此写成小说,离人性的真实可能挨得更近。那个小队长是文学中的“这一个”。作为小说,有可能。
还有,我那个引来日本人烧房子的叔叔,捅死了七八个日本兵,我曾经对此表示怀疑。他说,“是真的。有一次遇上个大块头高个哨兵,一下把我扑倒在身下,掐住了我的喉咙。我憋着气,悄悄掏出匕首,从下往上戳进他小腹。他的手松了,一泡尿射在我身上。”这个细节证实他没有撒谎。我特别注重细节。细节不能虚构,只能发现。后来,叔叔被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带去了南京,当上了文书,多次与日军血战。但是,他没有跟那个团长去台湾。这恐怕不完全是故土难舍,极有可能与他娶了金陵大学一个漂亮女生有关。岳丈是个资本家,不让独生女儿远离。叔叔舍弃不了爱情,就领着她回了故乡。照理,一个抗日英雄,从没和共产党军队打过仗,应当受到整个民族的尊重。然而,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加右派分子的帽子却戴了三十多年。生活的可能如此,小说不可能。突然,“海外关系”成了香饽饽,某市有个中学穷教书匠,一弄清其父是国民党军队驻金门马祖前线总司令,一个早晨当上了副市长。现实中的可能,反过来开了小说一个玩笑,让小说感受到了简单与游离的悲哀。
小说为何遭遇如此尴尬呢?仍然只有马尔克斯有资格回答。他活到37岁就写出了百年孤独,是在流亡结束后得到的诺奖。可能的代价是如此高昂。沈从文写出《边城》后,躲进了故宫,回避了小说的可能。而精神放逐的最终归属只能是“能理解我”。面对可能身后的追杀,少有写作者不望而却步。
母亲以偷窃遭祸。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农民生活之苦,难以想像。要把7个子女养活,除了偷窃,别无选择。她颤着三寸金莲出工,锄地,修京广复线,修水库,晚上回家总要拖回一大捆柴禾,悄悄解开。里面藏些红薯、豌豆之类。村支书和生产队长则是明偷,他们把持保管室仓库钥匙,可以深更半夜进去背回几袋谷子或挑回几担红薯。母亲跪在地上挨斗,说,“支书队长可以明偷暗抢,我刨几个红薯养命为什么不行?”队长抽了母亲一巴掌。母亲摇摇晃晃站起来,也伸手抽了队长一巴掌。母亲被送进磨子山劳教所。她在里面等待了半年。我和13岁的哥哥去探监,在岳阳的南郊找了整整一天。母亲说,“等一阵,我就出来了。等你们大了,就好了。”母亲说话总是少不了“等待”二字。她的等待可能吗?
那阵,村里常饿死人,有个叫翁××的老汉死时趴在公共食堂发了霉的空饭甑上,人们怎么用力都没法把他扳下来,只能找来剪刀撬开,指头都撬烂了。翁××恰恰是那个抽我母亲一巴掌的队长的父亲。队长老婆姿色出众,夜里社教工作队长一进门,他就主动让床,这才弄到保管室钥匙,得以明偷暗抢,却又忍心父亲活活饿死。极权、自私、无耻、伪善、残忍,是生活的可能,是小说的不可能。至少中国的小说落后现实一个世纪。可能变成不可能,是对小说的反讽。

我研究过有关马尔克斯的资料,他在写作中放弃政治的主题,并非心甘情愿;他选择文本和叙述方式的创新,绝非初衷。应当说,他的成功很伟大,至少引来中国无数小说写作者模仿复制,但用“歪打正着”概括,也不能算以蠡测海。两个写作者拥有同等天赋,成功可能偏重勇气与坚毅。
我十五六岁开始小说习作。有人笑我,“打草鞋,卖草鞋。今天去,明天来。”意思是稿子上个月投出去,下个月退了回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在等待。母亲说,“终归有一天会结果的。”母亲对生活的向往与执著,赋予了我坚毅的遗传基因,而旷日持久的等待,则让我陷入孤独。小说更多的时候是一次又一次失恋后的自慰。母亲是个不自觉的理想主义者,荒谬是她的可能的酵母。
母亲有个亲密邻居,人们叫她陈��。她有6个儿子,全是文盲。某一天,他们在一块水田来禾。区长来到田边叫,“翁老四,你上来!”老四就上来了。区长说,“把脚洗干净。”老四就去溪里洗净腿肚上的泥巴。区长说,“6兄弟,唯你没有成家。跟我走吧。”老四就跟着去了区公所,吃了一餐饱饭,换了一身衣服,当晚就上了火车,第三天深夜到了丹东,火车停靠二十分钟,给发了一杆三八大盖。接着拉去了朝鲜。三年过去,志愿军陆陆续续回来了。老四没有回来。陈��就天天坐在村口等待,母亲也陪着她等待,从50岁等到70岁咽气,陈��也没有等来她的老四。母亲给她的朋友送终,朋友托付她,“帮我等我的老四啊。等到了,就让他在我坟头放一挂鞭……”“文革”中,那个很老了的区长剃了阴阳头游街。我14岁,上前问了他关于老四的消息。他说,“被临时叫上火车拉过鸭绿江的人死得太多,美国人机枪一扫,人像倒麻将牌,连名字都来不及造上册子,除了毛岸英烈士,我一概记不得了。”我朝他丑陋的脸孔狠狠扇了一巴掌,说,“为了陈��的等待……”母亲78岁那年还给我说起这件事,问我老四是否还有活着的可能。1992年冬,我去朝鲜旅游,看了那个主体思想塔,特意拜谒了志愿军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有许多名字,我找了足足两个小时,没看到翁老四的名字。回家告诉母亲,“您朋友托付的事,您可能完不成了。”
母亲是个愚氓,但又是个朴素的哲人。她充分相信活着的可能。史铁生20世纪末的迷惘,她在20世纪初就有了明晰的答案。她晚年跟我住了21年,常积攒一点零花钱,偷偷送给某个日子略逊我家的儿子、孙子、外孙。而且家里的一些衣物也不知不觉出现在其他兄妹家里。她的平均主义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宏观调控手段,与国务院总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她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兄妹、孙子、外孙找到饭碗的消息。等待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然谈不上什么精神坐标和和价值向度之类。但这并不妨碍它是另一种意义的崇高。即便它没有形迹。可能还是存在。
我曾经和几个北京朋友一起去看贝克特的话剧《等待戈多》。“二战”结束时世界的饥馑和心灵的荒疏让人惆怅绝望。世界的那一极,人们在等待虚拟的戈多;世界的这一极,人们一边高唱没有神仙皇帝的国际歌,一边在倾力打造神仙戈多。结果,那一极似乎有了等待的结果;而这一极,却碰上了西西弗斯的巨石,把希望一次又一次砸得头破血流。这让我想到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
由母亲想到戈多,由戈多到加缪,再到西西弗斯,我既感到了等待的可能,也感到了等待的不可能;既感到了小说的可能,又感到了小说的不可能。在没有过文艺复兴洗礼的国度,小说有太多的不可能,不得不接受放疗化疗。那种可恶细胞固然杀灭了一小部分,但大伤了元气。惟剩一具缺铁性贫血的干瘦躯体躲在被窝里自慰,因短暂的快感大声哼哼。这种来自象牙塔中自慰的快感和哼哼,用刘再复的话说(见刘再复博客),伪文本主义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刘氏的批评可能吗?
当人们深感等待戈多是如此艰难时,我们无法不为某种失落感到惆怅;人们等待的,寻找的不是五谷杂粮,不是金钱财帛,而是一种精神的错位,基本价值的缺失。但是,我们如果只认识到了《等待戈多》中的绝望和虚无情感――这是我们一贯的认识,我们就会忽略等待戈多的潜在情感,那是一种“上帝信仰”的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与“信仰――拯救”的文化模式有关。因为在这种信仰模式中,人生同样有可能被视为等待的过程。小说可能吗?
母亲有着类似西西弗斯的执拗。复杂性在于,母亲的等待一方面暗示了希望的虚无,另一方面又翘首期盼希望哪怕是姗姗来迟的脚步。因此21世纪的小说身处中国社会转型期变迁史中的一个特殊点上,在这一点上,日暮苍茫,“虚无”和“信仰”执手相看,无语凝咽。人对生存在其中的世界,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然而,无论“戈多”将会是谁,理应从我们的小说中看出,他的到来,将会给等待中人带来希望的可能,带来小说的可能。母亲是不幸的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呼唤和向往。是当今社会人们对明天某种指望的代表,象征着“希望”、“憧憬”。肃立沈从文墓石前,我觉得我理解了他――无论社会呈现的状态怎样强大,实施惩罚的只能是人自己;人有自己选择生存态度的权利。
2007年12月10日 匆草于岳阳南湖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