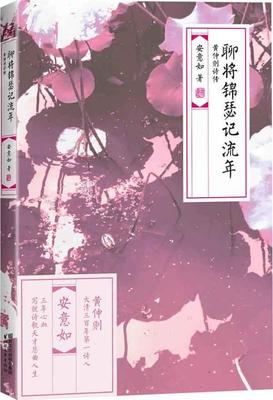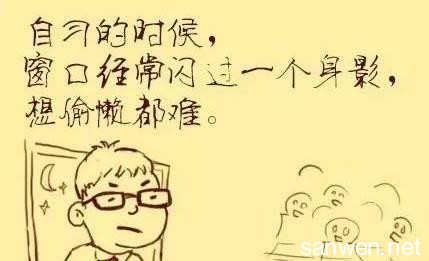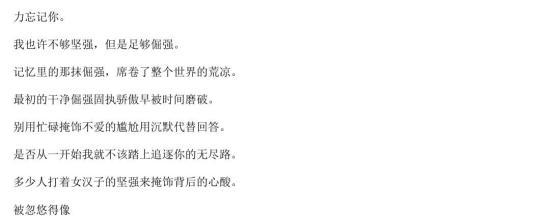前两天验尿验出中队长,我慌忙给我的老闺蜜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好像有了,她声音马上压得比我还低,神秘兮兮的问,谁的?
我说,当然是我老公的,她听后一秒恢复正常,你老公不是出国了么?我说你好歹也是医生,他走了才一星期好吗?紧接着就是电话那头肆无忌惮的浪荡笑声,她说,你也太响应国家号召了,政府放个屁你就累断气啊。
我挂断电话,不知道这个50年代出生的老家伙为何总讲些让我们这些开放的90后都接不了的话。用现在流行的词来说,她就是个超级无敌大逗比。
她幼年丧父,儿子身体不好,好在老公长得极帅女儿又聪明伶俐,自己又凭借狗屎运每步都赶对了点儿,莫名其妙成了大学生,鬼使神差被名家收为弟子,成功的从主任医师岗位安全退休,现在每日与一帮老干部专修国粹麻将,每次赢了钱就笑的花枝乱颤,跟我比智商,老娘好歹是跟死神较过劲儿的人!
2004年的时候,她脑干处梗死,抢救了数十天,病危通知不知道下了多少次,当时医生对家属说,你们准备一个轮椅吧,下半辈子最好的情况也就植物人了。
现在,她的病例被那所医院当成教学案例,每天在微信运动里刷的步数不知道甩我几条街。
她老公总情绪激昂的为自己当初的英明抉择点赞,她昏迷时我让医生全上进口药,加我四个特护24小时按摩,防止肌肉萎缩,每每这时,她就会甩出一个很强的爆破音作为回应,“屁!肯定是老娘我福大命大,前半辈子积了德。”
早些年,她家客厅的沙发上、地上,总住着农村来城务工和看病的各类亲戚和乡党,以至于每次一大早我离开她家时都感觉在玩跳方块。
她生病时,她老公正经八百的想把来探望过她的人一一记下,好日后还礼,后来很快就放弃了,每天病房里三教九流人的涌一屋子,有开出租的,蹬三轮的,卖羊杂的,做豆腐脑的,嗯嗯啊啊、乱七八糟一通客气送人出门之后,她老公摊开小本问,刚来的都什么人啊,她说,我哪儿知道。
有一次病房里冲进来一个老大爷,泪眼婆娑的拉住她的手,知道你病了我一夜都没睡好,今天一大早就来看你。她抬头就问人家,你是谁啊?那人说,我就那谁谁谁,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给我看过什么病还没收我钱,她恍然大悟状,噢,我想起来了,你还活着呢?
大概半年的时间,她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解决,我陪了她一段日子后,要回学校做毕业答辩,走的那天她看起来有些落寞,我说你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你办的吗?她说,有,能不能在我的床头挂满烧鸡、蛋糕和果丹皮。
再见面时,她给我讲她初恋情人来看她的事儿,脸上写满遗憾,她说:我当时刚在床上拉了屎,但自己又不知道,屎都蹭到袖子上了,我还在津津有味的吃着西红柿,她说这句时的语气,让我笑的屎都快出来了。她出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尿失禁,有一次我们逛商场,她忽然说,快跑,我把鄂尔多斯家尿了,她边跑边乐的前仰后合,我说大姐,这你也能笑的出来,她说不然呢?又不能去死。
我说你能长点心吗?难道最让你发愁的事儿就是你的发型和体重,即使裤子经常尿湿的时候,她也在不停的折腾她的那点头发,烫了染,染了烫,要不然就是发誓吃饱了这顿后一定开始减肥。
虽然我一直保持着嫌弃她的姿态,可我发现她严重的影响了我的择友观,身边像她一样的逗比朋友也越来越多,要么是喜欢自黑自嘲,能让我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人,要么是率真有趣拥有古道热肠赤子之心的人,要么被生活玩弄一心想着再玩回去的人,要么是外表长的丑心里想的美的人,要么是摸着自己的平胸说,我是男人我要坚强的人,反正至少得符合三不原则,不虚伪,不装逼,看起来不像性冷淡。
这样的人干干媒体公关也就好了,能在医生这个行当里混迹多年,我还是有点想不通的。她似乎从没有特认真特正经的说过什么话干过什么事儿,我一直在想,谁能放心委托让她来修理?但直到现在我去她家,依然会碰到有人登门求诊,每次我都怀着悲天悯人之心想对那位病人说声祝你好运。

我觉得唯一能让我意识到她是一名医生的,就是她帮我开病假条让我逃课的时候,以及用各种器官来遣词造句的时候,有一次我认真的问她一件事情的处理意见,她也真诚的对我回答:你这样做就好像把睾丸割下来敬神,人也疼死了,神也觉得骚,两边都不落好!
我经常会想,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不着调的人,只要她一开口说话,就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正经了。
后来我想,她能被病人爱戴和信任无非是因为她喜欢比别的医生多说两句话,一句是,全国像你这样的病人太多了,还有一句是,你这个情况还不是最糟的。
就好像今天我告诉她我胎停育了一样,她手头总攒着一百个比你凄惨的例子讲给你听,让你觉得,自己到现在还没死,也太特么的幸运了。
我耐心的听她从子宫环境讲到胚胎质量再到雾霾气候,巴拉巴拉说了半个小时后,她说,闺女想开点,给一个人当老娘这事儿是要讲缘分的。
挂完电话,我写下这篇文章,想感谢我跟她的缘分,很多年前的今天,是她给了我生命。她是我的老娘,她教会我,要做一个勇敢的逗比,敢于直面像段子一样的日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