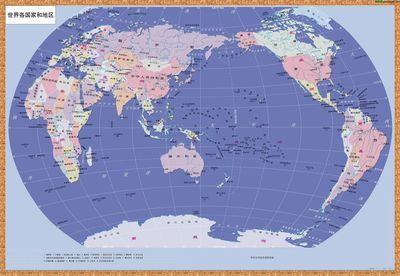刚到京都,入寮的第一天,东西还没有放下,就听见檐下“叮咛、叮咛”的声音,那就是风铃了。
推窗一看,窗檐上悬挂着一只小风铃。
那是一只仿青铜的生铁的“南部风铃”。
谁挂的风铃?管寮的人悬挂的吗?问过管寮的人,说:“不是的,是老寮生挂的。”
老寮生为什么要悬挂风铃呢?
因为风铃的声音很清脆,很悦耳,很动听,听日本人说,风铃可以清凉,可以消暑,可以避邪,其中“铃”字,日语中就是可以避邪的意思。
日本是一个风铃国家,小巧、玲珑、可爱,有舞蹈,有音乐,有情味,是诗意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风铃的声音,在各种电影、电视剧的片段里此起彼伏,和一休小和尚的歌声一样,为中国的孩子们所熟悉。
日本的风铃,五颜六色,质地不同,声音不同,名目繁多。
粗粗地看,有岩手南部的铁风铃、会津喜多方、江户、冲绳的玻璃风铃、爱知濑户陶瓷风铃、大分别府竹器风铃等等。
南部的铁风铃,古朴、厚重,音色美妙,有金属声,有穿透力;会津喜多方和江户的玻璃风铃是用手工做的,画家在玻璃风铃内部描绘各种花卉、动植物和人物画,半透明的风铃便更玲珑剔透;爱知濑户陶瓷风铃用爱知县著名的陶瓷做成,声音朴实、沉着、和顺;大分别府竹器风铃在铁制、陶瓷和玻璃风铃中加入竹编工艺,形成了形态优雅的竹器风铃,令人爱不释手。但最普遍的还是南部的仿青铜铁风铃,就是我窗前的这一只。
后来知道,到超市里买东西,譬如买三得利绿茶,作为添头,可以送你一只铁风铃。老寮生的风铃,也许就是买茶送的吧!
为了迎风,风铃下面,有一条长长的“舌头”,随风摆动,日本人称它为“短册”,那是一个非常雅的名字,一个叫起来,和紫式部《源氏物语》中女孩子一样亲切的名字。
短册上的字,大都是些草书,那是从中国王羲之《十七帖》里拆下边旁成为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后,写上去的;王羲之的草书成为假名以后,被日本人写得更加飘逸,更加潇洒,也更加像风的尾巴,可以舞到天边。
我经常注视风铃,看短册飞舞,企图破译风铃的语言。
但是,风铃的语言,是风的语言;风的语言,是天的语言;天的语言,是籁的语言,籁的语言,还有铃的语言,都是神秘的语言,三个月内,我不能破译。
积雪尚未化尽,春雨的靴子,湿淋淋的,整天在屋檐下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听,以为是下雨,拉开窗帘,一看,是融融的太阳,是融雪,融雪的天气最冷。

这时,檐下的风铃开始响了。
一只风铃响起来,所有的风铃便同时响起来。在大阪湾流水与鸟羽的飞渡中,最响的是京都一千六百多座寺庙的廊檐,随着鸽群毛羽轻轻地回旋,随着庙会风笛的伴奏,吉祥的“叮叮咛咛”的音乐,便清晰地响在寺庙五颜六色的地摊之间,响在我睁开眼睛,初到日本的新鲜感里。
是的,红灯笼属于江南,也属于京都。
杨衔之《洛阳伽蓝记》里的风铃,什么时候到了日本?又从寺庙来到寻常百姓家的,我不清楚。但是,铃在风里响着,日本人都知道,那是唐玄宗从长安逃往四川,又从四川回长安的路上,一路细雨,一路响着的风铃。响在马颈,响在雨里;响在告别的长安城,响在一千多年以前,响在日本人的喜闻乐见里。
洛阳有很多庙宇,所以有很多风铃。
京都有很多庙宇,所以京都也有很多风铃。日本的京都,是保存中国六朝和唐代文物最大,最好的博物馆;许多在中国,在长安,在洛阳已经失传了的东西,你不妨去京都寻觅,譬如风铃。
响在洛阳的寺庙,响在长安鸟声、风声、雨声里的风铃,也响在京都的金阁寺、银阁寺、清水寺、龙安寺、净土寺的飞檐上;悬挂在日本精致的门廊和屋檐底下,这时候,家家户户挂着的风铃一起响起来。
自从我喜欢聆听风铃,不问清晨或黄昏,我都侧耳听,向檐下听,静静地听。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听出不同的声音。京都的风铃声音无疑是最美的:春晨,有黄莺鸣啭;夏日,有蝉声和鸣;秋昏,风铃响的时候,木屐最能衬托出京都秋夜的寂静;冬雪,拥被而睡,高窗风铃,有飘雪喑哑的声音。
当夏日就要到来,京都各种传统节庆像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花,各寺院和商场展示不同的风铃;当东京知名寺院西新井大师一带自七月十日起举行“风铃祭”,京都以传统风铃为主题的“风铃祭”就开始风行了。
风铃的声音,是庙宇的声音,是檐雀的声音,是廊下钟磬的声音,是秋晴中午寂静的声音。
有人进寺庙的门,不管是白天还是月夜,不管是贾岛,还是韩愈,不管是“推”,还是“敲”,只要有人来,寺门还没有响,门上的风铃先响起来。
每一所庙宇里的风铃,都会说“般若”的语言,都能传达神祗的意思。可惜,佛祖不在。
同样是风,佛祖正好坐在那里。
当旗幡飘动的时候,佛祖问众弟子:“眼前,是什么在动?”
众弟子慌忙不迭的回答,是“旗在动”、“风在动”,都是错误的;真正答案,是“心在动。”
所以,当风铃响起来的时候,佛祖也可以问:“现在,是什么在响?”
这时,你千万别回答,是“风在响”,“铃在响”,要回答是“心在响。”
就像现在,檐间,风很大,风铃的短册在上下翻动。但是,响的,不是风,不是铃,而是我的心。
风铃响起来,那是“神祗”要来了;风铃响起来,那是我要走了,我决定回国了。
风铃依旧响着,“叮咛、叮咛、叮咛”。 风铃不知道我要走,并且,不会再来了。
“就让风铃这样一直在檐下寂寞地响着吗?”妻问。
“叮咛、叮咛、叮咛”。
“带一枚风铃回国吧!”妻说:“她挺留恋我们的。”
我说:“好。”便解下风铃,打进背包。
我知道,妻想带回的,不是风,不是铃,而是我们在京都一年半寂寞的生活。
——本文节选自「京都的风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