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与音乐的互映的问题,莫扎特是一个神秘的吊诡:他的音乐从来没有凸显和明确的生平自传性,但我们却总能从中察觉他个人的生命状态和心绪状况;...,但另一方面,即便我们能够在莫扎特的音乐中感受到强烈的个人情感诉求或鲜活的生命流动,它们却又总是带有某种特别的超越性和超然性——所以我们会觉得,莫扎特的音乐具备了远远高于个人的普遍性与共同性。(杨燕迪,引自《人生与音乐的互映》)
然而,音乐史上,至今还有很多人(甚至是主流)认为莫扎特的音乐与莫扎特的人生情境不一,他笔下的音符总是那么典雅,不哀伤而充满愉悦。最近文汇网刊载作者钱好的一篇标题为《莫扎特诞辰260周年:为什么莫扎特“不敢”哀伤》(2016-01-10)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莫扎特音乐不哀伤,进一步解释莫扎特不敢哀伤的理由。
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台湾乐评人杨照的论点:讨论“为什么莫扎特不哀伤”的问题。他认为,莫扎特并非不哀伤,而是“不能”哀伤:“他所处的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本来就不是个人经验与感受的发抒表达。音乐要为王公贵族的不同场合服务,决定音乐属性的,是那些场合需要的气氛,而非作曲家的个人感觉。更重要的,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语汇,根本就没有适合拿来表达深沉哀伤的完整工具。”(引自,《莫扎特诞辰260周年:为什么莫扎特“不敢”哀伤》)
文中还引用了上海音乐学院邹彦教授的观点:他(邹彦)认为,莫扎特在维也纳写的大部分音乐作品都是面向普通市民的。除了为剧院创作大量歌剧以外,他写的所有钢琴协奏曲也都是为自己演出用的,这种“商品属性”决定了他的音乐首先要愉悦大众,不单要具备很强的审美功能,同时还需要有娱乐功能。当时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启蒙主义阶段,人们崇尚理性,不太认同忧伤的审美。观众买票进剧院、音乐会,希望听到的是积极乐观的音乐,这也是莫扎特的曲风轻松愉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有在他晚年的作品里,有些微哀伤的影子,比如《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引自,《莫扎特诞辰260周年:为什么莫扎特“不敢”哀伤》)
就“莫扎特不哀伤”的观点,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指出:“说莫扎特的音乐不表达哀伤和痛苦,这是乐史中最持久的误会之一。我在文章和言谈中多次纠正这一误导,但很难阻止这个误导时常在坊间流传,让人无奈”。并认为“莫氏的所有小调作品或乐章——以及渗透了小调半音化曲折的诸多莫扎特的大调作品及乐章——均证明这篇文章误导的不确和错误”。
杨燕迪教授并进一步举例证实:“莫氏《G小调弦乐五重奏》K. 516是整个18世纪中最痛苦、最极端的音乐表达;他的《D小调钢琴协奏曲》K. 466是19世纪之前最不祥、最紧张的乐声;《唐璜》中终场之前主人翁被拉下地狱的场景则是歌剧史到当时为止最凶暴、最恐怖的时刻……。可以说如此例证不胜枚举'。杨燕迪教授在2013年1月也曾专门撰文《人生与音乐的互映》,从侧面谈及过这一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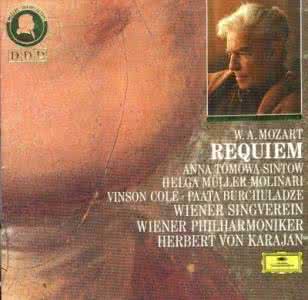
本公益平台原创素材、以及部分来源于期刊和网络已授权的素材,欢迎只为交流和学习的转载,实现原文的文化增值,以达尚音爱乐,人生新境界。对原文作者我们一起深表谢意,如有版权异议,请告知我们!我们当及时处理。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