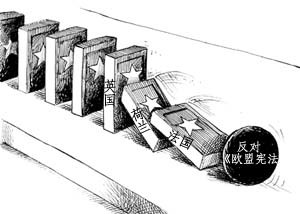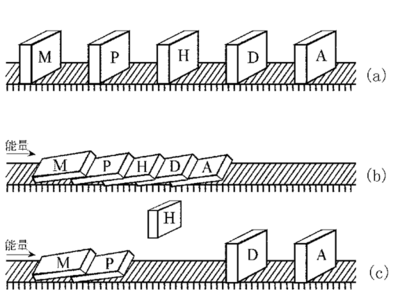彩色版画,描绘公元410年8月,西哥特人在首领阿拉里克一世率领下攻陷罗马,并大举劫掠。远处是古罗马凯旋门,军队攻占之处遍布尸体
文 | 郭晔旻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1月下独家稿件
2015年11月26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语出惊人,如果欧盟不重新对边界加以控制并阻止中东及中亚难民“大规模涌入”,就会有重蹈罗马帝国覆辙的危险,“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的命运,如果不能保护好边界,巨型帝国也会衰亡”。这是极不寻常的表态,难道当下被难民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欧盟真的会面临被“民族大迁徙”所毁灭的西罗马帝国同样的命运么?
“蛮族”遇到了更野蛮的匈奴人
公元374年,居住在今天的乌克兰地区的东哥特人(日耳曼人的一支)“听到说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骤然来临,碰到他们的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在他们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遭到一支来自东方的强大骑兵的侵袭。这些敌人身材短小粗壮,圆脸扁鼻,胡须稀疏,外表上与身材细长、长脸高鼻、胡须稠密的日耳曼人迥然不同。
哥特骑兵身穿铠甲、手执长矛;其长矛是由链条固定在马脖子上的,其击刺力可以加上骑者和长矛的冲击力,本不失为一支劲旅,结果在东方的陌生敌人面前却不堪一击。对手是优秀的骑射手,他们的弓箭比哥特人的长矛射程远得多,“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他们的钢铁般坚硬及能致命的尖锐骨制箭头”。敌人的骑兵队伍来势凶猛,去势如飞,令人莫测;这是日耳曼人闻所未闻的新战术。时已年迈的东哥特国王赫曼立克并非碌碌之辈,年轻时曾被誉为“哥特人中的亚历山大大帝”;但垂暮之年的昔日英雄面对如此强敌却无力回天,悲剧性地自杀身亡。而只过了一年时间,他的王国也毁灭了。
东哥特的毁灭者被当时的西方史学家记录为“匈人(Hun)”。古今中外都有学者考证,匈人即是汉文史籍中“匈奴”的后裔。东汉永元元年(89年),汉军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北匈奴81部20余万人先后归降汉朝,余部在单于率领下离开故土,向远方遁去。沙漠从南方向他们进逼,北方的森林草原地带引诱着他们。那儿有木材,可供取暖。林间空地中游走着野牛、鹿、狍子,这意味着肉食;但匈奴人不可能深入北方太远,马匹吃不习惯西伯利亚森林里潮湿的青草。“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去向只有往西,只有在那里的草原他们才能喂饱自己的战马。至2世纪后半叶,匈奴人经西伯利亚南部草原来到顿河、伏尔加河东岸。在里海北部荒草甸子游荡了两百多年后,跨过伏尔加河,向西推进,经过1.2万公里的长途跋涉后,匈奴人终于来到欧洲的东境。
东哥特灭亡之后,其族人一部分向匈人投降,一部分不愿屈服的人则仓皇向西逃窜投奔西哥特人(居住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将压力和恐惧带给了兄弟民族。自觉大祸临头的西哥特人将全民族的安全寄托在德涅斯特河上,在匈人骑兵来到德涅斯特河东岸之时,在西岸布置防线企图阻止匈人渡河。结果,能征善战的匈奴巧妙地绕道而行,趁着月夜在德涅斯特河上游偷渡成功,奔袭了西哥特人的后路。本已成为惊弓之鸟的西哥特军队,竟不战而溃,连同家属在内数十万人潮水般地向西逃去。
哥特人是匈人西侵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在其身后,还有法兰克、汪达尔、盎格鲁-撒克逊等日耳曼人部落。这些罗马人眼中的蛮族,彪悍尚武,信奉“能流血而获得的东西却去流汗,是一种耻辱”,“向邻人掠夺财富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战争成为民族生活正常职业”的野蛮人,眼下却遇到比自己更为野蛮的匈人,受到可怕的冲击,纷纷丧魂落魄,四处奔逃,后浪推前浪般向着西方涌去,“企图逃到这些野蛮人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安家”。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迁徙。“整个、整个的部落,至少是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都带着妻儿子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妇女、儿童和少量家具、家畜也赶着一起走。男子都武装起来,编制起来,准备摧毁一切抵抗和防备袭击”……受到匈人驱赶的“蛮族”最后走投无路,被“挤进”了多瑙河与莱茵河彼岸的罗马帝国,西方历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罗马帝国的不速之客
公元4-5 世纪,罗马帝国军队的日耳曼士兵:1、3 :君士坦丁大帝建立的日耳曼精英军团——皇家辅助军的士兵;2、罗马帝国皇帝的日耳曼亲卫,身着宫廷军服(选自世界军事史丛书第129 册《罗马军队1 :日耳曼与达瑟亚》)
在公元376年抵达多瑙河畔的西哥特人,为了想要逃避匈人的凶焰,都想渡过河去,其合于战斗年龄的人,总数竟不下20万人。他们站在河岸上,仰天高呼,伸手求援,诚恳地请求允许他们渡河,以躲避浩劫。他们相信,只有波涛汹涌的多瑙河水和强大的罗马帝国,才能挡住匈人的进攻,使自己获得安全。他们向罗马帝国提出入境申请,为了报答这一恩典,他们愿意永远效忠罗马帝国。
哥特人请求入境避难的消息立刻使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Valens)萌生了借用哥特人组建军队的想法。原因并不难理解:耽于安乐的罗马人已经越来越不愿意从军入伍,富人固然穷奢极欲,穷人也乐于享受帝国政府免费提供的“面包与马戏”。服兵役由罗马公民一种爱国职责变成了要尽力逃避的苦役:一些有钱人不再愿意到军队服役,“另外一些服役者则四处逃散,在被抓住后像奴隶一样打上烙印”,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常备军中的意大利公民逐渐减少,“从奥古斯都(屋大维)时代的65%”,到了212年已经“下降到不足10%”。既然蛮族大多好战,那么“让他们保卫帝国远比入侵帝国好得多”。这也算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手段。早在公元4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的大潮涌来之前,已经“有几万,也许有几十万日耳曼人进入了罗马帝国”,“以‘同盟者’的名义居住于边境各省内”,以服军役为条件领取耕地,或以隶农身份“移殖在人烟稀少或荒芜的地区”。
公元3世纪,罗马卢多维西的石棺上雕刻有西哥特人与罗马人战斗的场面
不过,让大量的蛮族涌进帝国毕竟有一定危险,瓦伦斯下了一道还算谨慎的命令:允许哥特人入境,以同盟者的身份居住在色雷斯地区;但哥特人必须交出所有贵族少年作为人质,并且在渡河前缴纳所有武器。走投无路的哥特人满口答应了这些条件,反正罗马的边防军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只需稍加贿赂,哥特人就可以保留自己的武器。多瑙河上的大门就这样对不速之客敞开了。
罗马帝国的繁荣和富庶是哥特人向往已久的,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来到色雷斯,可却事与愿违。贪婪的罗马地方官员逼得哥特人忍无可忍,“他们抬高卖给哥特人的粮食价格,一条面包要付出一个奴隶的代价,迫于饥饿,哥特人不得不卖儿鬻女;因为高昂的物价,为维持生计,哥特人只能食用狗肉以及其他因病死亡的动物的肉”。最终,西哥特人选择了反抗,宁可自由地在战斗中战死,不愿意在饥馑中饿死。“从这一天起,哥特人的饥饿与罗马人的安全同时宣告结束,哥特人已经不再是流浪无依的难民,而是占领了所有北方地区,自立为王了。”
在匈奴骑兵面前只是一群丧魂落魄的逃难者的西哥特人,在腐朽的罗马帝国面前却变成了骁勇善战的征服者。公元378年8月9日,哥特人与瓦伦斯皇帝亲自率领的6万罗马大军在亚德里安堡(今属土耳其欧洲部分)决战。哥特军队手中的武器丝毫不逊于对手,包括手盾、长矛、匕首和长剑,有些士兵还使用一种锋利的战斧,可以舞动也可以投掷,能够砍穿罗马人的甲胄和防盾。更重要的是,哥特人中还出现了一种(可能是从匈人那里学来的)新战术——车城,即把大车围成一个要塞,步兵和弓箭手躲在这个车城里,向外投掷箭矢和石块。
中午时分,突然从侧翼出击的西哥特骑兵“像闪电似的从陡峭的山上闪出,疾驰向前,神速进攻,把自己路上的一切扫光”。这是致命的打击,罗马的骑兵不是西哥特人的对手,很快就只剩下罗马的步兵方阵在战场独立支撑。但是,西哥特的骑兵像闪电一样快,令罗马的步兵措手不及,乱成一团。正在这时,地面上掀起了尘雾,几乎无法看到天空,到处只听得到可怕的喊杀声,投枪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掷过来,士兵们应声倒下。这时西哥特人又从车城中放出了他们的步兵,于是人马践踏,罗马士兵互相挤压在一起,无法后退,也无法突围,会战就此变成了屠杀,罗马军队遭到坎尼会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大约有4万将士阵亡,几乎占了全军人数的2/3,皇帝及麾下35名高级官员都死于疆场。
几百年来,罗马军团严格训练的重装步兵,其训练水平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敌手,一直在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PQR,罗马的正式名称)赢得胜利并保卫它们。甚至“蛮族”的新兵加入罗马军队时,依然主要是步兵。在此之前,步兵通常总是决定性的兵种,只要能够保持完整的秩序,就不必害怕骑兵的冲击。但随着投射兵器的增多,重装步兵无法一边躲避密集的弓箭和标枪,一边有秩序地移动队列,战场的主动权遂转移到了骑兵手中。哥特人在阿德里亚堡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罗马军团和方阵的彻底失败,重装步兵占据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场灾难性的失败是对罗马帝国的釜底抽薪,“罗马帝国走向伟大,并非依靠哲学和科学,而是通过政治智慧和战争,战争是首要因素”。在帝国的实力结构中,军队实力是首要因素。眼下,在蛮族铁骑所造成的尘雾中,罗马帝国的权力和光荣都似乎已经显得黯然失色,这个军事帝国的基础已经动摇。既然罗马军队无力保卫自己的边境,帝国只能在苟延残喘中等待死神的到来了。
永恒之城的陷落
公元382年,瓦伦斯的后继者狄奥多西大帝(the great Theodosius)在看尽了罗马与蛮族战争的苦果后,决定承认现实,采取怀柔政策,与哥特人签订了新的永久和平条约,将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地区赐予哥特人居住生活,并且不受罗马法的限制,用哥特人的习惯法管理自己的地区,并赠送了大量的金币和牲畜。唯一的条件就是哥特人为罗马帝国提供兵源,这时的帝国军队也到了不得不依靠蛮族人来注入尚武的新鲜血液的地步。这种方法固然增强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却也导致了罗马军队的彻底蛮族化。“罗马军队变成了蛮族军队,日耳曼军官成了最有才能的罗马军官”,这为一个世纪后所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西罗马军队司令官斯提里科的雕像
最后一位被称为“大帝”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395年去世之后,东西罗马皇位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统治。他的小儿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继承了西罗马帝国。“霍诺里乌斯貌似脾气性情温和忍让,不过他和他的兄长一样是无能之辈,常认为自己的能力经天纬地,实则固执愚蠢。”新皇帝不自量力地撕毁了与西哥特人签订的和约,帝国的反复无常彻底激怒了蛮族——他们原本只希望分享罗马人的光荣,最后却用憎恶罗马人来回报罗马人的轻视,决心取而代之。
公元400年秋,匈人的游骑已经出现在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Alaric)深知自己不是匈人的对手,第二年西哥特人就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罗马当局一日数惊,帝国首都名义上是在罗马,实际上一会儿在米兰,一会儿在拉文那,偌大帝国竟已没有一个安全之地作为京城了。为了保卫意大利,西罗马军队司令官、汪达尔(日耳曼人一支)裔的斯提里科(Sitilicho)不得不火急调回边境驻军。莱茵河上的堡垒被放弃了,甚至守卫不列颠岛上 “哈德良长城”的军团也被召回,而失去驻军的“罗马帝国的各行省应设法自卫”。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空城计岂能御敌?紧随罗马军队的撤离接踵而至的就是蛮族的涌入。“常常是一支日耳曼部落刚刚在帝国的某个地区定居下来,别的日耳曼部落就接踵而至。” 莱茵河,这道过去几百年中曾经存在于蛮族世界和罗马世界之间的藩篱完全倒塌了;不设防的高卢,这个富庶的罗马帝国行省匍匐在野蛮人的脚下。进入西罗马的日耳曼人总数并不多,一般认为只占当地居民的5%左右,却如入无人之境。汪达尔人从莱茵河到达比利牛斯山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而且没有同罗马军人发生过任何战斗。
尽管它的海外行省快丢光了,缩回到了意大利的西罗马帝国还在垂死挣扎。在波伦提亚和维罗纳,罗马军队的蛮族司令官斯提里科两次击败了西哥特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后者被迫退出了意大利。但胜利的喜剧竟一变为内讧的悲剧,408年,昏庸的皇帝以与蛮族勾结的罪名杀害斯提里科,“这个人在当时的许多统治者当中,也许是最善良的一个。”他的死导致罗马军中的3万蛮族将士投奔阿拉里克,这样西哥特人就再也不受阻挡了,阿拉里克的军队封锁台伯河,切断了非洲粮食的供应。没有流血,没有交战,阿拉里克仅使用饥饿,即获得了胜利,迫使“罗马城交出5000磅黄金、3 万磅白银,4000匹丝绸、3000卷牛皮、4000磅胡椒和释放蛮族出身的奴隶为代价换取罗马人的自由。”罗马元老院用贿赂的方式,总算侥幸保住了罗马城。
又经历了两次围城的挣扎之后,罗马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日。公元 410年8月4日,不可否认是西方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在这一天,永恒之城陷落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为之震惊。自罗马城建城以来,这是第一次被蛮族彻底攻占、大肆劫掠,“这座曾经制服世界的城市,如今也轮到它倒塌了”。西哥特人大掠三天离城而去,留下一片废墟,城中到处充斥着火光、哭喊声、疟疾和成堆的尸体。不过,阿拉里克尽管可怕,毕竟还是一个基督教徒和一支有纪律的军队首领,“命令战士不得侵犯教会的财产……更不能在教堂中杀人,所以很多人到教堂寻求庇护。罗马城内的圣彼得教堂和圣保罗教堂因此在这次灾难中并没有受到很大的侵扰。”
1894年,德国画家路德维希·蒂尔施作,描绘公元4世纪西哥特王阿拉里克一世(中坐者)进入希腊后,在雅典的生活
过去,蛮族只是进行漫无边际的掳掠,而现在,“罗马政府在敌人眼中一天比一天软弱”,羽翼丰满的蛮族敢于以征服者的姿态,在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建号称王了。418年,阿拉里克的孙子提奥多里克一世以图鲁兹为首府在“高卢最富庶的一块土地”建立了名义上臣服罗马帝国的西哥特王国,这也是帝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日耳曼人王国。其余的蛮族纷纷效仿,法兰克人于420年渡过莱茵河侵入高卢东北部;勃艮第人则占据了高卢东南隅,于457年以今里昂为首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样,到5世纪中叶,过去统一的高卢行省已四分五裂。439年,汪达尔人渡海远征北非,结束了西罗马帝国对最后一块完整的行省——非洲行省——长达500年的统治,包括西部罗马世界的第二大城市,古都迦太基也落到他们手里……公元444年,狄奥多西的孙子皇帝瓦伦蒂尼安三世,哀叹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已经破产:“纳税人已被榨干,我们现在无法满足现役军人和老兵的需要,甚至最基本的食物和服装也无法提供……”
最后的罗马人
当蛮族在罗马帝国内攻城略地之时,匈人则在这些蛮族空出来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虽然距离他们首次在欧洲出现已经过去两代人,匈人带来的恐怖仍然继续使欧洲人感到战栗。人称“上帝之鞭”的匈人国王阿提拉两次横扫东罗马帝国,连克70余城,除洗劫所到之处外,还强迫东罗马帝国签订了两个缴纳大量贡金、割让多瑙河以东的大片领土的条约。紧接着,阿提拉转而觊觎西罗马帝国,其借口十分滑稽。瓦伦蒂尼安三世的妹妹向阿提拉发出吁请,请他把她从与她不爱的男人的婚事中解脱出来。阿提拉把这一请求看成是这位御妹要嫁给他的表白,提出西罗马帝国拿出半个帝国作为这位御妹的嫁妆。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敲诈,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公元450年,阿提拉竟以此为由进兵高卢,“他的降临是为震撼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践踏世界上所有的土地”。翌年4月7日,阿提拉的大军攻占并焚毁了被恺撒称为“高卢地区最古老、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的梅兹,整个西欧都笼罩在极度恐怖的空气之中。
紧要关头,儿时作为人质在匈人国家内与阿提拉相识的西罗马军事首领,人称“最后一个罗马人”的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临危受命,成为“当时整个西部帝国的依赖”。此时的西罗马帝国,由于“帝国经济的衰退只允许维持一支较小的军队”,不得不依靠高卢地区及周边的诸多蛮族来补充兵员上的不足。因此,埃提乌斯不仅集结罗马军队星夜赶赴高卢前线,还竭尽所能联络西哥特人及周边诸多蛮族加入到罗马一方,共同抵御阿提拉大军。
描绘公元451年6月,匈人大军与罗马- 西哥特联军在特罗耶与沙龙两城之间的加泰罗尼亚原野展开决战的场面
451年6月20日,匈人大军与罗马-西哥特联军在特罗耶与沙隆两城之间的加泰罗尼亚原野展开决战。“那片只有1500步距离的土地,成为无数种族汇集的舞台;两股主导力量勇敢地投入战斗。”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投入的兵力据说超过100万人。“它不仅是一场著名的战役,而且是一场复杂和混乱的战役。”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在激励军队时,被自己的战马抛出”,不幸被乱军踩踏而死。他的战死激起了西哥特人的复仇怒火和决一死战的决心,西哥特军像杀红了眼一般拼命战斗,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战至傍晚时刻,匈人渐渐招架不住,处境不妙的阿提拉用匈人的大篷车组成车阵,弓箭手密布其间;用木制马鞍堆起一座小山;将他所有的金银珠宝和妃嫔置于其上;阿提拉自己端坐在中间,打算一旦罗马-西哥特军队攻破他的营垒,就引火自焚,免当阶下之囚。
好在埃提乌斯担心,“如果匈人被哥特人彻底消灭了,那么罗马帝国也将被(哥特人)淹没”,遂停止了追击,使阿提拉得以安全撤退。此时,可能已有多达16万人在战斗中丧生。沙隆之战也是阿提拉这条“上帝之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重大挫折,朝着到匈牙利平原退却时的阿提拉仍发出威胁:“我还要回来的。”
第二年,匈人取道阿尔卑斯山卷土重来,但意大利蔓延的瘟疫止住了他们的脚步。随着阿提拉在新婚之夜离奇暴死(453年),诸子都不具备他那样的权威和能力,导致匈人帝国迅速分崩离析,从此一蹶不振。结果,刚从阿提拉的阴霾中摆脱的西罗马帝国又生内乱,同样从外敌手中拯救罗马的埃提乌斯与斯提里科殊途同归,横死于宫廷阴谋之下。瓦伦蒂尼安三世身旁的一个近臣得知埃提乌斯的死讯后直率地对他说:“我不知道陛下的意图何在,陛下这样做无异是一个人用其左手把自己的右手砍掉。”“最后一个罗马人”的逝去使西罗马帝国失去了最末一员良将,从此再也没有人有能力来收拾残局了。

1890年,法国画家西尔韦斯特作,描绘公元410年8月罗马被西哥特人攻占,蛮族士兵将绳索套上城内的雕塑
帝国已经不可救药, “罗马人衰弱到这种程度,以致最小的一个民族都能加害于他们”。455年,汪达尔人从迦太基起兵,又一次攻陷罗马。这一次的破坏甚至远远超过当年阿拉里克所为。汪达尔人在罗马城大掠14日,宫殿、庙宇和公共建筑物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抢走了,就连利奥一世教皇也被迫亲自动手,将基督教堂里的贵重金属器皿搜刮殆尽,以满足胜利者的贪欲。无数艺术珍品就此毁于兵燹,以至有近代史学中毁灭文化的“汪达尔主义”之说,而在鼎盛时曾拥有百万人口的罗马城在汪达尔人离开后竟只剩下7000人!
终于走到穷途末路的西罗马帝国,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荡然无存,“帝国是蛮族的天下,军队是蛮族为主体的军队,皇帝被日耳曼雇佣军玩弄于股掌之间”。从455年到476年,9个皇帝先后登基,这些皇帝大多有名无实,“没有做出任何值得记述的事”,其中倒有6个死于非命。最后,日耳曼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在索要意大利1/3的土地未果的情况下,废黜了最后一个傀儡并决定不再拥立新的皇帝。仿佛是宿命一般,这位末代皇帝姓奥古斯都,名罗慕路斯。罗马城始于“罗慕路斯”,帝国兴于“奥古都斯(屋大维)”,这一切在辉煌之后却都终结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手中!
不过,在(西)罗马帝国一连串走向毁灭的历程中,被视为古典时期与中世纪交界的公元476年可能仅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尚不是决定性的终结。毕竟,几百年来,地中海世界已经习惯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哪怕西部的皇帝已不复存在,奥多亚克和此后取代奥多亚克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政权依然认为自己从属于君士坦丁堡的东部皇帝,仍在以罗马帝国皇帝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统治。甚至晚至508年东哥特人占据了高卢南部之后,还认为这并不是“东哥特王国”的扩张,而是罗马帝国西部的复兴。东哥特国王狄奥德里克(Theoderic)告诉“所有高卢行省的居民们”:在经过许多年之后,罗马传统终于在高卢地区复兴了。
尽管如此,公元476年拉文那的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被废黜的事件仍旧意味着甚至罗马城本身都变成了另一个日耳曼王国。无论如何,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或者变成某种别的什么;经历了“民族大迁徙”之后的欧洲物是人非,“蛮族”已经成为罗马帝国领土上的新主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