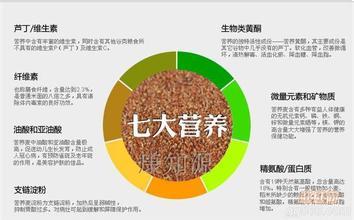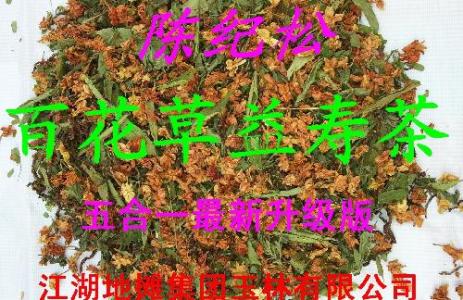如同最初“唐物”的价值地位远高于“和物”,在“侘び茶”创立以前,吃茶的茶会多是供贵族、武士阶层炫耀茶道具、游艺玩乐的奢华“书院茶”。
虽然村田珠光的“草庵茶”已经大大消除“书院茶”中的娱乐性,但直到千利休“侘び茶”精神与茶室茶道具等器物相连,才使之拥有完全胜过“书院茶”的物质力量。
虽然对《南方录》是否为千利休的思想产物,当代日本茶道学家持有不同观点,但不妨借此书探究千利休“侘び茶”中的“物和”。
1茶室与茶庭1.1茶庭
此前,村田珠光“草庵茶”庭已初现轮廓,千利休丰富了茶庭的内容以使更符合“侘び茶”观,如在茶庭中增加通向茶室的“露地”、用来洗手的“手水钵”、踏石(“飞石”)、齐腰高的墙垣(“待台”)、装饰用的便所(“饰雪隐”)等,使之呈现“闹市山居”的幽静美感。
“露地”:露地的由来,传说是千利休所记的《露地清茶规约》中的“露地的树石皆天然之趣,由此悟不明其中之意之辈,莫不如归去”,是“侘び茶”的专用“通路”。
露地分为内外露地,是营造出“市中山野”氛围的重要部分。比如一进入外露地,就是刚洒过水的石板路,让人感觉仿佛是山中露水。在内露地,铺有踏石的小路迂回变化。在小路两侧的四季常绿树,配合透过人工修剪得错落有序的枝叶洒落下来的阳光,还有故意散落在小径上的落叶,让人们感觉这是与尘世不同的深山幽谷(潘洁敏2009)。
“手水钵”:这是放洗手用水的钵或容器。起源于佛教,是参拜神佛必须洗手净身的悠久习惯。尤其是寺庙或禅院都会建有这种洗涤设备,以供访客使用。
但是应用于茶道世界,则始于千利休所设的“蹲踞”。“蹲踞”顾名思义,就是使用“手水钵”洗手时,必须蹲下来。即要有谦卑虚心,同时清洁外表与内心。这种“蹲踞”的形式,大体上以石头的材料最为茶人所喜爱。有利用自然的石头,也有人工打造的。在茶道的造园艺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林瑞萱1991)。
“饰雪隐”:在世界众多的文化艺术形式里,从未听说过把厕所当成艺术品供人欣赏的,然而在日本茶道里,厕所就是艺术品。在正规的茶室旁边附设有一个厕所,日文叫“饰雪隐”。建造“饰雪隐”所用石头是从河边运来的,以示清洁。
其内部设有足悬石、前返石、后返石,地面上铺满了白砂粒。主人要精心打扫,客人要装作去厕所的样子进“饰雪隐”,领会主人的匠心和修行态度,并不使用它。
1.2茶室
在茶室的面积上,对村野珠光时代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千利休改为可以只需一张半的微型间,即“小座敷”;并取消专门为贵宾设的“贵入口”,改设必须俯身而进的“躙口”;
在茶室外型上,采取农家古旧时的茅庵式,中间柱子常常是一根老皮粗树,甚至青睐有虫咬痕迹的柱子;茶室内的装饰也以简素为主。
“小座敷”:即草庵式的小茶席、小间茶室。也就是四张半榻榻米以下的茶室。与宽敞的书院刚好相反。小座敷是千利休所创的茶道礼法。这种茶道礼法特别是从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开始,千家的人都很爱用“小座敷”这个称呼。草庵式小茶席的茶道礼法,乍见之下似是容易,但如何以简单的手法,去表达茶会的旨趣才是最困难的。所以千利休认为进行“小茶席”礼法时,在内心之中,必须有“茶道的真”,也就是严肃敬谨的精神。
茶室挂物:最初用于草庵茶室的挂物,是德高望重的人所书写的佛语和祖语等墨迹。“就这样,吃茶时就像有位高僧在眼前,心情也会恭敬起来。”
到了千利休的时候,茶室便没有了悬挂物和席上的装饰品,只挂祖师大德的墨迹,令人品味其语意,没有题字的、纯粹的绘画则被禁止。千利休晚年喜欢挂元代僧人清欲了庵的书法,还有自己的老师古溪和尚的字,表达对佛语、祖语宗教意义上的礼敬。
现在,“侘び茶”在客人入席的时候,都首先要瞻仰壁龛上挂的墨迹,从心灵上和那墨迹形成一体,据说主客都能以此澄清心境。
茶室插花:按照千利休的思想,在低矮狭小的茶室,应当仅有投入一朵或两朵小花的插花,显示出“花就要像在野外”。比如在《利休》电影中展现的,他在花上看到了露珠就不忍把花剪下,一直等到露珠散了后才把花剪下,再给花加上水。千利休坚持露珠就是花的生命标志,拿到茶室的花即使露珠散了,也要让人感到露珠还在的样子。在竹花筒或竹笼里插上两朵野菊花,是非常朴素简洁的,在技巧上也没有什么高难度,更多反映的是对生命的珍视。现在的“侘び茶”茶室中也经常可以看到竹花筒里插着一朵山茶花,或是两朵野菊花。
由以上对茶室、茶庭的叙述可以发现,千利休是在为“侘び茶”创造出一个处于闹市的山间小居。此外,这里也是以“茶禅一味”分析日本茶道的矛盾之处,为什么千利休要煞费苦心地营造“市中山野”,而非采用更加自然的“山野山居”?也可以引申为两个问题,即身为僧侣的千利休为何没有佛家寻常意义上的“修来世”思想;若是碍于巨商身份,千利休也没有如我国历史上的“陶朱公”范蠡一样选择弃官归隐。而茶室、茶庭所隐约展现的、与当今日本文化关联的独特美意识,可以通过千利休的茶道具来深究。
2“侘び茶”的茶道具
为了更好融进“侘び茶”思想,使人在清洗茶道具、制茶点茶中平静身心,千利休弃正值盛行的“唐物”,独辟蹊径探求“和物”以至寻常器物的美。正因如此,在千利休的时代,“和物”终于可以与“唐物”相媲美;之后,“和物”的价值地位甚至超过 “唐物”。
在著名茶道具中,有由千利休选取长次郎烧制的七件乐茶碗精品组成所谓“利休七式”(或称“长次郎七式”),分别是赤乐的“早船”、“检校”、“木守”、“临济”与黑乐的“大黑”、“钵开”、“东阳坊”。今仅存“早船”、“大黑”、“东阳坊”三件[[i]]。赤乐是指茶碗的釉色红中偏黄,黑乐是指釉色黑中泛褐。
2.1千利休与茶道具
“崇尚名贵道具的思想,自日本茶道创立之初直至今日,从未曾稍微减弱过,因此,日本茶道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名贵道具的收藏与传承史。”(赵方任2001)
当时茶会用的“唐物”外形精致、颜色华丽,“草庵茶”创始人村田珠光就已发现“唐物”难以匹配素朴的“草庵茶”,因此提倡“混和汉之境为一体”。
但千利休力排“唐物”、主张多用“和物”,并将“和物”作为茶事主体。他的茶庭、茶道具、茶室摆设处处体现日本特色。因而逐渐改变了人们头脑中以“唐物”为美的固有观念,并确立了“和物”在日本茶道中的正统地位,将茶道进一步“和化”。
这里,千利休对“和式”茶道具的利用和创造,不仅阐释了个人审美观,也是给民众一个开始发现自身特色与美感的契机,带有自信确立与文化启蒙的意味。虽然村田珠光到武野绍鸥已经对过分追求“唐物”的观念提出过一些解决方案,但因未找出替代的茶道具而告失败。与前者不同,在晚年时千利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和物”的设计和制作上。一方面,把茶道具的花碗由原来的天目茶碗改为朝鲜农家的高丽茶碗、井户茶碗等,向着闲寂、朴素发展;另一方面,他通过设计或指导,烧制出乐窑茶碗,其茶碗表面粗糙、形状不均,与茶室风格最为相称。
此外,千利休还亲手制作竹花瓶、竹茶勺。“侘び茶”的茶室狭小,所装饰的花瓶为挂式就能节省空间,但来自中国的花瓶多为瓷制或铜制,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千利休注意到日本有丰富的竹材。他亲手削制竹花瓶,将花瓶后部打上孔后挂在茶室里,也体现了与自然相融的艺术气质(齐海娟2008)。
现在,茶道具还成为代表茶师修为的标准。“中日茶道择器标准的不同,不单纯是一种美意识上的差异,主要还是因为各自追求的目的不同所致。日本茶道对待茶道具,几乎不考虑与茶的颜色般配与否,而是更侧重于考虑茶人修为深浅与茶道具的色调是否般配。”(张建立2004)
由此,综合前文的“人和”可以得出,千利休的“物和”对民众的意义不是旨在确立某种美意识的定义,而是重在放弃把外界价值观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转为积极探索原有的自身优势,并据此勾勒出自然美感。
2.2茶勺“泪”
早先在日本,抹茶因为量少珍贵,因此小罐来盛装,但用中国式大茶勺取用时非常不便。从村田珠光起的茶师们虽然也曾对茶勺改良过,但可能因外形的原因并未普及。千利休经过不断的研究与实践,设计出一系列风格、形态各异且便于使用的茶勺,很快得到了认同,成为日本茶勺的创造者。另外,千利休还创造出竹茶筒来装茶勺,并将茶勺名和自己的名字写在竹茶筒后面,有的甚至还配有说明书。
在千利休制作的众多茶勺中,不得不提到其辞世前亲手制作的茶勺——“泪”[[ii]]。自知死期将至的利休,用两根竹子作了两个茶勺,即“泪”与“命运”,送给弥留时仍守在自己身边的古田织部与细川三斋。
古田织部所得到的就是刻有“泪”的茶勺,他还为“泪”制作了茶勺筒,并在小筒中部开了长方形窗眼,据闻以此替代利休的牌位,随身携带。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古田织部最终也遭受了与千利休相同的命运。

由上千利休对茶道具的选择与创造可以看出,“侘び茶”的茶道具并非简单粗陋;虽同样强调精致美、需茶师倾注精力与心血,但为避免茶道具在传递“侘び茶”精神的茶道仪式中喧宾夺主、而选择刻意的暗淡化。
正如“形式往往是为内容服务”,在外在形式上,茶道仪式细节可以不同、茶道器物也可以由“唐物”转为“和物”;那么在内在精神中必然存在某些不变之处,是千利休“侘び茶”的精神境界,也是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侘び茶”都具有的生活意义。相对千利休的思想境界遥不可及、亦不可名状,“侘び茶”中传达的生活之态度当可作为借鉴。
[[i]]现藏于畠山纪念馆
[[ii]] 现保存在日本德川美术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