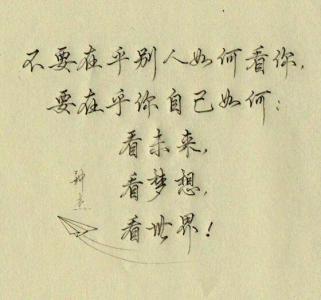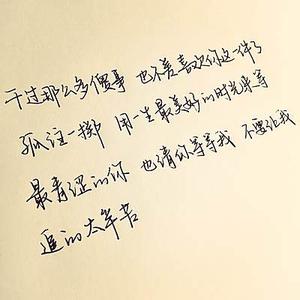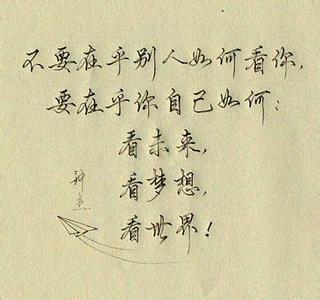两百年前,大约读懂林黛玉的人还不多。两百年后,好像还是不多。
关于林黛玉的解读有很多,批评她的观点就不说了。而赞美她的观点,不外乎说她貌美有才、追求独立人格之类的话头。夸大一些,说她的精神世界如何纯洁美丽,对外在的浑浊世界如何有反抗的精神和勇气,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对抗的高度。
但是我想,无论批评还是赞美,都没有真正把握住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用心。譬如你赞美她的纯洁的美,如何解释她对刘姥姥的恶俗吐槽?很多人当然会选择一些奇葩的角度来为林妹妹洗白,想洗总是有可洗的余地的。但是你动了洗白的念头,说明这一部分已经超出你预设的“纯洁的美”的范围了。以批判或赞美的二分观点去看待这个事儿,这种思维本身就决定了,这件事将永无可以恰当解释的希望。
我个人认为,牟宗三是真正看清楚作者用意的人。他的解读很朴素,也很简单:宝玉、黛玉这样的人物的存在,只是要表示世人对善恶两种人格之外的第三种人格的不理解。
贾母、王夫人、凤姐等等掌权派和实际频繁出场的人物,这些人无论怀着怎样的目的,若是能抛开意识形态对立的流毒,让我们回归生活的常情来判断,这些人都是希望宝黛能够好好生活下去的。然而因为这“不理解”,这些人的善意最终促成了悲剧。牟宗三是罕见的褒奖后四十回的人物,原因就因为后四十回将这“不理解”的主线写圆满了。黛玉因这“不理解”而亡去,宝玉因这“不理解”而断绝了和所有人的关系。这是完全看不到希望的绝境,是没有任何应对策略的死局。因为“不理解”,就是“不理解”,解释再多也不理解。
所以黛玉的好坏是非,无需褒奖或贬低,若是真的喜欢这个人物,就应予以理解。黛玉的生活方式带着浓烈的自戕的气息,用今天的话说,全是负能量。然而我们不要去分别这个善恶,以我们以为善的标准为“善”,以我们以为恶的标准为“恶”,强行将一个人物三七开还是怎么样。作者写《红楼》,正是可怜世上这种“审判者”太多了,是你们的善意杀死了很多黛玉,逼得很多宝玉去出家。又或许,本没有什么宝玉和黛玉,是我们的所谓“善恶”,杀死了本来独立的我们自己。
这是一种伪善。我们总喜欢宣扬一种标准化的善与美,天天鼓吹这些,让自己居于这个审判高地,然后以温和或激烈的方式杀死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比如,抽烟是有害健康的,年轻人你要努力,有修养的人虽知道但不说,看完这个拯救你的拖延症,我的写作的初心和我的文学梦……整天就是这些调调,讲着千篇一律的大道理,绝对正确毫无破绽。
这些整齐划一的“健康的”生活观背后,折射出的是人们对“个体”的不理解和冷漠。这种用三个故事说一个大道理的“新八股”文体,就是社群里的贞节牌坊。老实说,真正的八股文,要比这些搬砖文写得强多了。我总是很好奇,写作,这样私人化的内心活动的呈现,怎么就会形成这样整齐划一的“道德认同运动”呢?这种将“正能量”变成新的全民宗教的文化运动,完全是这个时代的“新道学”。
也许并不“新”,当它成为全面暴露人人瞩目的现实时,往往也是它的腐朽性已经入骨的时候。
胡塞尔在短暂戒烟后,说为了保持工作效率而选择了复吸。几万支香烟和几万杯咖啡,加速了一个人生命的燃烧,但是保证了其创作的质量和稳定性。大多经典的哲学、文学作品就是这么诞生的。曹雪芹要是选择健康向上的生活,你们就没有《红楼梦》可读了。创作艺术品的人,大都有拖延和熬夜的习惯,因为这不是在搬砖,加把劲就能提前搬完。这是生命自戕的美,是需要被理解的生活方式。
然而我并不想举这些功利的例子,用精英人士或哲学家、艺术家的成功来解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性。我只是想说,所谓的“不健康”的生活,也是一个人的自由,在他没有压榨别人的自由之前,就是值得尊重的。而所谓“生命自戕的美”,美就是美,就是完全无功利的。它不是要你觉得舒服,更不是要你觉得有用,它是一种姿态,处于不断流逝的时光之河的姿态。因为这流动性,它无法概括不能抽象。也无法复制。
这正是林黛玉这个形象的最成功处,她是几乎完全无功利性的自戕。她的生活方式无论美也好俗也罢,她就是那么生活的。二百年前,人们不理解。二百年后,也未必理解。因为你鼓吹着你的善与美,除了所谓的“伟大的爱情”的部分能引起文艺小清新们的共鸣之外,又怎能理解这样一种自戕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艺术。
黛玉其实本不为爱情,而是为了“还泪”。若我没记错,张爱玲曾说不喜欢林黛玉“还泪”的设定,认为古人没有纯爱,必须要“恩爱”。“爱”前面加一个“恩”,是这位文艺女性受不了的地方。我倒觉得,“还泪”的设定更纯粹,这就是一段不断自戕至死的生命的美。黛玉这个形象的意义,应该不是“爱情”这玩意儿所能局限的。
这个平常人只能试图模仿,其实却做不来,因为无法承受这样做的代价。这就是黛玉超越世俗生活的地方,因为她从不以世俗的生活为满足。她无需你来褒贬评判,只有理解或不理解。换句话说,理解与不理解,只是体现了我们自己的平庸与否,和黛玉本无关。
我们现在的理解能力,大概就是“道学家看见淫”这个水平。我们是鸡汤盛世下新的“道学家”,我们的趋同性和盲目性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愚民”要好一些。朋友圈里惊人一致的动作状态,就是这个判断的证明。杨绛因为我们的“民国才女情结”火了一把,吴亦凡又因为我们的“道德认同危机”火了一把。我们在极端趋同的信息交流中寻求着自我认同,其实是以消解掉“自我”的方式来流放自己。

理解生命是一个个需要被理解的个体,并不是要你去施舍给他怎样的道德恩惠。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能否理解自己也是个独立的个体。意识到他人的不健康是自己强行“健康化”的意识的产物,大约才会理解自己的生活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真正是“自己的生活”。才会让自己高喊的“写作梦”、“文学梦”、“xx梦”变成真正的“自己”的梦——虽然理解之后也许更容易体会这仅仅只是个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