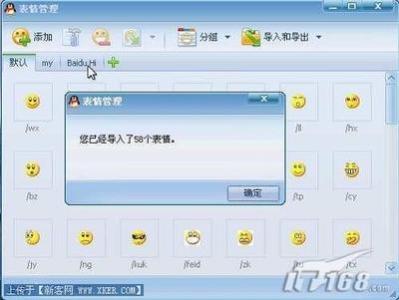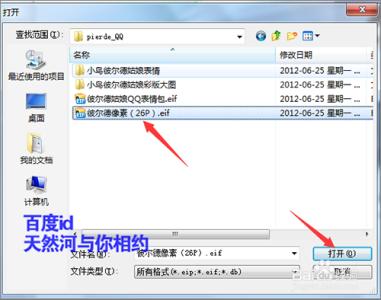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图为侵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二郎(右)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递投降书。
曾看到一个对日本好感度的调查,不喜欢的比例很高。反过来,日本也做过相关调查,对中国的印象不好。不喜欢日本,简单概之,因为那段侵略中国的历史及日本领导人表现的言行;那日本为何对中国也印象不好?说起来,都挺复杂,不是专家学者,不好在此作轻浮论述。
昨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不少国内媒体报道,有网友评论“玩弄文字和词语游戏,豪无悔意”,也有认为“终究是一个正常国家元首的正常态度”。
话说回来,为何德国反思二战赢得尊敬与合作,而日本对待战争的态度引发如此多争议?今日微信给大家带来一篇专注于研究日本的学者伊恩·布鲁玛的相关文章。文章选自伊恩·布鲁玛著作《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相较于很多学者研究视角的宏观,伊恩·布鲁玛在这本书里以其翔实的具体材料和敏锐的思考,在学者中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回应。
德国和日本迥异的二战记忆
文 | 伊恩·布鲁玛
足球,特别是欧陆足球,是检视各国国情一个很有用的风向标。2006年,德国举办了世界杯。除开决赛中齐内丁·齐达内的“铁头功”让人大跌眼镜外,这届世界杯还因为德国人迸发出的毫不做作、欢天喜地的爱国热情而显得与众不同。在过去,德国人有充分理由对在全世界面前挥舞民族标志物感到犹豫。这一次,他们这么做了,过程中流露出的友善让人无法将其误认为是什么邪恶的事。尽管德国队在2006年未能杀入决赛,但德国人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是德国人。
那届世界杯的另一大非凡之处在于,德国队赢球时,似乎没人会太往心里去。在过去可不是这样。比方说你是荷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或波兰人的话,输给德国就好像又被侵略了一样。因此,难得战胜德国队时就会大肆庆祝,仿佛甜蜜复仇。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这种情绪似乎终于消散了。对了,德国最好的两位球员都是波兰裔。
随着记忆淡去,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尽管有些历史记忆挥之不去,很是要命。但我相信,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我在1994年写作《罪孽的报应》一书时,世人仍很畏惧德国,也不信任这个欧洲经济强国。就在前不久,德国人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街头欢庆两德统一,震天响地高喊“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这在那些记忆尚未淡去的人听起来有一丝不祥的意味,某些德国人尤其如此。但到2006年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那句名言—“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听着比1989年时更像是在自抽耳光,荒谬得无以复加。作为欧洲一份子的德国做得十分出色,几十年来一直规规矩矩参与欧洲机构和北约的事务,因此若再对新一代德国人心怀戒备,会显得心胸狭隘。毕竟二战时,他们可尚未降临人间。不过,德国人之所以获得邻国更多信任,是由于他们正一点点学着信任自己,尽管这一过程缓慢而痛苦,且有时并不彻底。
总而言之,在西德,小说家、史学家、记者、教师、政客和电影导演都已经反思过德国最近的一段残暴历史,有时会执念于此,但态度往往相当开放和坦诚。很少有德国学童会不知道自己国家过去的滔天罪行。如果说有杂音的话,那么也确实有部分人开始对这种不间断、填鸭式的教育感到厌烦。直到21世纪,依然有公众人物就战争发表不甚光彩或不成体统的言论,但这些人随即会遭到其他德国人的口诛笔伐。
主张历史谢罪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但村山以及持类似观点的人很难改变日本政坛。
鉴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些区别,也许读者会以为我的书在德国更受好评。其实不然。该书在日本不仅销量更大,而且获得了更为积极的反馈。对此,我只能猜测个中原因。日本人乐见自己的国家被拿来和德国作比较,它们都有高效、干净、勤奋、守秩序等优点。而战后的德国人坚定不移地想成为自由、进步的西方社会的模范成员,他们可并不热衷于被人拿来同日本人作对比,因为这太像是对战前“东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种肯定和赞许。
然而,如若我的看法是对的,即两国之间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那么德国人这种神经过敏就毫无必要。不过,认为文化无关紧要、世界各国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想法很天真—在过去也被证明很危险。但文化差异绝对论—学界的理论家喜欢管这叫“抓住本质”—同样大谬不然,而且也很危险。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部分是想检验这些想法,探求类似的心理创伤何以影响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这项冒险之前,我的直觉是—您愿意的话也可以管这叫偏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似局面下反应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德日两国人的行为并不一致——但在东德、西德和日本,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局势也都迥异,今天亦是如此。
-END-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