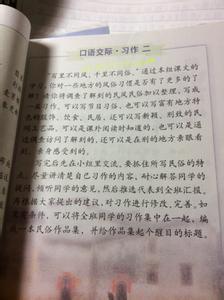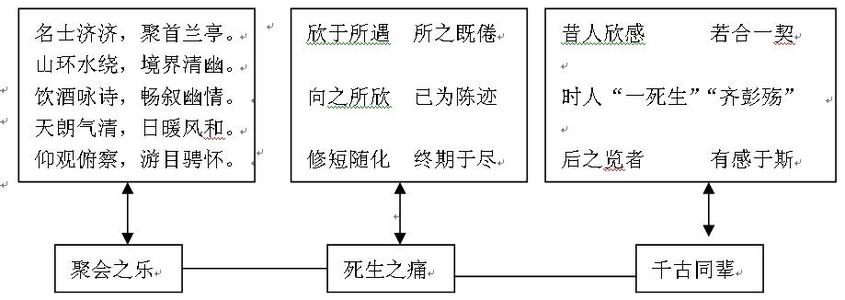如果說秋白通過自己的哲學研究已經形成了某種個人的理論的話,那就是折衷主義,是瞿世英的理想主義與張太雷的唯物主義的混合物。他早期的「厭世觀」已經為樂觀主義所取代。他接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不過他覺得,那更像是精神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由經濟因素所決定的必然之事。這是用佛教加伯格森主義的框架來闡釋歷史唯物主義,在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無異於異端邪說。在《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中,瞿秋白在好幾處都談到了哲學思考,不過主要是「宇宙的意志」和「生命的大流」之類的觀念。如果算不上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那他似乎一直是個二元論者。當然,在他加入共產黨后,這些觀念都必須摒棄。或許那個時候,他已經對形而上學方面的思考失去了興趣。
然而宇宙間的「活力」,那「第三者」(主體和客體之外)普遍圓滿,暗地裏作不動不靜的造化者,人類心靈的諧和,環境的應響,證實天地間的真理。況且「他」是「活力」,不流轉而流轉,自然顯露,不着相而着相,自然映照。他在個性之中有,社會之中亦有,非個性有,非社會有,——似乎是「第三者」而非第三者。
勞工神聖,理想的天國,不在於智識階級的筆下,而在於勞工階級實際生活上的精進。心靈的安慰,物質與精神的調和,——宇宙動率的相映相激——全賴於人類的「實際內力」。「實際內力」能應付經濟生活的「要求」及「必需」,方真是個人,民族,人類進化的動機。
這些觀察和洞見是他還在中國的時候所寫下的。在《餓鄉紀程》最後的「跋」(標註的日期是1921年10月,距他初到莫斯科已有九個月)裡,他還是表現出了對佛教概念和佛教象征的偏愛:
幾世紀幾千年的史籍,正像心血如潮,一剎那間已現重重的噩夢,印象稀微,何獨不因於此。人類社會的現象縈迴映帶,影響依微,也不過起伏震蕩於此心波,求安求靜,恃生活為己後援。一切一切都放在這「實際」上,好一似羣流匯合於心波的海底……心海心波的浪勢演成萬象,錯構夢影。醒時愈近,夢象愈真;亦許夢境愈強。心海普通圓滿,心波各趁奇勢;所以宇宙同夢,而星神各自炫耀他自己的光彩……(接著作者又鋪陳了一些比喻,而且間接談到了自己。)羅針指定,總有一日環行宇宙心海而返,返於真實的「故鄉」。
1921年12月24日,距離他加入共產黨還有兩個月,他在《赤都心史》裡的某一篇如此寫道:
「我」與「非我」相合,方有共同之處可言。「我」與「非我」相對,只覺個性之獨一無二。
如此,不得不有以繫連之:「愛」。
兒童酷好遊玩,誠然不錯;然而他假使不知道有「母懷」可返,遊玩便成迷失,漸覺可怕;我們個性的高傲,假使不能從「愛」增高其質性,他便成我們的詛咒。

像這種狂想曲般的晦澀冥想,在這兩本書中佔了很大的比重,「抒情段落」篇幅尤其多,相比之下實況報導就少得多了,特別是在第二本書《赤都心史》中。《赤都心史》所記述的是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的莫斯科,那正是一個多事之秋,而作者當時大部分時間都在莫斯科生活。書名既為「心史」,這也正是瞿秋白希望向讀者呈現的。他說,另外一些內容將在第三本書《俄羅斯革命論》中呈現[35],這本書我還沒有機會讀到。不過,既然瞿秋白把它描述成一本包含「歷史的觀察、制度的解釋」的「社會科學論文」[36],那么此書對理解他的個人生活恐怕幫助甚微。這裡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社會的動蕩和人類的犧牲對瞿秋白內心所激起的反應是否像其他事物,比如風景所激起的反應一樣強烈?貝爾加湖、烏拉嶺和俄羅斯荒原,帶有一種怪異的慘淡,又隱藏著一種不懼嚴冬的巨大力量,常常引發瞿秋白奇異的感想,讓他文思泉湧,寫出一些生動的文章,記錄他內心真切的感受。我們會期待他描述俄國革命中和人有關的場景時也能夠那么生動。但我們卻大失所望。從文風上來推斷,他在俄國社會的所見所聞并沒有激起他太多的感想。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充滿著戲劇性,但瞿秋白對它的報導卻顯得無力、敷衍,甚至可以說是半心半意、毫不熱心,這令我們十分詫異。他的這兩本書沒有把群眾運動中令人難忘的人物或場景躍然紙上地勾勒出來,連一個都沒有,絲毫沒有展現出他對共產主義革命理應有的幻想。文風上的扁平和單調恰恰反映出,在莫斯科的所見所聞並沒有給他帶來興奮和興致,畢竟只要他樂意,他絕對能夠寫得很出色。例如紅場上的一場遊行,他三言兩語就給草草打發了:
廣大的曠場,幾千赤軍,步馬砲隊,公認軍事組織,共產黨軍事訓練部,南宮,女工,兒童,少年都列隊操演。各國代表都致祝詞。……「萬歲」聲……
列寧在瞿秋白的記憶裡只留下了模糊依稀的印象,如他在報導中所寫的,列寧有著碩大的頭影,談吐「沉著果斷」。[37] 至於克萊摩宮(譯按:即克里姆林宮),他記述了它「巍然高大的城牆,古舊壯麗的建築」,以及「光滑雪亮的地板,金碧輝煌的壁柱,意大利名藝術家的彫刻」,可見他有點心不在焉,畢竟那裡是舉辦訪談和會議的重要場所。[38] 他也沒有把自己的生花妙筆用在俄國百姓的革命熱情上,畢竟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那些無名的「伊凡」們啊。瞿秋白對這些俄國百姓的總體印象是,他們對革命者以他們的名義所行之事既不開心,也不熱心。
不過,我們的作者在那個時候也悶悶不樂。這個廣袤的歐亞國家確確實實是餓鄉。到處都是饑荒導致的慘象,而新近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只能在茫茫晦暗中勉強地擠出一絲獰笑的幽影。這苦不堪言的生活條件使得瞿秋白更加關注自己的內心世界,灰暗的情緒如暗潮般在他的「心海」漲起。他沒有徹底心灰意冷也實屬意外。他的身體惡化得很厲害,加入共產黨的時候,他已經病得幾乎不成人形了。
《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是瞿秋白個人「心波」的記錄,書中的語句大量借鑒了他之前頗有研究的詩詞和佛經。他的這兩本書不是寫給無產階級和略微識得幾個字的人的,而是寫給他所屬的這個階級,即有一定文化修養的讀者,他們讀著四書五經長大,而今又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重新調整自身。這些讀者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由「五四」運動所促生的新文學的風格與內容。
自我表現,本就是中國文學的主流,由於西方名著與文藝理論的引進而更加風行。中國的抒情傳統為歐洲浪漫主義在華的成功移植提供了十分肥沃的土壤,而這一點還沒有被充分重視,人們往往只強調個體靈魂的覺醒。但是,白話文運動,以及隨之而生的文藝理論,為文人們抒發心志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於是,大量以自我表現為特色的作品應運而生。有的為戰鬥而吶喊,為特定或不特定的鬥爭而吶喊,為鬥爭中的勝利而吶喊;有的將自己的心志在作品中寄託於某個人物,可能是一位英雄、一個情人、一名烈士,或是一個世間最清醒最痛苦的靈魂;有的描寫受驚后錯位的靈魂,堅持要掀開自己的傷口給全世界看。這些是二十年代中國文學的風尚,瞿秋白似乎也被籠罩於其中。
如今,瞿秋白的這兩部作品已經顯得過時了。它們保有那個時代的獨特風味,那時的文學還只屬於少數人,散文和詩歌之間的界限還很模糊。那時白話雖然已經成為文學創作的工具,但仍然需要借文言之力來使得表達更加豐富、準確,更有感染力。瞿秋白的這兩本書寫得十分精緻與考究,就新聞報導的目的而言,甚至有點太過精雕細琢了。不過,瞿秋白的文學才華是毋庸置疑的,尤其當他抒發心緒時,可謂文采飛揚,惆悵之感,深深淺淺,躍然紙上。從文章的筆調、肌理、遣詞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作者對中國古典詩詞下過功夫並且不想對此隱匿不宣。就整體而言,這兩本書帶有直接受「五四」運動影響的文學作品的特點,雖然其中雕琢的文風和過度的感傷在如今已經顯得過時了。但是,瞿秋白為蘇維埃俄國寫的頌文,無疑是這類文章中寫得最早的,它們竟然充滿了個人悲傷的歎息,這真是對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文壇的一種諷刺!因為這些歎息來自瞿秋白,其間的矛盾顯得尤其有啟發性。我們無法確定他這個人持有多少熱情,不過他早期的作品透露著一種病態的蒼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