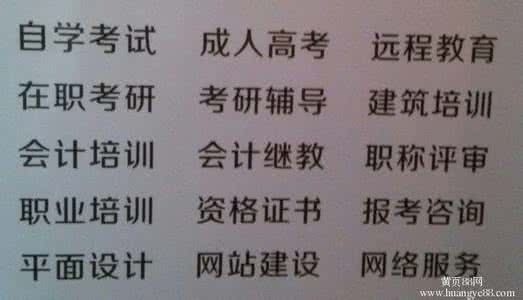一、韩文的历史虚无主义情绪
韩文开头说:“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中央集权,****,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在作者看来,“一般人”是怀着自卑的心态看待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的。他说:“不幸的是,此后(指鲁迅以后——笔者注)人们看中国历史,只看剥削压迫性;看西方历史,只看其进步性,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他又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也说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这就是韩文立论的情绪基础。作者的本意也许是打算跳出这种丧失自信的自卑情绪,因此他没有把自己置于“一般人”之中。他试图超脱“西方左右两翼理论”,从独立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诠释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根据他对“一般人”思想的曲解来看,应当认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同样是这种悲观的情绪,因此他就难免从另一个极端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首先,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这样认识中国近代史是很不全面的,因为近代中国历史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包括思想界人士自强不息、前仆后继为民族的振兴而勇敢探索,为之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作为后人,我们不但为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而“悲哀”(这个词汇并不准确),也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而自豪。如果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包括思想界总是笼罩在“悲哀”和“丧失自信”的情绪中,怎么会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怎么会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取得战胜外侮、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
其次,正如作者所言,“一般人”在提到中国历史的时候,容易联想到他所列举的那些消极的、反映否定性价值判断的词汇。但是这样理解“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很不全面的,因为,“一般人”在提到历史的时候,还会想到一些积极的、反映肯定性价值判断的词汇,例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礼仪之邦、百家争鸣、盛世、四大发明、繁荣、唐诗宋词、道德文章,等等。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只是联想到了一些消极的词汇,而且把这种联想强加到“一般人”头上。
事实是,在绝大多数的“一般人”,如果联想到那些消极的词汇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自卑,而是出于自强的理想,是有勇气面对自己民族弊病和不足的表现。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所蒙受的巨大灾难,中国思想界对我们民族自身的弊病的反思是十分痛切的。今天,先辈的理想已化为现实,我们处在历史的新的高度和氛围中,在回顾先辈们对历史的反思过程的时候,有时很难理解他们的痛切情绪,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甚至使用近乎刻薄的语言来针砭自己民族的不足和弊病。对于这一点,漂浮在现象的表面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我们必须深入到更深的层次;我们今天可以把中国所蒙受的灾难称作“屈辱史”,但是先辈们却是置身于“屈辱”的现实中的,这是在回顾先辈们的反思过程的时候不能忘记的一点。
反思能力、克服传统羁绊的能力,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理性,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光明前途的基本条件。任何进步、发展、创新,首先都是对传统力量的克服。一个民族的传统越是深厚,对创新、发展的羁绊力量就越大,克服起来就越是困难、痛切;如果这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崇尚祖制、抵触创新的特性,问题就更严重了,任何创新的思想和举措都会付出巨大的甚至是血的代价。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康梁变法,阻碍改革的最大的力量不仅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是传统观念的力量。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一方面造就了历史的辉煌,一方面也形成了牢固的传统,对进一步地发展、创新造成强大的羁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有时甚至近乎停滞,包括韩文所不解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中国”,都与此不无关系。因此,反思(包括批判和继承)传统、克服传统的羁绊,其深刻程度就必须是革命性的,不但需要深邃的思想,更首先需要巨大的勇气。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思想界有着一大批勇敢的探索者。
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傲视于世界民族之林。“秦王扫****,虎视何雄哉!”秦王们“虎视”所及,便是“中央之国”,并且看到这个“中央之国”以外还有其他民族,也在“虎视”、“狮视”、“狼视”着。秦王们的指导思想,便是在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筑起我们民族的牢固坚硬的外壳,一则抵御外边的虎狼们,一则保护内部的躯体。万里长城是物质的,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筑起外壳”这种思想,可以说“筑起外壳”的思想渗透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的社会体制和具体运行的机制都体现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合理性,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而且外壳的存在果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民族在其保护下稳定、繁荣。但是,无庸讳言,外壳毕竟是消极的,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限制了进一步的发展、强大。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重创了我们民族的外壳并深入我们躯体内部贪婪吞噬。这时,中华民族要振兴、要自立,首要的、迫在眉睫的、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反思传统,克服羁绊。这种反思所需要的巨大勇气,丝毫不亚于抵御外侮。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反思、克服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的痼疾。尤其是敢于抛弃外壳,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世界,求得自身的健壮和发展。反思当然包含继承和批判,但是在当时,首要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是批判。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在当时,人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批判是那样的尖锐,深刻,痛切,以至于韩文感到,对中国历史的这些批判性的认识,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常识。但是正是批判使得我们获得了前进的力量和方向,知耻而后勇,此之谓也。先辈们对民族传统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诚挚、深邃的热爱,因为爱之深,所以痛之切。
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吃人论”很不以为然。韩文说:“鲁迅先生应该同时能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东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剥削压迫日益严重、集权****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丧失、穷人的****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的历史!吃人与被吃是从出现私有制起的“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东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释其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作者在这里真是义正辞严啊,可惜是无的放矢。因为,鲁迅笔下的“吃人”,不是指物质上的剥削压迫,不是指穷人的****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而是指封建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等等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禁锢,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的扭曲与泯灭,指造成人们意识上自私、麻木、愚昧的那些因素,造成一盘散沙的那些因素,造成堂堂大国在外敌面前不堪一击的那些因素!总而言之,“吃人”指的是精神上对人性的禁锢和扭曲,指的是封建礼教对人格的压迫和****。被“吃”的不仅是穷人,也包括富人,首先包括知识分子。这一点只要读过鲁迅作品,并且把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氛围中来体验,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呢?站在今天的高度上和氛围中,当然无需加重语气指出封建礼教“吃人”,但是在封建的思想文化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指出封建礼教“吃人”,是具有振聋发聩的伟大意义的。有什么理由去指责前辈人“单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性”,甚至臆测前辈人“最后就会单方面否定中国历史、肯定西方历史,制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西方“吃”中国”?
总之,从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道德的层面,深刻地揭露自己民族的历史弊病,这绝对不是什么自卑、失去自信,而是有信心、有勇气的表现,这样的民族才是理性的、有前途的、不可战胜的;同样,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唤也绝对不是对西方社会的盲目羡慕。
在反思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虚无主义的倾向和思潮呢?当然是有的,这种思潮全盘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妄自菲薄,自惭形秽,盲目羡慕西方社会的成就,确实如韩文所说完全失去了自信,很没出息。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思潮从来不曾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从五四运动的领袖们,到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在揭露自己民族、国家所以落后的历史原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定自己民族、国家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只是在当时,甚至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振兴的主要任务是克服自身的弊病和不足,因此对这些弊病和不足的揭露和批判就显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而已。这些都被韩文理解成“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了。
我不知道韩文所说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是指什么,我只想指出,进入新中国的大多数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他们破天荒成了国家的主人,那种充满自信的豪情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钱学森们才不顾一切返回祖国,所以中国能在朝鲜以至弱战胜至强,所以中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在今天所难以设想的极端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设起了初步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无视中国的存在,“东亚病夫”再也不是中国人的形象。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不用说两弹一星、完善的工业体系,单是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就是伟大的人间奇迹。怎么可以设想,这些成就是“自觉低人一等”的人们能够取得的。如果说后来的经济建设出了问题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在思想意识上仍然自觉低人一等”,恰恰相反,是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走向极端,轻视客观规律的结果。尽管后来的人们为了改弦更张,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描绘的一团漆黑,并且放任敌对势力抹黑毛泽东时代,但是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并不因为后人的好恶、人为的描绘而改变。
二、中国古代是市场经济社会吗?
韩文用了大量篇幅,旁征博引,论证在古代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而且是发达的市场经济。这是作者立论的认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
作者根据〈〈管子〉〉的记载,“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证明“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还是根据《管子》,“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举出“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的例子,列举了当时着名的大商人范蠡、陶朱公、弦高、吕不韦等人,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
当然,自秦汉以后,市场经济的发达就更不得了。
但是,作者显然是把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和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了,或者说他把交换、交易行为牵强附会地说成市场经济了。这使我联想到一个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某个地区的领导听说要实行市场经济,就部署说:我们地区要有计划地建设几个大市场。原来这位领导根本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以为多搞点买卖东西的场所就是市场经济了。纵观韩文关于古代市场经济的描述,我觉得作者和这位领导犯了同样的错误。当然作者不是不懂,而是为了论证他的历史观,故意牵强附会地将交易行为混同于市场经济就是了。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的源头追溯到货币产生以前,追溯到原始社会,因为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交换行为,尽管在那时还只是偶然的、实物的交换,但既然是交换,就具有交换的一般性质,因此也可以把原始社会说成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了。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
市场经济必定包含交换、交易的行为,必定要在市场上将产品实现为商品。没有交换、交易行为,就没有市场经济。但是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不是市场经济,却不能仅仅根据有没有交换、交易的行为,不能因为存在大量的交换、交易行为就断定这个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总之,不能把交换、交易行为,把市场等同于市场经济,
什么是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着眼点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例如人们通常着眼于资源配置与调节、生产力运行形式等角度定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或本质。但是无论怎样定义,人们所谈论的市场经济肯定不是简单地指交易行为的存在,而是市场对社会经济已成为一种支配力量,处于社会经济运转的主导地位。简言之:生产的目的必须是交换,劳动产品必须成为商品。
交易行为是市场存在的条件之一。但要形成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工的普遍化。韩文说:“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是啊,产权私有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自不待言,但是分工却不是简单的“存在”,而必须是普遍存在;交换也不是简单的存在,而必须是作为生产的目的而存在。没有普遍的社会分工,所谓市场就只能是零散的、简单的交换行为,能够转化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只能是少量的。这种交换行为无论多么繁荣兴旺,都不足以称之为市场经济。而社会分工的普遍化,只有在工业社会才能实现。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生产的分工既不普遍,也很简单,所谓城市,也只不过是交换行为的比较集中的场所而已(“市”和“集”一样本来就是交易场所),远远谈不上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中,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消费,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所占的比重很小。尽管在从自然经济向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是接近自由经济,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所占的比重越大,但是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全面改变生产的目的。在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生产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的,需求旺盛,生产就旺盛,需求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而在自然经济中的情况恰好相反,生产发达,可以用于交换的东西才丰富,市场才发达,生产对需求的刺激远远大于需求对生产的刺激。在韩文所谓的市场经济中,我们看不到激烈的竞争,以及由竞争所带来的生产的进步。
至于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社会运用市场的机制来调节资源的流向等等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更谈不上了。
韩文为了证明中国古代存在市场经济,特别指出当时存在的土地和劳动力买卖。“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并据此把地主也划归“商人”之列。可是,韩文完全忽视了所谓土地买卖的具体情形和条件,完全从“买卖”的行为本身出发来看问题,在韩文看来,买卖土地就像买卖衣服那样,就是非常单纯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般的交易过程。
土地买卖是怎么回事?如果稍有常识,如果哪怕只是简单地考察一下古代甚至是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农民出卖土地的情形,就可以了解,土地买卖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所谓土地(生产要素)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绝对不是多余的东西,可以“任意买卖”的。如果农民不是走到了绝路,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就绝对不会出卖土地——出卖土地的时候就意味着走到了生死的关口,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饥寒而亡已经顾不上长远的生存;而地主收买土地,则是趁火打劫,聚敛财富,掌握农民的命脉以便更加残酷的剥削他们。这种所谓“交换”既不可能是等价的交换(因为买卖双方根本不在平等的地位上,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是买方强势,卖方弱势),也不可能刺激生产,发展生产,相反,失地农民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即向地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亦即被韩文纳入“市场经济”概念的“劳动力买卖”),其积极性将大打折扣。在这里,绝对不像韩文所说什么生产资料的市场交换,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那般美妙,因为土地没有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商品,这根本不是市场,不是经济活动,而是地主对农民的盘剥、赤裸裸的聚敛财富而已。与其说这是经济行为,不如说是地主对农民的强取豪夺更准确,这种所谓“交换”,浸满了失地农民的血泪,是农民到了如果不出卖土地和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的地步的被迫的选择。至于把地主当作商人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商人”如果不是指交易双方,也应该指卖方才是,而且卖方必须盈利;如果土地交易中存在商人,那么出卖土地的农民才是商人,地主不过是消费者而已,可是农民并不盈利——何等混乱的逻辑!
韩文指出:古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这是正确的,尽管作者故弄玄虚地把“土地”说成“生产要素”,毕竟他指出了一个事实:所谓重农抑商,主要就是抑制土地兼并。但是作者把这当作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控,认为这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且以较长的篇幅论证了在这种干预下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地主、商人都可以称之为资本家,这就值得商榷了。如上所述,土地买卖活动根本就不是经济活动,因此国家所干预的就不是经济,只是干预地主对农民的盘剥程度,聚敛财富的程度而已,重农抑商的目的也很简单:抑制两极分化的趋势,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平衡,不使农民陷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从而危及统治者的江山社稷。因此,重农抑商政策在本质上不是经济政策,而是政治政策。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调控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只是在发展到了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的时候才由国家实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阶段,直到韩文所提及的“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的时候,资产阶级是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甚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被当作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只是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威胁下,尤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的教训下,资产阶级才普遍认识到并接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由市场经济才发展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阶段。着眼于经济来说,国家干预经济在本质上是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反制手段。
当然,中国古代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长期稳定、平衡的社会生活环境,使得现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得到有利条件和环境,于是生产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发展),人口增长,剩余的劳动力分流到其他行业也就多了起来。这就是韩文所说的市场经济的繁荣。但是恰恰还是在重农抑商的政策禁锢下,加上体制结构的稳固性,这种繁荣终究没有导致生产目的的根本转换,不可能产生竞争和竞争的压力,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技术,也就不可能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强烈要求,而且自然经济中的生产方式并不要求(起码是不强烈要求)劳动者发挥创造性——这大概就是韩文百思不得其解的“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的答案,重农抑商政策下不可能导致市场经济,在重农抑商政策尚能容纳生产力时,是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的。
综上,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即使在每个朝代的后期,市场经济已经得到相当的发育,但市场经济也没能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生产的目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自然经济的社会。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秩序,逐步增加的劳动产品必定越来越多地涌向市场变成商品,造成竞争,导致市场经济成分的量的增加,最终导致质变,引发工业革命,自然地而不是被迫地走向市场经济。
三、韩文否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在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上,韩文接着就要否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很自然的,商人、地主在作者看来就是资本家,农民就是无产阶级,农民起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一)
韩文否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理由,不是从着眼于生产关系等基本的社会方面,而是着眼于“封建”的字面含义,从“封建社会”的名分出发来提出论证的。
韩文说:“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因此,作者对于“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是很有意见的,因为中国自秦以来的社会并不是“封国土、建诸侯也”的社会,而是中央集权的社会。
如果作者是个中学生,他在回答语文老师“什么是封建”的提问时说:“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那么可以得满分。但是这里是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而不是名词解释。我也认为将中国古代社会名之为封建社会不见得完全恰当,但是“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的时候,并不是根据中央集权与否,而是根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当然也和人们主观上要和欧洲封建社会相对应有关。分封制抑或是中央集权制,只是国家政体的表现形式,不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不能根据它的政体,只能根据它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就好像今天虽然英、日等国保留君主立宪制度,但是并不能据以否认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至于为什么要称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而没有冠以别的名称,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名称具有局限性,由于这个概念的广泛使用和深入人心,已经很难改称其他名称了。总而言之,此“封建”非彼“封建”,中国古代社会的称谓并不规定该社会的体制和政体。但是韩文却恰恰从“封建社会”的名分出发来分析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并非“封国土、建诸侯也”的社会就否认其封建性质,这是很可笑的。
韩文说,“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可是,究竟是谁个曾经“把秦以后的中国当作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作者究竟了解不了解“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出现、其内涵发展的过程和讨论的过程?仅仅因为把中国古代社会叫做封建社会,就是把它当作了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了?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封建”的概念从来不单纯指“封国土建诸侯”。所谓“封建”还有另外两个意指:一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二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第二章。在同一章里,何怀宏引用了新中国史学巨匠侯外庐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将中国古代社会以“封建”名之:“我们把中国中世纪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然而,秦废‘封建’,为什么又成了封建制社会呢?我们的答复是∶秦废封建的‘封建’二字,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是‘宗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这里我们所举出的封建制社会,‘封建’这两个字则是立基于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译自外文Feudalis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为时已久,我们倒也不必在此来个正名定分,改易译法。”)。其实不止“封建社会”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的概念也存在争议,以至于有的学者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定义的时候感叹:“资本主义”这个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都较“资本主义”一词为佳(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512页)。因此,韩文仅仅从“封建”的名称的问题来否定古代社会的性质,又虚构出“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批驳对象,是没有意义的。
(二)
韩文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作者在这里又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批驳对象。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说过,“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从来没有明确地规定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里找不到关于社会形态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五个阶段的任何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西方人,他们所描述的封建社会主要也是西方封建社会的状况。至于把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混为一谈,我看那是韩文的虚构,我孤陋寡闻,没有见过这样的观点。
社会主义发展到斯大林阶段的时候,发生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和偏差,并且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及其实践,尤其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教条主义的表现之一,是片面强调世界的统一性,而忽视多样性。其中,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也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成为主导中国思想意识的理论。虽然马克思说过类似五种社会形态的话(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的一段话),但并未明确地为各个社会形态命名,更没有认为人类社会要严格地按照这些形态递进发展,只是到了苏联时代才有了明确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虽然韩文作者以“作为80年代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新一代”自况,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局限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中,所以他把教条主义者的观点扣到马克思主义头上是很自然的。但是即使在教条主义者那里,也从来没有公然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因为那样的话,就无法解释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何以能领导人民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概述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和趋势,同时也不否认具体到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强调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这些属于常识的东西,在韩文那里变成了“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似乎马克思主义认为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历程都是千篇一律的,处于同样阶段的各个民族、国家的状况都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和18世纪以前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综上,中国古代社会能否称之为封建社会可以存疑,但是这绝不是可以把中国古代社会说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由。韩文生硬地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外衣套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身上,或者套用韩文的话说,削中国历史之足,适西方资本主义之履,简直就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结果是把中国古代社会更加弄得面目全非了。
四、韩文借马克思之口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并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
韩文在将中国古代社会定性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没有忘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理论支持。但是我们看到,作者同样是按照他自己对中国历史作出的结论来重新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观点,然后让被他诠释过的马克思的观点来支持他的论点。通过韩文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对无产阶级的定义等等的论述,可以看出韩文借马克思之口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并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
(一)所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
为了看清韩文是如何重新诠释马克思的观点的,让我们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韩文原文: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理解。一种定义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的。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领主、奴隶主,没有资本家。但是,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16世纪后半叶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刚刚发生、还远没有影响到法国经济时,1789年的法国革命,又都被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马克思还有另一种定义,即从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大体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奴隶,则是奴隶社会;是农奴,则是封建社会;是自由雇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按这个定义,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才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受益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曲解。
实际上,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涵义不明确的、模糊的概念。而使“资本主义”具有明确内涵、以至人们耳熟能详、成为常识的概念,是马克思时代以后的事情。因此,在马克思着作里可以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概念,大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含义。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多有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习惯使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或类似的词语来称呼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例如上文所引:“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再如《共产党宣言》中:“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等等。怎能设想,马克思对于一个连自己也未形成明确含义的概念会提出什么定义呢?而且作者还让马克思从两个着眼点提出两个定义!
或者会辩解说,韩文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马克思笔下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定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我赞同这种看法,但是同时需要指出,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或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从来没有单纯着眼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在描述阶级和社会形态的时候,从来没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而总是从生产力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整体上来展开论述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作者强加到马克思头上的“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
韩文说,马克思认为“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大概是指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马克思是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是在形象地说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而不是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过程(韩文作者大概不知道,手推磨这种“生产技术”在奴隶制社会也是存在的)。联系上下文,马克思所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中的“社会”,置于特定语境中,不是指社会形态,而是与上面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是同义语。如果说马克思这段话可以看作什么定义的话,那么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定义,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在这里,在马克思笔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的,是对立统一的。韩文之所以得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的荒谬结论(更糟糕的是作者把这个结论强加到马克思头上),之所以对马克思将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大惑不解,是因为他预设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实际情形是,如同在奴隶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一样,在封建社会中也产生了新兴资产阶级,而且这些新兴阶级是处于被统治地位上的革命的阶级——关于这一点,关于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有着系统而明确的论述,资产阶级从作为被统治阶级到作为统治阶级、从革命阶级到反动阶级的发展演变过程,都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明确的结论。总之,所谓马克思“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完全是韩文的不负责任的杜撰。
第三,对于所谓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定义资本主义,韩文诠释道:“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奴隶,则是奴隶社会;是农奴,则是封建社会;是自由雇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这样诠释并不严谨,带有庸俗化的倾向,但是这样理解大体是准确的。然而问题是,韩文由马克思将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推断出发生革命的这些地方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推断出这是马克思将这些地方的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这就属于牵强附会了。诚然,革命前的尼德兰、英国、法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很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足以发动革命来****现有的封建****统治,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被革命****的那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封建社会。换言之,革命前的尼德兰、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因素在数量上的增长已经到了引起质变的程度,于是革命就发生了。总之,新兴的资产阶级产生于旧社会,而不是韩文所理解的只存在于新社会。
(二)所谓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定义
为了进一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支持,韩文在杜撰出所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两个定义后,很自然的,又杜撰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两个定义,而且同样,让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分别着眼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提出两个定义。
“从生产关系看,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的,即属于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失业者是劳动力的后备军,因此也是无产阶级”。于是,“按照此定义,则古代中国的佃农、雇农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谓流民(即失业者),都属于无产阶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
这简直就是胡言乱语了。如果马克思果然有这样的定义,那么奴隶时代的奴隶岂不更是无产阶级了?我们要问,马克思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定义?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描述或曰定义,什么时候脱离过时代背景?
2、“另一个定义是从生产力方面看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产生于现代工业。相应地,也只有在现代工业条件下,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马克思在描述无产阶级的时候确实有类似的说法,但是,这可不是“从生产力方面看的”,马克思笔下的现代工业、机器磨等等概念,不单纯指生产力,更多情况下指的是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从来没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成不相干的两件东西,然后着眼于其中的一件做出什么定义。
恩格斯于1847年在着名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以非常通俗的语言非常明确地为共产主义的诸多概念做出了定义。例如,“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但愿韩文作者在读了这一段之后不会说,这是恩格斯从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的角度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更不会说,这是恩格斯从时间的角度对“无产阶级”的定义!但愿韩文作者继续往下读,读到“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的时候,不会因为马克思把早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尼德兰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架的结论!
五、割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最终将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在理论上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必然要夸大它们矛盾的一面,将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在韩文看来,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得出的不同定义、结论之类,也就完全是非此即彼的。而这时就会发现,是不是如同唯物史观所揭示的那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是社会发展(革命)的本源动力,就成了问题,就陷入了韩文所谓历史的悖论中去了。于是,就必然要到精神领域寻求答案,必然要继而将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夸大它们矛盾的一面,夸大精神的作用,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全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发展的历史悖论,是韩文强加到马克思头上,然后加以分析批判,然后试图跳出这一悖论,就是说,韩文分析批判的、试图跳出的历史悖论,其实是他自己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理解而制造出来的。
例如,韩文在杜撰出马克思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给无产阶级做的两个定义以后说,“这两种定义对革命的动力、时机、方式、结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韩文说,按照从生产关系出发的无产阶级定义,“革命的动力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按照从生产力出发的定义,“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还可以发展时,哪怕剥削、压迫多么深重,都不可能产生革命,也不应该革命——因为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看来作者认为,深重的剥削、压迫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并不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马克思主义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基于社会发展的事实考察,对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着辩证的分析判断和评价。简单说来,就是,一方面肯定资产阶级曾经作为革命阶级的历史作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一方面对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本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给以严厉的批判。而这在韩文看来,却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心态是很矛盾的”,韩文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肯定和否定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就形成了所谓的矛盾和历史悖论:“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肯定中,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被杀戮、被掳掠者的生命和尊严消失了,一切道义、情感、理想消失了,剩下的是冷冰冰的‘现金交易’和‘历史规律’。共产主义不再是劳动人民对于无阶级社会的向往,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在这一自然历史进程中,拿破仑和波拿巴,俾斯麦和希特勒,英雄和流氓,都成了历史合力的不同分力,都将汇合到共产主义的洪流中”。这真是匪夷所思!为什么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就是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被杀戮、被掳掠者的生命和尊严消失了呢?为什么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共产主义就“不再是劳动人民对于无阶级社会的向往,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了呢?韩文按照怎样的逻辑,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弄成了非此即彼的呢?
我理解韩文所谓矛盾或历史悖论是这样的(我在此不愿意引用韩文原文,因为韩文的表述较为冗长而混乱,读来使人如坠雾里而不知所云):马克思主义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而按照同一规律,则应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是两极分化,又不应该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而是应该鼓励(起码是乐见)两极分化的实现。韩文说:“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被贴上了封建社会的标签,可以任意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加以杀伐掠夺;在生产力还可以继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内,本国的工人则只能继续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样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被贴上了早产儿的标签,被剥夺了历史合理性”。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客观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剥削压迫的合理性,并为之提供了理论根据。韩文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剥削就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剥削,是有合理性的、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忍受也必须忍受的剥削。”因此韩文认为“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甚至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首席经济师”。
在这里,韩文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弄的面目全非,然后指出:这是悖论。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由韩文来提出答案:怎样走出悖论。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如同充分肯定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历史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同样也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如同强烈批判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强烈批判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然而马克思主义在肯定剥削阶级曾经起过的革命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剥削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要走向反面,成为反动阶级的必然性。剥削阶级在上升时期起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但剥削阶级的本性,私有制的社会体制,却最终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悖论是有的,这就是在剥削阶级那里,它们越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越是成为禁锢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资产阶级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实践革命作用的同时,也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一切剥削阶级由其本性所决定都走不出这个历史悖论。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是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革命,就是因为革命将最终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人类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
六、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剥削阶级从革命走向反动的过程,就是从解放生产力到禁锢生产力的过程。就资产阶级而言,对生产力的禁锢,一方面通过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或社会不公表现出来,一方面通过限制、抑制、抵制生产的社会化表现出来。当资产阶级再也无法通过改良、改善社会机制来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时,革命的时代就会到来。
任何社会、任何生产关系的存续过程,必然同时也是完善自身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是高于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社会,其完善自身的能力,其容纳生产力的能力,其理性程度,更是远非其他剥削阶级社会所能比拟。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其中最为深刻、可以称之为革命性变化的完善过程,是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个转变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所完善的不只是经济运行的体制,更重要的是缓和了生产关系的矛盾,缓和了阶级矛盾(韩文忽视了这个转变,因此看不清资本主义至今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吸纳了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理念。马克思的时代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时代,马克思无从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完善自身的能力和容纳生产力的限度,韩文所说“资产阶级比马克思聪明”的那些变化马克思确实没有看到。但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趋势并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的转变,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丝毫不能证明唯物史观是错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虽然得以缓和、调和,但是却没有解决,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也不可能解决。
在资本主义表现出旺盛生命力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经历了高速的、堪称奇迹的发展之后,却表现出来停滞不前,最终被资本主义甩在后面,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关于这种情况的原因,这些年来中外学者已有众多的分析。我认为,无论在前苏联还是中国,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偏差,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实际上并没有构建起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斯大林开始,就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混为一谈,认为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自然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是可以依靠自身机制解决社会运行中的矛盾的,因此是无需改革、发展、完善的。人们没有搞清,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回事,生产关系是另一回事。公有制不过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但它本身并不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着力构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没有发挥出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另文阐述。总之,社会主义的挫折,同样没有证明唯物史观的失败,相反,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脱离、背离了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的结果。共产党人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就一定能够迎来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
历史总是按照其固有规律前进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绝不会因为暂时的曲折而改变。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这一点,因而马克思主义者永远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革命的动力来源等等问题,近些年来有着活跃的讨论和议论。发生这种情况的现实背景是,历史似乎没有按照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迄今看不出衰亡的迹象;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迄今看不出复兴的迹象。于是,不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兴高采烈地宣称唯物史观已经破产,就是在社会主义内部,在思想界,各种思潮、观点也不断出现。韩德强同志《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一文(以下简称《韩文》)所体现的观点,就是较有代表性的。我对韩德强同志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为了响应《乌有之乡》讨论历史观问题的吁请,特不揣冒昧,提出粗浅见解,就教于韩德强同志,并希望得到方家指教。
一、韩文的历史虚无主义情绪
韩文开头说:“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中央集权,****,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在作者看来,“一般人”是怀着自卑的心态看待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的。他说:“不幸的是,此后(指鲁迅以后——笔者注)人们看中国历史,只看剥削压迫性;看西方历史,只看其进步性,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他又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也说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这就是韩文立论的情绪基础。作者的本意也许是打算跳出这种丧失自信的自卑情绪,因此他没有把自己置于“一般人”之中。他试图超脱“西方左右两翼理论”,从独立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诠释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根据他对“一般人”思想的曲解来看,应当认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同样是这种悲观的情绪,因此他就难免从另一个极端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首先,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这样认识中国近代史是很不全面的,因为近代中国历史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包括思想界人士自强不息、前仆后继为民族的振兴而勇敢探索,为之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作为后人,我们不但为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而“悲哀”(这个词汇并不准确),也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而自豪。如果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包括思想界总是笼罩在“悲哀”和“丧失自信”的情绪中,怎么会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怎么会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取得战胜外侮、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
其次,正如作者所言,“一般人”在提到中国历史的时候,容易联想到他所列举的那些消极的、反映否定性价值判断的词汇。但是这样理解“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很不全面的,因为,“一般人”在提到历史的时候,还会想到一些积极的、反映肯定性价值判断的词汇,例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礼仪之邦、百家争鸣、盛世、四大发明、繁荣、唐诗宋词、道德文章,等等。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只是联想到了一些消极的词汇,而且把这种联想强加到“一般人”头上。
事实是,在绝大多数的“一般人”,如果联想到那些消极的词汇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自卑,而是出于自强的理想,是有勇气面对自己民族弊病和不足的表现。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所蒙受的巨大灾难,中国思想界对我们民族自身的弊病的反思是十分痛切的。今天,先辈的理想已化为现实,我们处在历史的新的高度和氛围中,在回顾先辈们对历史的反思过程的时候,有时很难理解他们的痛切情绪,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甚至使用近乎刻薄的语言来针砭自己民族的不足和弊病。对于这一点,漂浮在现象的表面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我们必须深入到更深的层次;我们今天可以把中国所蒙受的灾难称作“屈辱史”,但是先辈们却是置身于“屈辱”的现实中的,这是在回顾先辈们的反思过程的时候不能忘记的一点。
反思能力、克服传统羁绊的能力,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理性,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光明前途的基本条件。任何进步、发展、创新,首先都是对传统力量的克服。一个民族的传统越是深厚,对创新、发展的羁绊力量就越大,克服起来就越是困难、痛切;如果这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崇尚祖制、抵触创新的特性,问题就更严重了,任何创新的思想和举措都会付出巨大的甚至是血的代价。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康梁变法,阻碍改革的最大的力量不仅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是传统观念的力量。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一方面造就了历史的辉煌,一方面也形成了牢固的传统,对进一步地发展、创新造成强大的羁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有时甚至近乎停滞,包括韩文所不解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中国”,都与此不无关系。因此,反思(包括批判和继承)传统、克服传统的羁绊,其深刻程度就必须是革命性的,不但需要深邃的思想,更首先需要巨大的勇气。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思想界有着一大批勇敢的探索者。
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傲视于世界民族之林。“秦王扫****,虎视何雄哉!”秦王们“虎视”所及,便是“中央之国”,并且看到这个“中央之国”以外还有其他民族,也在“虎视”、“狮视”、“狼视”着。秦王们的指导思想,便是在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筑起我们民族的牢固坚硬的外壳,一则抵御外边的虎狼们,一则保护内部的躯体。万里长城是物质的,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筑起外壳”这种思想,可以说“筑起外壳”的思想渗透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的社会体制和具体运行的机制都体现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合理性,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而且外壳的存在果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民族在其保护下稳定、繁荣。但是,无庸讳言,外壳毕竟是消极的,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限制了进一步的发展、强大。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重创了我们民族的外壳并深入我们躯体内部贪婪吞噬。这时,中华民族要振兴、要自立,首要的、迫在眉睫的、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反思传统,克服羁绊。这种反思所需要的巨大勇气,丝毫不亚于抵御外侮。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反思、克服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的痼疾。尤其是敢于抛弃外壳,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世界,求得自身的健壮和发展。反思当然包含继承和批判,但是在当时,首要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是批判。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在当时,人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批判是那样的尖锐,深刻,痛切,以至于韩文感到,对中国历史的这些批判性的认识,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常识。但是正是批判使得我们获得了前进的力量和方向,知耻而后勇,此之谓也。先辈们对民族传统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诚挚、深邃的热爱,因为爱之深,所以痛之切。
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吃人论”很不以为然。韩文说:“鲁迅先生应该同时能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东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剥削压迫日益严重、集权****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丧失、穷人的****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的历史!吃人与被吃是从出现私有制起的“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东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释其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作者在这里真是义正辞严啊,可惜是无的放矢。因为,鲁迅笔下的“吃人”,不是指物质上的剥削压迫,不是指穷人的****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而是指封建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等等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禁锢,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的扭曲与泯灭,指造成人们意识上自私、麻木、愚昧的那些因素,造成一盘散沙的那些因素,造成堂堂大国在外敌面前不堪一击的那些因素!总而言之,“吃人”指的是精神上对人性的禁锢和扭曲,指的是封建礼教对人格的压迫和****。被“吃”的不仅是穷人,也包括富人,首先包括知识分子。这一点只要读过鲁迅作品,并且把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氛围中来体验,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呢?站在今天的高度上和氛围中,当然无需加重语气指出封建礼教“吃人”,但是在封建的思想文化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指出封建礼教“吃人”,是具有振聋发聩的伟大意义的。有什么理由去指责前辈人“单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性”,甚至臆测前辈人“最后就会单方面否定中国历史、肯定西方历史,制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西方“吃”中国”?
总之,从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道德的层面,深刻地揭露自己民族的历史弊病,这绝对不是什么自卑、失去自信,而是有信心、有勇气的表现,这样的民族才是理性的、有前途的、不可战胜的;同样,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唤也绝对不是对西方社会的盲目羡慕。
在反思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虚无主义的倾向和思潮呢?当然是有的,这种思潮全盘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妄自菲薄,自惭形秽,盲目羡慕西方社会的成就,确实如韩文所说完全失去了自信,很没出息。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思潮从来不曾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从五四运动的领袖们,到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在揭露自己民族、国家所以落后的历史原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定自己民族、国家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只是在当时,甚至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振兴的主要任务是克服自身的弊病和不足,因此对这些弊病和不足的揭露和批判就显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而已。这些都被韩文理解成“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了。
我不知道韩文所说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是指什么,我只想指出,进入新中国的大多数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他们破天荒成了国家的主人,那种充满自信的豪情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钱学森们才不顾一切返回祖国,所以中国能在朝鲜以至弱战胜至强,所以中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在今天所难以设想的极端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设起了初步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无视中国的存在,“东亚病夫”再也不是中国人的形象。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不用说两弹一星、完善的工业体系,单是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就是伟大的人间奇迹。怎么可以设想,这些成就是“自觉低人一等”的人们能够取得的。如果说后来的经济建设出了问题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在思想意识上仍然自觉低人一等”,恰恰相反,是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走向极端,轻视客观规律的结果。尽管后来的人们为了改弦更张,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描绘的一团漆黑,并且放任敌对势力抹黑毛泽东时代,但是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并不因为后人的好恶、人为的描绘而改变。
二、中国古代是市场经济社会吗?
韩文用了大量篇幅,旁征博引,论证在古代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而且是发达的市场经济。这是作者立论的认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
作者根据〈〈管子〉〉的记载,“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证明“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还是根据《管子》,“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举出“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的例子,列举了当时着名的大商人范蠡、陶朱公、弦高、吕不韦等人,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
当然,自秦汉以后,市场经济的发达就更不得了。
但是,作者显然是把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和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了,或者说他把交换、交易行为牵强附会地说成市场经济了。这使我联想到一个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某个地区的领导听说要实行市场经济,就部署说:我们地区要有计划地建设几个大市场。原来这位领导根本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以为多搞点买卖东西的场所就是市场经济了。纵观韩文关于古代市场经济的描述,我觉得作者和这位领导犯了同样的错误。当然作者不是不懂,而是为了论证他的历史观,故意牵强附会地将交易行为混同于市场经济就是了。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的源头追溯到货币产生以前,追溯到原始社会,因为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交换行为,尽管在那时还只是偶然的、实物的交换,但既然是交换,就具有交换的一般性质,因此也可以把原始社会说成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了。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
市场经济必定包含交换、交易的行为,必定要在市场上将产品实现为商品。没有交换、交易行为,就没有市场经济。但是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不是市场经济,却不能仅仅根据有没有交换、交易的行为,不能因为存在大量的交换、交易行为就断定这个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总之,不能把交换、交易行为,把市场等同于市场经济,
什么是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着眼点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例如人们通常着眼于资源配置与调节、生产力运行形式等角度定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或本质。但是无论怎样定义,人们所谈论的市场经济肯定不是简单地指交易行为的存在,而是市场对社会经济已成为一种支配力量,处于社会经济运转的主导地位。简言之:生产的目的必须是交换,劳动产品必须成为商品。
交易行为是市场存在的条件之一。但要形成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工的普遍化。韩文说:“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是啊,产权私有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自不待言,但是分工却不是简单的“存在”,而必须是普遍存在;交换也不是简单的存在,而必须是作为生产的目的而存在。没有普遍的社会分工,所谓市场就只能是零散的、简单的交换行为,能够转化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只能是少量的。这种交换行为无论多么繁荣兴旺,都不足以称之为市场经济。而社会分工的普遍化,只有在工业社会才能实现。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生产的分工既不普遍,也很简单,所谓城市,也只不过是交换行为的比较集中的场所而已(“市”和“集”一样本来就是交易场所),远远谈不上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中,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消费,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所占的比重很小。尽管在从自然经济向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是接近自由经济,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所占的比重越大,但是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全面改变生产的目的。在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生产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的,需求旺盛,生产就旺盛,需求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而在自然经济中的情况恰好相反,生产发达,可以用于交换的东西才丰富,市场才发达,生产对需求的刺激远远大于需求对生产的刺激。在韩文所谓的市场经济中,我们看不到激烈的竞争,以及由竞争所带来的生产的进步。
至于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社会运用市场的机制来调节资源的流向等等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更谈不上了。
韩文为了证明中国古代存在市场经济,特别指出当时存在的土地和劳动力买卖。“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并据此把地主也划归“商人”之列。可是,韩文完全忽视了所谓土地买卖的具体情形和条件,完全从“买卖”的行为本身出发来看问题,在韩文看来,买卖土地就像买卖衣服那样,就是非常单纯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般的交易过程。
土地买卖是怎么回事?如果稍有常识,如果哪怕只是简单地考察一下古代甚至是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农民出卖土地的情形,就可以了解,土地买卖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所谓土地(生产要素)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绝对不是多余的东西,可以“任意买卖”的。如果农民不是走到了绝路,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就绝对不会出卖土地——出卖土地的时候就意味着走到了生死的关口,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饥寒而亡已经顾不上长远的生存;而地主收买土地,则是趁火打劫,聚敛财富,掌握农民的命脉以便更加残酷的剥削他们。这种所谓“交换”既不可能是等价的交换(因为买卖双方根本不在平等的地位上,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是买方强势,卖方弱势),也不可能刺激生产,发展生产,相反,失地农民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即向地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亦即被韩文纳入“市场经济”概念的“劳动力买卖”),其积极性将大打折扣。在这里,绝对不像韩文所说什么生产资料的市场交换,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那般美妙,因为土地没有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商品,这根本不是市场,不是经济活动,而是地主对农民的盘剥、赤裸裸的聚敛财富而已。与其说这是经济行为,不如说是地主对农民的强取豪夺更准确,这种所谓“交换”,浸满了失地农民的血泪,是农民到了如果不出卖土地和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的地步的被迫的选择。至于把地主当作商人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商人”如果不是指交易双方,也应该指卖方才是,而且卖方必须盈利;如果土地交易中存在商人,那么出卖土地的农民才是商人,地主不过是消费者而已,可是农民并不盈利——何等混乱的逻辑!
韩文指出:古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这是正确的,尽管作者故弄玄虚地把“土地”说成“生产要素”,毕竟他指出了一个事实:所谓重农抑商,主要就是抑制土地兼并。但是作者把这当作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控,认为这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且以较长的篇幅论证了在这种干预下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地主、商人都可以称之为资本家,这就值得商榷了。如上所述,土地买卖活动根本就不是经济活动,因此国家所干预的就不是经济,只是干预地主对农民的盘剥程度,聚敛财富的程度而已,重农抑商的目的也很简单:抑制两极分化的趋势,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平衡,不使农民陷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从而危及统治者的江山社稷。因此,重农抑商政策在本质上不是经济政策,而是政治政策。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调控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只是在发展到了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的时候才由国家实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阶段,直到韩文所提及的“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的时候,资产阶级是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甚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被当作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只是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威胁下,尤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的教训下,资产阶级才普遍认识到并接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由市场经济才发展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阶段。着眼于经济来说,国家干预经济在本质上是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反制手段。
当然,中国古代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长期稳定、平衡的社会生活环境,使得现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得到有利条件和环境,于是生产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发展),人口增长,剩余的劳动力分流到其他行业也就多了起来。这就是韩文所说的市场经济的繁荣。但是恰恰还是在重农抑商的政策禁锢下,加上体制结构的稳固性,这种繁荣终究没有导致生产目的的根本转换,不可能产生竞争和竞争的压力,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技术,也就不可能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强烈要求,而且自然经济中的生产方式并不要求(起码是不强烈要求)劳动者发挥创造性——这大概就是韩文百思不得其解的“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的答案,重农抑商政策下不可能导致市场经济,在重农抑商政策尚能容纳生产力时,是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的。
综上,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即使在每个朝代的后期,市场经济已经得到相当的发育,但市场经济也没能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生产的目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自然经济的社会。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秩序,逐步增加的劳动产品必定越来越多地涌向市场变成商品,造成竞争,导致市场经济成分的量的增加,最终导致质变,引发工业革命,自然地而不是被迫地走向市场经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