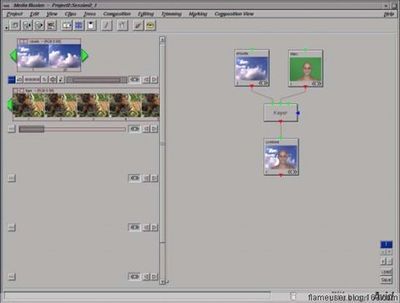文:烟波人长安
从小到大,我爸给我最多的评语是三个字:太浮躁。
小时候让我练字,庞中华字帖,我练了一年,一本书练去一半,说练好了,吵着要学别的。也确实练得还行,一笔一划像模像样,他没法儿说什么,放我去学画画。后来字越写越倒退,我振振有词,说数字时代了,以后没什么写字的机会。这直接导致我现在一拿起笔就犯怵,写出来糊涂花脸、除了我谁也认不出来,甚至我自己过两天都认不出来。老人家冷眼旁观,说,该。

画画也没学好。素描刚学会就想学水粉,水粉刚入门就琢磨升级成彩墨,后来按步骤该学油画了,我觉得油画没大用,从画画班退课。现在再看基本上等于什么都不会,六年就只熟练掌握了怎么从各种角度画静物石膏,连人脸都画不明白。出门从来不敢说自己是学过画画的人。老人家还是冷眼旁观,说,早就猜到了。
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也一样。看书从来都是看个乐,脑子里装了一堆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的书名,没有一本看到结尾。大学专业英语,没好好听过课,瞎看了不少通俗小说,混到一张专业八级证书,再也不肯上学,急着毕业出来工作。现在看见不会说中国话的老外就紧张。老人家知道了,叹口气,不说什么。
他自己不浮躁,还聪明得很,五年的医学课程,三年就啃得七七八八,现在管着他们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当年的教材还存在家里,翻开里头全是密密麻麻的笔记,也不知道买个本子。他炒股炒了快二十年,里头的条条框框门儿清,我看见那些K线图就头晕,他抱着个电脑,看得不亦乐乎,关上电脑就和我吹牛逼,说又赚了钱。
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对毛笔字有兴趣,买了一大卷宣纸回家。我写作业,他在一边写毛笔字,说要监督我学习。我作业写完,偷摸看了一个小时闲书,一转头他还在吭哧吭哧地重复同一个笔画。我嘲笑他钻牛角尖,被他一顿好打。过一年,他写毛笔字已经能形神兼备,我?我假装看不见。
我初中的时候,他们医院搞电脑化办公,他这种平时开电脑只用来扫雷的,要从头开始学Word、Excel、PPT。我都学过,在一边指指点点,嫌弃他手慢,气得他把我赶出书房,不准我说话。后来他用Office办公的水平超过了我。我报了计算机竞赛班,因为看不懂编程语言中途放弃。他还拿我的教材研究,说这么简单的东西,我笨得简直不像他生的。
我高中住校,和他交流变少。一周见一次面,主要任务是要下周的生活费。没人管,有段时间成绩水平稳步下落,他着急,拿他自己当年上学的光辉事迹教育我,炫耀他文理通吃。我不信。但他如今还能帮楼下邻居家孩子辅导高中数学,会修电灯,会检查水管,还记得莫泊桑的老师是福楼拜。我也学他在租的房子里修水管,把阀门拧断了,赔了房东一百块钱。
有一回我们俩回家,谁也没带钥匙,老房子,他拿了个身份证把门顺开。后来我自己在家,我们邻居忘带钥匙进不了自家门,我也学他,用水浒英雄卡给人把门打开,结果把邻居吓得好歹,认定我这孩子有问题,过半年就搬出了小区。
反正他那些真本事,我一样都没学会,只对旁门左道感兴趣。但凡他有心思研究的,我都玩儿不过他。他手机上有个游戏,我碰十分钟准死,老人家能不吃不喝捣腾一下午,最后手机不高兴了,死机来向他示威。从小和他下军棋、象棋,让我一组车马炮,我一样输。去年过年回家,我又要下,使出浑身解数,最后还是平局。后来我找到了打败他的办法,兴冲冲地抱着一盒棋子去找他,说,老头子,我们来比围棋。他翻个白眼,不理我。
我所有的启蒙都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家里书架上摆着很多书,从《唐诗鉴赏辞典》、《羊脂球》到《厚黑学》、《古代军事大全》,横跨天上地下。他让我选一本看,我挑了一本《古国奇遇记》,本来以为是童话冒险故事,结果发现是编排《西游记》,写得怪力乱神、屎尿屁横飞。别的没记住,只对唐僧蹲厕所、臭味儿从手机里传到唐太宗的鼻子跟前有很深的印象。看完我跟他邀功,给他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床响。夜来风雨声,多少光棍想”,被他一脚踹出去两米远。
打那以后他就不让我碰他的藏书,带我到书店买书看,从《汤姆·索亚历险记》开始,一直看到《呼啸山庄》、《平家物语》。他选书有他自己的理论,名著也要分出三六九等,《飘》不买,说看完把人变得磨磨唧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砍掉,说浪费时间。他喜欢历史,连带的我也开始看《上下五千年》《世界通史》。后来我看书有了自己的喜好,经常和他在书店一泡一下午,有一次买到了一套精装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不知道译者是谁,但水平极高,现在再想找这套译本,已经找不到了。到今天说起来我们俩都乐,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
但是现在我离他越来越远,不只是距离上,也是精神世界上。我搞互联网、做运营、玩儿自媒体,他不怎么懂。我用微博看新闻、用支付宝付款、买一圈抽纸还要上网下单,他很难理解。每次回家,我拿着手机,开着电脑,旁边平板充着电,他说我像个机器人。不过他对我的平板很感兴趣,只要我不用,他就拿过去,打开视频网站看恐怖电影。三番两次,我没办法,给他买了一个新的,他嘴上说不用不用,头一天就研究了一晚上。我手把手教他怎么设置账户、怎么下载APP、怎么关掉后台闲置的程序,得意地和他说,老头子,你的时代结束了。
他举起拖鞋,作势要打我。
我们见面的频率,从高中的一周一次、到大学半年一次、再到如今一年一次。我每年都会变,而他已经不怎么变化,像一座山脉长到顶点,顺势成为了一片高原。过去我和他一起看同一套书,比谁看得快;一起看球赛,半夜喊得山呼海啸,我妈在卧室敲门抗议;一起去路边吃馄饨,他吃大碗,我吃小碗。现在我有自己的事要忙,他也有他的事要忙,话少,他看他的《翡翠鉴赏》,我看我的《红拂夜奔》,他看足球,半夜,我看篮球,上午,我吃馄饨要改大碗的了,何况他也开始嫌路边摊不干净。
不过他的地位还在,我过了他说东我准往西的年纪,有些话也认真地参考他的意见。以前我从觉得我比他强,现在觉得,如果让他一夜年轻二十岁,混得肯定能比我好。
他依然保持着他的作风,依然想一言九鼎、不容置喙,想说了算。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找工作,他急冲冲跑来北京,托关系让我进电视台,我被电视台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搞得差点儿崩溃,自作主张跑了,去做兼职、审字幕,最后自己找一家公司上班,工资只够交房租。他电话里骂我一顿,第二天让我妈给我转了两千块钱。我上班三年,最近要换房子租,他老人家又坐不住了,找了一个认识的、在北京的亲戚,说要帮我把关。我说你儿子我好歹二十多岁了,房子都租过三回了,咱们不折腾别人了行吗?他说,怕你被人骗。
我在电话里嘚瑟,说能骗你儿子的人,这会儿估计还没生出来呢。
他在电话那头不轻不重地咳了一声,吓得我赶紧挂了电话,联系那个亲戚。
当然最后也没出什么幺蛾子,亲戚匆匆来又匆匆走,临了嘱咐我,给你爸打个电话,他肯定担心着。我打了,老人家嗯嗯啊啊,没说几句,感觉他心里很舒坦的样子。
挂了电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他眼里,我大概永远都是个孩子。
而在我眼里,他永远都有威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