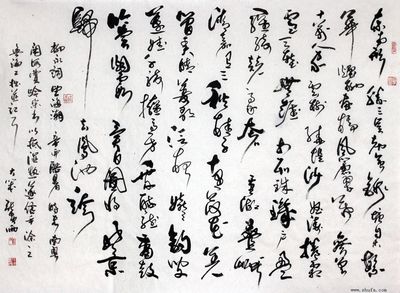易安词论云:“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然词语尘下。”易安此段词论介绍了柳永词的新编的背景和结果,也指出了柳永词在当时风评标签为“尘下”。给柳永打造了一种非主流变奏的民谣歌手的感觉。柳永不仅是北宋词史上产量丰富的一位词人,更重要的是,他让词这种体裁得以完备。
当词被称为“诗余”的时候
自中唐大事件“安史之乱”之后,战乱摧残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人们为了寻求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安慰,于是纷纷开始拒绝盛唐气势恢宏的诗篇,转而倾诉自我和心灵的焦灼,于是,“软性文学”应运而生。再加上民间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到了宋朝,人们有了消遣、娱乐的需求,那时候词还叫“诗余”,颇见词之地位实在是难以登堂入室。从形式上看,这时候的所谓词,诗歌的痕迹非常明显,实在是和诗歌这种题材傻傻分不太清楚。唐诗讲究的平衡和对称,“诗余”仔细效仿鲜有违抗。字数上,不是五言就是七言,要不就是五言七言的组合,甚至连句读都还是原先的模式。而市面上最畅销的“诗余”集子是“花间派鼻祖”温庭筠的《花间集》,王孙公子沉醉于舞榭歌台,纸醉金迷,儿女情长,最最喜欢的也是婉约细腻精致的“花间派”。此外,另一大家韦庄却以其清理质朴的文章特色打开一番天地。直至柳永响彻文坛之前,词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番情况。
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而柳永词里就没那么多规矩了,人家是“奉旨填词”的柳三变,穿着有阳光味道的白衣长袍逍遥于舞榭歌台,好不热闹。虽然尽是风流,也有命途多舛的愁苦。于是,四言、六言,甚至二言、三言、八言长句,都可以随心情停停走走,这样一来,词就有了应该有的样子——长短句,也就是词的结构。从此、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起来。不仅如此,柳永还自创了大量的新词牌,是因为旧词牌发挥不开,索性创造新的自己用。

比如《甘草子·秋暮》:“秋暮。乱酒衰荷,颗颗真珠雨。”还有著名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可以小清新,也可以很有气势做御姐,是不是自由了很多。是的,词在柳永之后,因句式的灵活,可以表达更多的内容,可以寄寓更复杂的情感,描物体态,也可以更细致。
而我们前文提到的句读,也就是断句,也有了一番变化。柳永词常用一字引领下片,少则一句,多则整篇,呼之欲出,妥溜畅达,又兼长短音律顿挫,读之吟之,如聆天籁。感受一下代表作《望海潮》:“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像在简单介绍景物,却又那么的有文采。因此,柳永使词真正的成为了词,而他也在填词的过程里实现了真正的自己。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那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台阁吃皇粮的文人形象,亦不同于怀才不遇满腹哀愁的文人形象,而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端着酒杯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
既然花间词也主力描绘声色霓虹,那柳永的歌舞楼台有何不同?还是因为,柳三变写的是自己,词里的主人公就是自己,不论是羁旅行役,还是万千愁绪,都是一种自我化,不同于以男子口吻代替女子抒发闺怨的花间词。柳永是将自己和歌儿舞女们,一视同仁了,我们都是因为有缘才相聚,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的欢乐就是我们共同的欢乐,柳永比花间词派的词人们,更能写得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还有自然风物的天真未染。
比如《采莲令》送行的和被送的两者的角度,都在词中了。好像离别之时柳永就站在“隐隐两三树”后面那般,很有参与感。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口兵]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柳永《传花枝》)”
最后的最后,柳永病逝,是歌儿舞女用AA制为他殓葬,但这丝毫没有损害这位词人的清誉,反而,他一直鲜活温和地,在词史中做那骄傲的一抹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