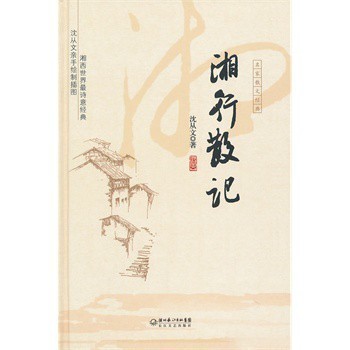小时候,我时常在内心里抱怨为什么我的成分是地主而不是贫农。即使不是贫农是个中农也好,因为中农是团结的对象,而地主是斗争的对象。
我不是抱怨我的爷爷奶奶,我没觉得他们是坏人。特别是我的爷爷,是一个有文化的庄稼人。他曾在故乡的村子里教过两年小学,是个很尽责的老师。后因分家,家中无人理财才辞去教职。他在种地的同时经营过油坊和酒坊,成为一个乡村工商业者。土地所有者兼工商业者的爷爷是一个从不与别人争吵斗气的温厚的人,常常教导他的子孙们万事忍为上。忍让成了我们家族的性格。我也不是抱怨我的父母,他们一个是中学教师,一个是小学教师,都是少年上学,青年出来工作,也不是坏人。特别是我的父亲,秉承爷爷的性格,是个谦恭的儒雅君子,从来没见他有过高声言语的时候,甚至没见过他发过脾气。不过他的一生中有过一次例外,那就是在一次造反派的斗争会上,他被当时会议的气氛所感染,终于血冲脑门,把派人到处调查,试图把他打成地主分子赶回老家的校革命委员会主任揪上台亮了相。这是他一生中干的最重大的事件。后来,他对此后悔不已。
我知道出身不可选择,但我当时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我?这其实是个无解的问题。虽然无解,但我却反反复复地想,怎样才能揭掉自己身上这张地主成分的皮。
“文革”开始后,我所上学的小学校里也闹翻了天。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每个班都贴出了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我们六年级一班也买来了笔墨纸张,有的同学在打草稿,有的同学在抄写。这当然不会有我的事。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看一本科普读物。这时中队长走到我跟前,大声对我说:“你被停课了,以后不要到学校里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收拾好自己的书包,走出了教室。我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晃荡,不愿回家。家里也没有人,奶奶作为地主分子已被遣返回邳县老家了,父母都在学校里写检查。我走到一堵教室的山墙前,看到上面贴着批判我母亲的大字报,我一张张地看,也没看到有什么重要内容,只是说母亲有资产阶级思想,烫了头,穿高跟鞋等等。正看着,我又听到一声断喝:“让你走你怎么还不走!”我看到中队长满面怒容地站在我的面前,两只拳头紧紧地攥着。我不能再在学校里赖下去了,再赖下去,拳头可能就要挨到头上。于是只好怏怏地走开。平日里,我和中队长关系挺好,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时常和他在一起开班会。现在“文革”刚刚开始,一向比较温和的他就变得凌厉暴躁,如一只好斗的小公鸡了。人的改变真的很快啊!六年之后,我留城参加了工作,分到了一个小厂。没想到进了厂就碰到了他。原来他没上初中,已在这个厂干了三年了,我们又成了工友。关于撵我离校的事,他没有向我道歉,或许他早已忘了。他出身一般,在厂里不得志,工作中同我相处和睦,我心里过去结下的疙瘩就慢慢地化解开了。
奶奶被遣返回了邳县老家,心情郁闷,生了病。父母让我背上十余斤面粉步行三十里回老家看望。我先乘船渡过大运河,然后沿乡间小路往南走。快走到车夫山公社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后面追上了我,放慢了脚步与我搭腔:你这小孩上哪去?
我扭头看了看他,见他不像个坏人,不会抢我背着的面粉,就回答道:去梁口。
怎么没上学啊?他又问。
我是被同学赶出学校的,已没有权利再上学,但是,这些事情,能对一个陌生人说吗?说了会是什么后果?不能说实话,我只能撒谎。学校停课了,搞运动。我回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说谎。我的心里很慌,声音也有点打颤。奶奶一直教育我,做人要诚实,不能说瞎话,可是现在我不能说实话,只能说瞎话。我已万劫不复,堕入深渊了。
你家是什么成分?他又问。
他哪壶不开提哪壶,一下就接触到这个敏感问题。听他这样问,我的心里很烦很烦,我家是什么成分,碍你什么事呢?
“中农。”我回答。为什么说是中农而不说是贫农呢?十二岁的我为什么不敢把自己的成分说为贫农呢?现在想来只能说明那时的我有一种心理障碍,不敢高攀伟大而高尚的贫农成分,只敢和团结对象的中农扯上点关系。
“中农?”陌生人沉吟了一下,然后说,“中农成分不好不坏,一般化,但入党、参军都不大行。”
我转脸仔细看了一下他,他年纪三十多岁,皮肤黧黑,脸瘦削,是个正儿八经的农民。但他却对党的政策了解得那么透彻,分析得那么到位,真让人吃惊。看来他属于农村政治家一类,是个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
对他的话,我只是“唔”了一声,没有再接着往下聊。他已将我的情绪打击到了冰点,我同他还有什么话说?又走了一里多地,他该拐弯了,我同他淡淡地道了别,他拐进村庄里面去了。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我的心里很不好受。
十八岁我留城干工时,区劳动局发下一张表,上面有家庭出身一栏。我无可奈何地在上面填上了“地主”二字,但同时我又怀疑这样填写的正确性。我的爷爷有四十九亩地,因父亲在外上学,他雇了人帮着种,剥削了长工短工,按政策他应被定为地主分子。但父亲自幼上学,1948年淮海战役后开始教学,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本人成分是学生。我出生于1954年,父母是教师,不是地主分子,我为什么也要填地主呢?我为什么不能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教师或自由职业者呢?
某一天,我下了班,带着这个问题我去找了当时的教育科曲科长。区委大院里我只有他一个熟人。他曾是我的小学校长,我母亲的同事。我上一年级时,他最喜欢用他的胡须扎我,经常把我扎得嗷嗷乱叫。
见到长大了的我,他没有流露出一点热情,也没让座,就让我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把我的问题讲完。然后,他表情严肃地问:是你妈妈让你来问的吗?听了他的话,我心中一惊,他问得分明不怀好意。我说不是,是我自己想问的,我入团要填表(其实我哪有什么团可入,厂里团支部的几个人根本没有要我加入的意思,从没找我谈过一次话。在他们眼里,我是另类。我从十八岁进厂,到二十四岁考学离厂,六年时间我从未写过入团申请书,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听了这话,他板着的脸有些缓和。他站起来端起茶杯去倒水,然后说:这事不属于教育科,你可以找一下区里的宣传部门。听了他的第一句话我已经后悔了。我不该来找这位昔日的曲校长。他已不是那个逗着我玩用胡须扎我取乐的曲校长了。他已是一位政府官员。而我也长成了一个想问一下为什么的青年。我们之间是政治关系了。我心中懊丧,扭头走开。他可能也觉得回答有些不妥,连声喊着我的小名,并起身送我。我没有回头,一直往外走。我让他尴尬地站在办公室门口,只能看到我已健壮起来的背影。
虽然我很生曲科长的气,但他毕竟告诉了我打探的路径。区里的宣传部长姓高,区里开大会的时候我见过他。高部长个子高高的,白净面皮,有点知识分子味道,人也和气。他的夫人在商店做售货员,人也很和气。但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呢?那几天,我下了班就在区委大院里转来转去,幻想着能碰到高部长。我想高部长水平高,肯定会给我一个很好的答复。如果把家庭出身改为自由职业者,那就是有了出头之日了,我也就可以入团入党参军提干,走一条有前途的光明大道了。前途是个极有诱惑的字眼,谁不想有个前途奔个目标?我也不能总是站在切纸机前一刀一刀地切个没完没了吧。一连等了四五天,我都没看到高部长。那天我正沮丧地从区委大院往外走,刚出大门,不想迎头碰上了高部长。我鼓足勇气喊了他一声。他愣了一下,没有停下脚步,问道:你有什么事?我追上他说,我想问一下成分的事。
他继续走:什么成分?
我慌忙告诉他:我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个人成分是学生。我的家庭出身还填地主,我觉得不合适。我以为应该填教师或自由职业者,不知道这样填行不行。
他没有回答我,因为已经到了他家门口,他掏出钥匙,打开门进了家。他没有邀我进家,我只好站在门口等。他家住三间西屋,青砖黑瓦的老房子,玻璃门窗。房门口有一个自来水管和洗菜池。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走出来,锁上门,又往大门口走去。我紧跟着他,等待他的回答,但他却一直不说话,就让我像秘书一样跟着。出了大门,他站住了,看着我说:你问的问题现在没有新文件,原来填什么现在还那样填吧,好不好?我还有事情,我走了。说完,他手里托着那包东西往东走去。
人还算和蔼,没有像曲科长那样不怀好意,一下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他告诉我没有新文件也是实情,新文件要等邓小平来制定。把地主富农出身一律改为社员,那还要等八年,要到1980年。那一年,当我握着笔在一张表格上郑重填上社员时,我总会想起高部长。最起码他没有怀疑我的目的,也没有训斥我,而是平等地同我说了几句话。尽管我没有找到真理,但也没有被当成坏人对待。而且,他也没有教导我“要重在政治表现”之类空话。重在政治表现,那都是骗人的把戏。我在那台温州产的老掉牙的切纸机旁干了六年,出大力流大汗,年年被工友们评为先进工作者,但既不能入团,也参不了军,提不成干,只能眼瞅着身边的工友一个一个上学、提干、当兵。而我,两眼茫茫,看到的只是切纸机后面的白色墙壁。那些上学、当兵、提干的工友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同我道别。他们知道不能来,我也不希望他们来。六年后,高考恢复,我考上枣庄教师进修学院之后,郑重其事地向一个个工友道别。这些工友都是好人,六年来没有人欺负我,没有人蔑视我。一位姓庞的大姐拉着我的手说,化乐,你走了,我们还得干下去。听了她的话,我不禁有点愕然。是啊,生命在一天天的工作中消亡,当成分不再成为心灵的压力,我们将面对的是生存,是为什么活和怎样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去问高部长,只能问我们自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