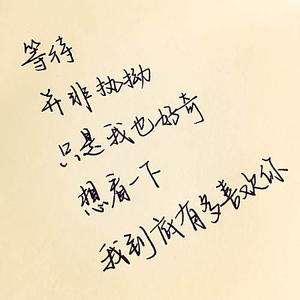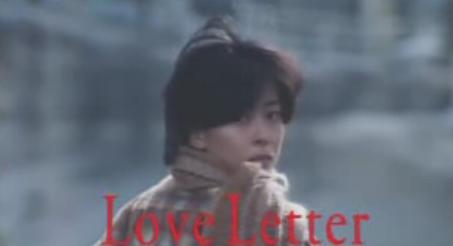本文转载自山路幽静《(原创)军嫂的苦乐年华》
一顶军嫂衔头的凤冠,伴我走过三十余年风雨路,回首间:岁月斑驳了时光的齿轮,填平了年轮的千沟万壑,漂白了一颗清纯少女之心,苍老了一段苦乐交织的生命年华,演绎了一场与军人联姻的活报剧,留下了一本堆叠厚厚的记忆相册。
翻遍军语词典,却查不到“军嫂”一词,军嫂本不归属军队,因与军人的一纸婚约,改姓为“军”,此后,军人、军队便分别成为她的丈夫和婆家,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和联系。军嫂,是军人背后的一座山,一座陡峭崎岖、蜿蜒迂回,且风光秀丽、延绵不断的青山;是一本用生命谱写的诗歌,一本镌刻着艰苦相携、寂寞为伴,且抒发着“婆家”昌盛、小家平和的圣贤书;是一个温馨和煦的港湾,一个军人赖以歇脚补氧、修身静心,且荡漾着温暖、洋溢着欢欣的避风港。
当一个女孩选择军人为夫时,便开始品尝寂寞、独守、思念、牵挂、期待的味道,意味着从此以后,她们将始于一种与常人绝然不同的生活之路,而为之付出青春年华、靓丽容颜,绝缘浪漫与鲜花。同为女子,她们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丈夫怀中的金枝玉叶,遥遥无期的两地生活,赐予她们一把精神枷锁:耐住寂寞、承受磨难、学会坚强、忠贞守望。长达三年的恋爱,我们情系书信,相聚不过四次,婚后九年,兵分两地,隔河相望,缺失了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琴瑟和鸣痴痴昵昵,无数个春夏秋冬,穿越时空隧道,只为短暂的相聚;无数个白昼黑夜,当娘又当爹,独自抚养儿子,熬红了双眼,累垮了身体。八四年的中越反击战,一年半的别离和牵挂,给以身心健康致命的摧残,留下的阴影,殃及一生......忘不了,只身赶往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军营,于一个临时来队军属的四合院,一间墙皮剥落的小黑屋,两张木制的硬板床,一张破旧的三屉桌,两条绿色的军被的地方完婚,升格为军嫂;忘不了,没有丈夫的陪伴,经受孕吐、先兆流产、艰难生产煎熬,生下儿子,并在儿子百天后,坐着硬座,历时四天,中转签票,去部队探亲,那一路的艰辛和劳顿;忘不了,在观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时,正值丈夫在离友谊关七公里处的宁明机场经历战争炮火,音信全无,终日胆颤心惊之际,触景伤情,珠泪纷飞,湿透了衣衫,黯淡了心境......
无休止的付出奉献,长时间的离愁别绪,生活的导航仪并没有偏向军嫂。随军、迁徙、安置、落户、就业,让军嫂失去了原有的事业辉煌,归零重启,无疑又是一次损伤。记得九零年随军来京,为谋求一份职业,东奔西波,甚至还曾依照招聘信息去应聘面试。后通过关系,找到国家劳动部某处长,见面时,她一脸惊诧地问道:你是军嫂?我答道:嗯,是的。她更为诧异:你和我想象中的军嫂差距甚大......之后的沟通,方才找到疑问所在:军嫂,在常人眼中,是穿着大花袄的村妇、家庭主妇,她们没有文化,没有素养,没有气质,是依附于军人的衍生物!少顷,悲从心来,军嫂,莫不是除了忍受辛劳,还将蒙受人们的褒贬?这,难道就是军嫂的天命?
几十年的军嫂生涯,喜忧参半,苦乐交替,如此肤浅、粗糙、简要的文字,不足以表述漫长的军嫂岁月。回眸往昔,有时也需要勇气,这篇拙文,用泪水编辑而成,渐远的伤痛,一次次被揭开,那份痛,无以言表,刻骨铭心......军嫂,不求同情,只求理解。如果,当各位在生活中,偶尔想起这样一群女子,她们是平凡的化身,她们是贫穷的后代,但她们的精神是富足的,她们的人格是高尚的,请给予这群女子:温和的笑容、平等的尊重,这些,与她们而言,已经足够,真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