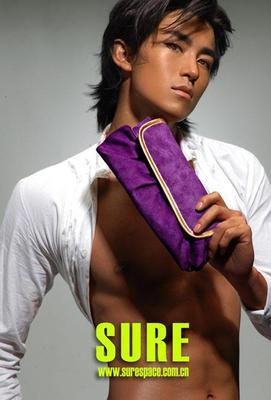我的这个邻居姓杨,大名叫杨生根,队里没多少人晓得他叫这个名字,只知道他属龙小名叫龙锁。他还有个诨名叫杨瘸子。其实他并不瘸,只是走起路来有点儿外八字(听说是胎里带,生下来就这样),大集体时,男人们天天在一起干活无聊时便相互打趣,差不多每个人都有绰号。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倒霉的绰号,害得他到了二十七八岁还没能定下一门亲事。
龙锁有三个姐姐,他是老小,又是家里的独子。他爹走得早,刚解放没多久还在单干时,才五十多岁就撒手人寰,听说是因为挑苏北灌溉总渠时落下的痨伤。其时,龙锁的三个姐姐已经出了嫁,龙锁才十岁。是妈妈带着他过着孤儿寡母的艰难日子,把他拉扯大。因此,龙锁没上过几年学,先是替农业社里看了几年牛,后来人民公社了,就成了队里的大劳力。三年经济困难那会儿,龙锁的妈妈在黄海边上的“海里”讨了几年饭。每隔十天半月都要步行四五十里路回来看一下龙锁,给他带一些讨来的玉米糁子和山芋胡罗卜之类的吃的。后来龙锁曾跟我说过,那几年要不是他妈讨饭他可能早就饿死了。三年大饥荒过后,农村的形势开始有了些好转,虽然吃不饱,但也不至于饿死人。妈妈把他照顾得很好,煮粥时总要存心捞一碗稠一点的给他吃,宁可自己喝薄汤。因此,龙锁的个子长得不算矮,国字脸上红朴朴的,见人一脸笑,力气不小,脑子也不笨,样样农活都拿得出手。除了走得快时一条腿有点那个,其它方面都挺不错的。眼看着人家的小伙子到了二十多岁就结婚生孩子,他妈妈心急如焚。
其时,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庄子上,龙锁有个比他妈小几岁的姨娘,姨娘家有个二十岁刚出了头的丫头,这姨表妹叫粉莲子,比龙锁小七岁。粉莲有三个哥哥,她最小,又是家里唯一的一个“丫头宝”,哥哥们从小都让着她,脾气有点儿任性。粉莲的三哥比龙锁小一岁,因为眼睛高度近视,至今也没说上对象,姨娘就想要女儿跟人家换亲让老三成个家,说的那个人家姑娘倒挺不错,就是哥哥有点儿不“玲珑”(半傻),粉莲死活不肯答应。姨父就劝老伴:“你就别再逼丫头了,我家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成了家,有了孩子,老三就先由他去吧,说不定将来碰到机会还能娶个半边人(指寡妇)”于是这话就不提了。
过了些日子,姨娘又问女儿:“你大姨娘跟我说过好几回了,她想要你嫁给龙锁表哥,如果你没意见,我就答应了。”对这个表哥,粉莲是再熟悉不过了,她觉得除了岁数大一点,其它倒也没什么不合适的,表哥忠厚老实,长得也还算过得去,她没说不同意就等于是认可了。事情定下来后,当年秋天就张罗着过了门。虽然那时的婚姻法已明令禁止表兄妹通婚,但农村中“亲上加亲”的旧习俗一时改不了,因为那时没多少人领证,也没人去制止。
杨家的老屋与我家隔一条巷子,大门对着大门,那时我还在生产队里当会计,大家都替龙锁高兴,这么大了,想不到还能娶到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表妹做婆娘。记得进门的那天,是个天高气爽的好日子,蓝天白云,秋阳高照。那几年,婚事都办得极简单,谈不上什么排场,都是亲戚朋友们撑一条稍大点儿的木船,船艄上面搭个临时棚子,就将新娘娶回来了,船靠岸时放几串炮仗,新娘便由“搀妈奶奶”的搀扶着,在爆竹声中缓步走进家门。那天,新娘子上身穿着一件“毛纶格子”(一种斜纹棉布,价钱大约是洋布的双倍,那时时兴这种布料,算是姑娘们的高档服装)夹袄,不松不紧地裹着她略显丰满的身材,曲线毕露,十分养眼。那时还不时兴化妆,只是在出嫁时要先将辫子改成髻儿,再用细线扯一下脸,(此前,姑娘家是不扯脸的所以叫“毛脸姑娘”)。门前挤满了看新娘子的闲人,都说新娘子“痛”得像观音菩萨(“痛”是方言,美丽漂亮的意思)。那天晚上除了招待家中的亲戚还多请了一桌客,庄上的大、小队干部正好凑了一桌,记得一桌只有两小并2两5的瓜干酒,最后吃的米饭里掺了许多剁碎了的胡罗卜。尽管如此,有肉有鱼还有罗卜饭管饱,对那时的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场盛宴了。
2
在龙锁结婚的第二年春天,他妈妈得了一种怪病,有时候,吃的东西咽进了喉咙,要好长时间才进得到肚子(胃)里。一查,是贲门癌晚期,医生说,至多还能活三个月。那时得了这病,是拿不出钱来作无谓努力的,只能回家等死。小夫妻不敢将实情告诉妈妈,一直隐瞒了两个多月,后来连很薄的粥都很难喝进去了。有一天小两口都上了工,我和我的那口子桂芬一起过去看她,她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像个半死的人,桂芬喂了她几口水,她说感觉到好像是流进去了,她告诉我们,粉莲要在家里陪着她,她不曾肯,她说她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省得队长三番两次地在门口喊。后来她还跟我们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话,她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得的是“老症”(过去农村里都将食道癌之类的病叫“老症”),我已经比他爸多过了十多年了,七十多岁死也不算短寿了,在最最困难的这些年,我将龙锁带大成了家,到那边去,对老头子也交代得过去了,唯一让我丢不开手的还是龙锁两口子,有我在,他们早上不要起早煮早饭,下工回来有现成的吃,农忙的时节,他们换下来的衣服也都是我洗,我虽然不上工挣工分,但我在家里养十来只鸡鸭,一年还能养一头大猪子,收入并不比他们少。我不在了,估计他们的日子不会好过……还有,龙锁这小伙太老实,他婆娘从小就娇生惯养,看样子还是个“油神”(方言,指不检点不安分),俗话说:“烈女怕闲夫”,我就担心将来龙锁管不住她。你们跟他门对门住,这些年对我家照顾得也不少,我走了,还要靠你们帮着点儿,如果出了什么事,要劝劝龙锁别认死理,让着她点儿,好丑都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将来有了孩子要将孩子养成人。”
她说完了这些话,好像力气已经耗尽了,就停下来泪眼婆娑地望着我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话安慰她,我就说:“婶,你别多想了,我看龙锁两口子还是挺有出息的,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好的。再说,我们两家的关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跟龙锁哥哥又是从小就一起长大的,就是有什么事,我们都会互相帮忙的。”
其实龙锁只比我大两岁,桂芬比粉莲大三岁,我们结婚早,当时我的大女儿已经两岁多了。因为我多念了几年书比他见多识广些,又是他的“父母官”,因此平时相处,倒好像我是他的大哥哥。
龙锁妈咽气的那天已是暮秋,队里正忙着秋播种冬麦。那时还是土葬,龙锁请人用一副床板和一扇老屋房门为给妈妈拼凑了一口薄皮棺材,又跟队里预付了些钱、粮,才将老人入土为安。
妈妈死后,龙锁两口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因为操办丧事预付了队里一些钱、粮,当年分红时没分到一分钱还倒欠队里几十元,本来口粮就不够吃,每月还要被队里扣掉一些,家里又拿不出钱来买青菜胡罗卜之类的代食品,每至月底都要断几天炊,那时候大家都困难,在粮食方面谁也帮不了谁,就是临时跟人家借一点,下个月分了粮也是要还的,否则以后就不好意思再去借了。后来我跟队长商量了一下,暂时不扣他家之前预付的粮,结果还是坚持不到月底,主要是两个大口扯不住,又没钱买代食品。提起钱,他家那时可真的是一文不名,妈妈得了病时就将一条半大的猪子卖掉了,现在连几只母鸡都养不起来,有时家里买一盒火柴的二分钱都没有,烧饭时都是拿一个草把到我家灶膛里过火,有时风大,点着了的草把在路上被风吹熄了,要反复好几回。
那时候,队里好像总有干不完的农活,主要是社员出工不出力,大家都是混日头混工分,因此社员们天天都要上工,而且天天都要起早带晚,天没亮时,队长就挨家挨户地叫门,先是叫人起来烧早饭,接着就派工、喊工,以前龙锁妈妈还在时,都是将早饭煮好了再喊小两口起来吃现成的,现在几乎都是龙锁煮三顿,粉莲从小就被她妈宠着,睡惯了懒觉,又因为是老夫少妻,丈夫都要把婆娘当孩子似的宠着。
那年冬天,每个队要抽出六七个大劳力上大型河工挑河,我跟队长说:“不如安排龙锁去挑河吧,工地上每天有一斤几两米的补助,还能补到几角钱零化钱。”后来龙锁果真去了。我原以为这样安排能够解决他家的粮食困难,哪想到我是犯了一个错误,那年冬天,粉莲在家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了。
3
龙锁走后个把多月后的一个晚上,桂芬悄悄地告诉我:“好像这几天粉莲有点儿不正常,龙锁刚走的那会儿,她三天两头往娘家跑,我还替她高兴,隔三差五地到娘家去混几天饭,家里的口粮就够吃了,不过这些天不往娘家跑了,老看到二侉子有事没事地往她家跑,有时捧个粥碗也要转过去搭几句寡话,不晓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听了开始并没在意,后来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果然看到了一个个子不高胖敦敦的黑影子熟练地撬开了她家的大门,反手又将门关上,人进了里就再也没什么大动静了。从那身材上看,是二侉子无疑。后来村子里也有人说,二侉子走了桃花运搭上了龙锁家的“痛”婆娘,两人正打得火热,夜夜不空房。据说这情况还是二侉子本人在外面“摆方子”(方言,显摆的意思)不经意间说出来的,已经成了村里公开的秘密。
二侉子也是我们队里的人,与我同龄,住在村子中间一处破败的大瓦房里,家里有一个三十大几岁的哥哥和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妹妹,因为他爸是富农,弟兄俩至今都没娶上媳妇。二侉子家姓陈,小名叫二小,小时候特别皮,十岁出了头时还光着屁股在巷子里跑,邻居们就都叫他二侉子。我们那里都把北方人叫“侉子”,将南方人叫“蛮子”,不过在地区划分上是很模糊的,我们家乡地处长江北边,有时也常被北方人叫蛮子,被南方人叫侉子。习惯认为,与儒雅文弱的南方人相比,北方人更剽悍豪爽一些。不过,这种称呼是含有贬义的,通常是指这个人既邋里邋遢又不拘小节。
这几年,二侉子倒是一点儿也不“侉”了,他有一套“相亲服”,穿起来仪表堂堂的,好像换了一个人。他年年都要相好几回亲,大都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谈几天就谈黄了。他本人的条件倒是挺不错的,中等个儿,胖胖的圆盘脸,人也机灵,干起活儿来从不卖奸,还是驾牛耕田的一把好手。让他觉得伤心的是,就连同是富农家庭出身的姑娘也都不肯嫁给他。其实也难怪,那时出身不好的人就是二等公民,干的都是些苦活脏活,工分给多给少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哪像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有时还敢对干部发发牢骚。
自从粉莲嫁过来后,二侉子的那套专门用于相亲的服装,就成了常服,有时男劳力与妇女一起干活时,他也穿得整整齐齐的,小分头也梳得服服帖帖的,与龙锁站在一起,就好像龙锁是他的大叔,有人说,他是穿给粉莲看的,他是在想她的心思。这次龙锁出去挑河,听说要到过了春节才能放工,客观上为二侉子攻城掠地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事实印证了龙锁妈妈的担忧——“烈女怕闲夫”,一来二去的,二侉子就得了手,而且两人都相见恨晚如鱼得水,轰轰烈烈得一发不可收。
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能帮到龙锁,这种事人家做得旁人却说不得,弄得不好要出人命。幸好桂芬与粉莲处得不丑,平时好像无话不谈,只能叫桂芬去探探虚实,顺便说说她。有一天晚上,桂芬在她家跟她谈了好长时间,回来后告诉我:“她倒是一点儿也没瞒我,外面的传言确是一点不假,两人已经好了个把月了。她说‘与龙锁相比,二侉子更会体贴女人,他日早日晚地粘着我,我就也动了心,现在要我跟他断恐怕很难。’她还说:‘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跟他在一起感觉就是不一样,好像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女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是觉得跟龙锁结婚一年多了,一次都不曾有过那种感觉。我也寻思过了,反正他也不容易找到人(对象),如果能瞒住龙锁或者他不计较,我们就这么扯着过,假如龙锁要责罚我,我就跟他私奔上江西。’”(我知道二侉子有个叔子在江西,五八年逃荒过去的,早就有了江西户口,现在在一个林场里当工人),听了桂芬的话,我觉得事态已经严重得超出了我原来的估计。很显然,粉莲是被二侉子的床上功夫征服了,也难怪,二侉子这么大了还是个处男,家里也过得不丑,龙锁历尽坎坷,活儿苦,生活上又有一顿没一顿的,那个方面怎能与之相比?
后来我直接找二侉子训了一次话。我说:“你这是破坏人家家庭的行为,人家可是贫下中农,你出身不好却还这样胆大包天,还敢在外面嚼舌头摆方子?你也不怕龙锁回来会打断你的腿?还有,万一丑事传开了,女方寻死觅活地出了人命,这责任你怎么负得起?”二侉子被我连珠炮似的发问吓蒙了,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他慌忙表态:“我听你的,我保证改。”我虽然知道他言不由衷,但也只是希望他收敛一点,把事情做得隐蔽些。后来我听桂芬说:“从被你训过后,去得没以前勤了,而且总要等到庄子上定了人脚才敢悄悄地过去。”在外面,人家跟他说笑时,他也矢口否认,说以前是他瞎说着玩的,绝对没这回事。
4
龙锁放工回来时已经过了正月。憨厚老实的他一点也没发现家里有什么异样,还给粉莲带回了一件裤子料,那是他用他在工地上省下来的零花钱买的,他不抽烟不喝洒,没什么开支,那点钱别人大都不够用,工地上的伙食太差,除了饭粥,一天只能吃到一大碗在大锅里沤熟了的青菜汤,别的人隔三差五的会买点儿肉碰头(聚餐),他舍不得,活儿又重,因此他回来时显得比别人更憔悴些。不过,毕竟久别胜新婚,他们也还年轻,自然会有好几天激情澎湃的日子。
过了个把多月,粉莲害起了宝宝(我们那里都把妊娠反应叫害宝宝),队里婆娘们就在私下议论,也不知道是龙锁的还是二侉子的,议论的结果是:管他是那个的,反正照田收庄稼,生下来总归是要跟龙锁姓杨的。对此,龙锁却没一点犯疑,要当爸爸的感觉让他兴奋异常,一早一晚的像宠孩子似的宠着粉莲。
龙锁回来后,我又找过一回二侉子,严正警告他与粉莲绝对不准再有来往。后来,虽然还有点藕断丝连,但两人都特别谨慎,二侉子是怕“犯法”,粉莲也觉得对不起龙锁。古人将婚外恋情叫“偷情”,现在看来这个“偷”字确实是用得恰如其分。
那年夏天,二侉子也找了个人结了婚。是他爹妈做主,拿妹妹跟人家换的亲。那户人家也是富农成分,姑娘已经二十七岁了,一直不肯把人家,因为怕二十岁刚出头的弟弟将来寻不到人,特地留着为弟弟换亲的。这桩交易,看起来是双方都互不吃亏各得其所,但对二侉子这边来说还是不太划算的,因为那姑娘生得太丑了,虽然不麻不疤也样样活儿拿得出手,但脸上的下巴好像比常人短一截,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起先他是不同意这门亲事的,因为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难免会有曾经沧海的想法。后来经不住他妈反复开导,妈妈说:“我和你爸也是怕你犯法,想早点了却掉一桩心事,那小伙跟你妹妹也般配,就是姑娘的面貌不大好看,但我听人说了,那姑娘勤劳、懂理,手也不笨。你就别再犟了,婚姻是前世里注定了的。再说长得丑一点怎么啦,“痛”又不能当饭吃,老话还说:瘦田丑妻家中宝,美貌娇妻惹祸根。娶一个会过日子能生儿育女的人,我看挺好。”二侉子想想妈妈说的也有道理,这事情就成了。说来也奇怪,结婚后,小两口感情还不错,起先是看不顺眼,时间长了就越看越顺眼了,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说的就是这个理。过去,乡里人都这样,男女双方结婚前都不曾有过多少交流,他们之间的感情都是在后来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里慢慢积累起来的。从此,二侉子就彻底断绝了与粉莲的那种关系,有时候在上工的路上遇见了也没多少话说,只是二侉子会从粉莲那哀怨的眼神中读懂藏在她心中的千言万语,此时,二侉子就在心里对她说,我也舍不得跟你断,只是没办法,我这样做是为你好。
秋天,粉莲生下个白白胖胖的丫头,按时间推算,“早产”了个把月,也算是在常理之中,只是丫头那圆嘟嗜的小脸就像是从二侉子脸上剥下来似的,不过这只是队里的那些碎嘴婆娘们参详的,龙锁可一点儿也没往歪处想,高兴得好像是拾到了个宝贝。丫头出生时,他家院子的一角正盛开着一簇黄灿灿的菊花,于是他们就为丫头取了个乳名叫小菊。
那年秋天,我们这个生产队“领导”大换斑。先是我被调到村里任大队总账会计(原来的会计年老多病),算是“升迁”。后来,与我共了好几年事的队长被免职,表面上说他是年纪大了没领导能力,老好人一个,管不住队里那些邪头逆角的男劳力,队里产量上不去,工作没起色。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村支书想借机安排他的一个亲戚。这个亲戚是支书儿媳妇的哥哥,村里还有传言说支书“扒灰”,挺怕儿媳妇,儿媳妇交的任务,他不敢不完成。那时,支书免队长的职就跟过去地主辞退管家一样便当,虽然公社规定撤换队干部要经公社组织科审批,但一直没严格执行过,有的队长跟支书顶一回嘴,支书一句话就把他撸下来了。
新队长上任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作风,倒是真的镇住了这个长期后进的生产队。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慢慢地露出了狐狸尾巴。那人特好色,队长的特殊地位又为他的这种恶习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年,他搭上了粉莲,差点儿搅散了龙锁的家庭
5
新队长姓陆,叫陆凤基,因为此人特好色,人家在背地里都叫他骚公鸡。他不是我们队里人,到这里来当队长,也算是“空降”。全村人都清楚,他原来在他那个生产队里是出了名的邪头,常常闹得队长头疼,没法开展工作,又因为有支书护着,更奈何不了他,因此,队里私下里都叫他是“二队长”,还有人说“二队长是‘国舅’,比队长的权力大。”
陆队长比龙锁大两岁,没上过几年学,生得人高马大,打起架来心狠手辣,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他是家中的“惯宝儿”,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还在十多岁时就是家里的小霸王,姐姐妹妹们都没少挨过他打,对此,他妈妈不但不责备反而说他有本事,将来没人敢欺。
一开始,他敢于碰硬,不循私情,办事说话也还公正,原来队里的几个投机取巧惯了的邪头社员还真的被他镇住了,他谁也不怕,杠桑(方言:吵嘴)、打架他随时奉陪,有的社员说,队干部就要像这样有点“虎气”的。
不过,好景不长,他除了有点“虎气”外还有痞气,而且不是一般的痞。他在他原来的那个队里,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除了有两个老相好,有时还打打游击,他的婆娘被他打怕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平时在田里干活,也是没大没小的瞎胡闹,就连比他大十几岁甚至还是长辈的婆娘们都敢摸奶子捏屁股。他还在人前摆方子,总结他的那一套猎艳的心得体会,说什么“对姑娘家要猛,对婆娘家要哄”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所谓“经验”。
他刚来的那会儿,粉莲正在坐月子,那年冬天,龙锁又上了工地去挑大型,这主意还是桂芬帮他出的,桂芬对他说:“粉莲刚生了孩子,孩子又没人带,不如你再上一年河工,让粉莲带着孩子到她妈那里过一个冬天,明年开了春回来上工,把孩子丢我这里,我奶奶(其实是我的母亲,我们那里媳妇都将婆婆叫奶奶)反正又不上工。”那年河工放工早,快过春节时就放了工。龙锁两口子都说桂芬的主意不错,既解决了他家的粮食问题,又没耽误多少工分,因为冬天上大型一个男劳力差不多能拿到两个人的工分。
春节过后,他们两人都上工时,就把小菊跟我的二女儿一起丢到我妈妈那里,那时我又有了一个比小菊大两个月的二女儿,妈妈那时在家里同时还照看着我哥哥家的两个孩子,她还用一台旧缝纫机给人家做衣服,已经是够忙的了,但没办法,他家小菊没处丢。好在那时的孩子也不难带,小菊就整天躺在童车里,上、下午粉莲都要在干活休息时,急急忙忙地跑回来喂一回奶。平时也没人去抱她。那时都这样,俗话说:“哭不死儿伢,吊不死茄儿”,婴儿只要没病不饿,让他们哭会儿也没事。再说,丢在我妈那里总要比锁在家里放心得多。
夏天,骚公鸡打起了粉莲的坏主意。上工的时候,他那色迷迷的眼神,老在粉莲身上转,因为正值哺乳期,粉莲的两个大奶子越发丰满挺拔,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每回看到了都让他心动不己。在这方面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这回他采取的策略是慢慢地哄她上钩。他先是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对她进行感情投资。那时的队长也等于是家长,每个“家庭成员”今天干什么活,记多少工分,都是他说了算,绝对不能不服从分工。安排农活时,他都会将粉莲安排一些比较轻巧的,离庄子近一些的,工分却不比别人少,这样既可以少出些力,回家给孩子喂奶也少走些路。受到“照顾”的人会对这种人性化的安排十分感激。后来,对她的照顾又升了级,干计件的活儿时常常有意给她多记一些工分,甚至有时因事歇工,记工薄上也给她记出勤。次数多了,粉莲也就猜到了他的心事,他这么一个绰号叫骚公鸡的“好人”如果不是图她的身体,他还会图什么?
想到这里,粉莲就觉得有点害怕,她想:“这个人与二侉子不同,二侉子是真心地爱她,这人分明是想玩弄她。如果拒绝了他,他会恼羞成怒,将来没好果子吃,如果顺了他,他得了手后,就有可能到处显摆,通庄人都晓得她粉莲是个烂货。万一传到龙锁耳朵里后果不堪设想。
有一天晚上,桂芬跟我说:“我看队长这些日子有点不正常,怕的是看中了对门的那婆娘,他这样想方设法地照顾她,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思。”我说:“这事情你要说说粉莲,叫她注意点儿,那人不是个东西,千万不能跟他搭讪。”因为又没拿到过什么红的白的,我也不好贸然地去找那家伙说什么,只能静观其变。
6
后来我看到,这段时间里龙锁老是被派出去“远征”(那时常常派男劳力弄船出外取肥料,习惯叫远征),每次出去都要在外面过三四宿。桂芬听队里人说,前些日子骚公鸡已经得了手,有人在黎明时看到他从龙锁家出来。在桂芬的盘问下,粉莲在私下里将实情全部告诉了桂芬。
那是一个刚下过一阵雨的夏夜,天气难得的凉爽,骚公鸡在龙锁家不是太高的院墙外,两手攀墙,双脚一蹬,身子就窜上了墙。他轻手轻脚地翻过了院墙,很快就熟练地撬开了里边搭着门搭子的堂屋门,这种老式的对开木门,即使从里面用门搭子搭死了,对于想进来的人还是形同虚设,很容易从外面撬开,只要将其中的一扇门向上提一下,下面的门轴就脱了臼,人就挤进去了。其时,粉莲刚给小菊喂过奶,正沉沉睡去,虽然撬门的动静并不大,但还是将她惊醒了,迷迷糊糊中她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摸到了铺边上,是他!她早就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她惊坐起来,故作惊愕地说:
“哪个?你要干什么?”
“是我,别吱声。”说着一只手已经压上了她乳房。
“你千万别胡来,龙锁脾气犟,要是被他晓得了就没命了。”她虽这么说,但声音并不大,骚公鸡经验老到,只要女的不大声呼叫,这事就算成了。他说:“怕什么?怎么会让他知道?”说着就用嘴捂住她的嘴,又用双臂将她紧紧地搂进怀中。那时候,生过孩子的女人夏天睡觉时大都光着上身,下身也只有一件薄薄的洋布短裤。等到骚公鸡伸手去拆除她那最后一道防线时,她好像也有点儿进入状态了,竟然连一点装模作样的反抗也不曾有。在窗外月光的映照下,她一丝不挂的胴体是那样的曼妙动人。他先是像一头发情的公羊一样贪婪地吻遍了她的全身,紧接着就是一场残酷的肉博。
她太饥渴了,一切一切的顾虑都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从未体验过的愉悦,她觉得身上这个将她“折磨”得欲仙欲死的男人仿佛就是一头野兽,比二侉子更娴熟老到,与之相比,龙锁那循规蹈矩,经典而传统的三板斧根本算不得一回事。她以前听队里的婆娘们谈起过他,说他胯间的那话比常人长而粗壮,跟他好过一回的女人都还想着他,现在与他长期保持着这种关系的两个婆娘,都是在做姑娘时被他强过奸的,她们没告发他,反而成了他的老相好。耳听为虚,今天她算是领教过他的不同凡响了。她觉得她再也不想离开他了,哪怕他是个魔鬼,哪怕她将会因此万劫不复。

反反复的激情过后,他们都精疲力尽,本能让他们恢复了理智,粉莲幽幽地说:“如果你想和我好得长一些,你要听我的劝,第一你不能在外面吹牛皮摆方子,说在这里又搭上了我,这事传到龙锁那里,说不定他会跟你拚命。你倒是无所谓,我将来怎么做人?”那时出轨的女人最在乎的就是这一点,有句俗话说:“十个婆娘九个肯,就怕那人嘴不稳”。她接着又说“第二,今后你对我的照顾别做得太显眼,让人家怀疑;还有,你别看队里的那几个剌儿头被你整得服服贴贴,他们心里可恨你了,一旦抓到你的什么把柄,肯定不会有好果子给你吃。”骚公鸡听了,觉得这婆娘说得有理,想不到她还这么有情有义,他说:“你放心,这事我在外面打死也不嚼舌头,至于其它事情我也全听你的,我会和那几个人把关系处得好一些,他们无非就是要沾到一点集体的光,我让着点儿就是了,一点儿小恩小惠就能捂住他们的嘴,反正集体的又不是我个人的。”
后来,队里还真的比以前平静了一段时间,社员们发现队长好像比以前温和了一些,特别是他动辄爆粗口骂人甚至有时还会动手打人的恶习已经极难得发生了。他也清楚我与龙锁是发小,怕我坏他的事,对我也有点毕恭毕敬起来了。只是他与粉莲的那些风流韵事,队里除了龙锁几乎没人不知道。世界上事就是这么奇妙,越是做得隐秘的事情越难瞒得住人,常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其实,他们的事做得也不是很隐秘,有时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在龙锁接连好几天不离家的那些日子里,为了重温一回旧情,他们有时也会挺而走险,违反常规出牌。比如在大忙时节,粉莲每天要回来给小菊喂奶,她在我妈那里匆忙地喂过奶后还会回家去看一下,如果是两个人约好了的话,骚公鸡就会尾随而入,那时节巷子里空无一人,他们关上门,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够吃一顿“快餐”。还有时队长起早喊人煮早饭,摊着稻草的锅膛门口也能成就一回好事。龙锁家有个小厨房在院子的一角,以前大都是龙锁起早煮早饭,今年粉莲一反常态,说龙锁活儿重,让他多睡会儿,早饭由她起来煮,为此,龙锁还觉得是体贴他,心里暖暖的,他哪里晓得其中的猫腻?
7
第二年秋天,骚公鸡马失前蹄,被龙锁捉奸在床。这段维持了一年多的畸形恋情瞬间走到了尽头,他的“仕途”也因此寿终正寝。
其实龙锁早就起了疑心,他发现队长没来由地对他照顾有加,分明是有意跟他套近乎,比如安排送粮,几乎每次都少不了他,别的男劳力一年只轮到一两回。那时送粮是桩“美差”,虽然到我们的定点的粮站有二十里的水路,下半夜就要撑船出发,夯粮时还要爬很高的粮屯,但在那里可以拿集体的粮换米换肉大吃海喝一顿,那时候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有一回龙锁无意中听到几个男劳力在背地里议论他,其中有个人大发感慨说:“有个‘姨夫’当队长真好,回回送粮都有他。”在我们那里“姨夫”一词有另一层含义,别人会把女人的相好调侃说成是她男人的“姨夫”。话说得这么直白,龙锁又不傻,心想:怪不到每回队长遇到粉莲,虽然说话不多,但那眼神总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自此,龙锁就提高了警惕,不过,他还是挺有心计的,他也没回去“拷问”粉莲,他晓得如果真的有事,问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反而会打草惊蛇,只有多留心观察,一旦有了真凭实据,再出这口恶气不迟。
队里收中稻的时候,有一天夜里,队长喊人“翻场”。那时没机器,脱粒全靠人力和畜力,一般是将人工割上来稻把摊铺在大场上,用牛拉碌碡碾场,午夜过后,一遍碾过了,再用人工翻过来碾第二遍,一片大场需要喊七八个男劳力翻一个多小时。这天也轮到了龙锁,他想:这段时间他已有个把多月没出门了,就连起早煮早饭也不曾让粉莲起来过,如果真的有那么回事,他们极有可能要利用这点时间“作案”。果然,骚公鸡将人喊上场后,在场上转了一圈就不见了人影。场翻到一半的时候,龙锁就说肚子不舒服要上庄解手。那片大场就在庄后,只有庄上才有茅缸,离龙锁家也只有些200多米远。翻场的其它几个人,看到今天龙锁有点失常,此时上庄会不会是回家“侦察”情况?如果真的是回了家,恐怕今天会有好戏看,骚公鸡十有八九会在他家床上。有人提议:“不如我们也歇会儿,上庄看看动静,龙锁一个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假如让他逃脱了,他提起裤子就不会再承认。或许黑灯瞎火的我们能帮龙锁点儿忙。这家伙太张狂了,这回要彻底治一治他!”那些人大都是队长的对立面,其中有一个被队长打过嘴巴子的人还悄悄地拿了场上的一根细麻绳。
当这帮人在黑暗中走到龙锁家大门口时,只见大门洞开,房间里传出撕打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女人和孩子的哭声。正当这些人不知所措时,堂屋门里突然窜出来一个高大的身影,显然是这家伙已经成功地从龙锁手中挣脱了,正惊失措地向外突围,他那里料到院子里站满了人。他一愣神,立即就被从屋里冲出来的龙锁扑倒在地,不知是那个在黑暗中还蹬了他几脚。这时有人悄悄地递了一根细麻绳给龙锁,没多会儿他就被几近疯狂的龙锁捆了个结结实实。
等到我和桂芬被惊醒赶过去时,屋里己点上了油灯,骚公鸡被捆得像个棕子似的掼在堂屋的地上,他光着上身,下身虽有一件短裤但只伸了一只裤管,他的那个超级小兄弟,在暗淡的灯光下显得垂头丧气。龙锁正一边喘着大气一边挥舞着一把菜刀,嘴里嚎叫着说:“你们都出去,我今天非要把他的上头下头一齐剁下来。”幸好有两个大劳力死命地按着他,人们心里都清楚,事情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好。这时已经有人去叫醒了支书和主任,我料到这两个人今天都不会到场,这事情对支书来说他是不具备调解资格的,主任那人正与支书闹着矛盾,正好要看支书的笑话。因此,只有我才是“消防队长”的最佳人选。后来果然两人都没到,支书让人带来了口信,说这事由大会计处理(那时习惯将大队会计叫大会计,把生产队会计叫小队会计)。桂芬进门后,只厌恶地瞟了那家伙一眼就进了房门,她关上了房门,点上了房里的灯,看到粉莲用双手捂着脸在嘤嘤地哭,身旁的小菊在拚命地哭。桂芬先是抱起了小菊,对粉莲说,不管怎么样,别把儿伢吓坏了,就将自己的乳头塞到小菊嘴里,小菊才止住了哭声。那时我正在外面紧张的思考着如何才能平息这一场不同寻常的风波。
8
我先是拿下了龙锁手中的菜刀,接着又对那几个翻场的男劳力说;“这事由我来处理,你们翻场的人还是继续去把场翻结束,不能耽误明天起场晒稻。其它的人也都回去睡觉,明天大家都还要上工。”后来,我只在那些半夜起来看热闹的人中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德高望重的老队长,还有一个是龙锁的本家哥哥。我对他们二人说:“你们先在这里看住一会儿,我到大队部去打个电话(全村只有大队部里一部电话),这事如何处理要请示一下公社的顾科长”(那时还不曾有派出所,一般治安方面的工作都由治保科长和他的一个助手处理)。回过头又对已经平复了一些的龙锁打了一剂防疫针,我说:“这事情你千万别瞎来,国家有法律,你如果瞎来也要犯法!”
顾科长听了我的汇报后,在电话那头跟我说:“你们这事算不上是什么案件,只要不是强奸,在捉奸的过程中又没有打伤人,由大队里调解一下就算了,不过,因为是队干部腐化,公社还是要管的,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弄一条船把人送到公社来,这样可以先平息那边的风波,然后再由我们通过调查后冷处理。人送过来后,你们重点要做好女方那边家庭的工作,千万不能再出事。”我听了就说,这办法好。
回到龙锁家,我对他们说:“顾科长说了,问题很严重,他要我亲自将人‘押送’到公社去,可能要逮捕。”说完后,我看到龙锁对这个结果没反对就立即叫来了大队公勤员,叫他把那条带棚子的小差船划过来。等到船划出了庄子,我才替那个倒霉的家伙解开绑在身上的麻绳,穿上了上船前他老婆给他送来的一套单褂裤。后来才知道,这家伙“作案”时只穿了一件短裤,而且在行事时只将短裤褪掉一只裤脚,主要是为了遇到突发情况时好方便脱身。我松了一口气,这事情的第一阶段算是圆满解决了。
那天夜里天特别黑,静悄悄的河面上偶尔有鱼儿跃出水面,岸上不时传来一阵阵秋虫的鸣叫。这里离公社驻地有十多里水路,平时大约一个半小时能划到那里,这种一个人划双桨的小船,速度不慢,今天是摸黑,估计天亮后才能到。惊魂乍定的“罪犯”与我一起挤着躺在狭窄的船舱里,感觉到他好像在微微颤抖。黑暗中,他轻声地对我说:“真难为你了,对不起。”很显然,他对我用这种方式把他救出“虎口”是十分感激的。
顾科长问了我一些详细的情况后对我说:“好了,人先丢在这里几天,你回去仍要注意女方那边情况,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再出事。”我说:“科长你放心,我跟那家住门对门,那女的又跟我婆娘处得不丑,估计过几天能缓过来。”
后来的几天,桂芬也没上工,整天地陪着粉莲,头两天那婆娘躺在铺上不吃不喝,连奶也不给小菊喝,害得桂芬好像生的是双胞胎。夜里也是桂芬带着两个丫头跟她一起睡,她家只有一张铺,龙锁就在我家临时过渡了两宿,这时龙锁已经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只是希望粉莲别寻短见。夜里,桂芬反反复复地开导粉莲:“你别老想不开,世界上又不是你一个人有这事,别说我们是做农民的,就是那些有工作的当演员的当大官的女人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家背地里嚼舌头,她嚼她的,嚼嚼就不嚼了,她总不敢当着你的面嚼。龙锁跟我说了,他不怪你,都是那个畜生太花心,这回他也算是出了一口气。把你的脸撕破了他现在也懊悔,你也要体谅他的感受,这事情哪个男人能忍受?再说,不是我说你,本来错就在你,这回给你个教训我看也好,听说公社里发狠要认真地处理那个家伙,至少他别再想当什么干部了。你要知道,你这样不吃不喝的其实是在折磨我,我哪有那么多奶给小菊喝?”粉莲默默地听着桂芬的数落,也不吱声,显然是觉得桂芬的话句句都在理上。后来桂芬从我家端了一大碗热粥过去,看着她喝下去了,接着就把小菊推到她怀里。那晚,桂芬对龙锁说:“没事了,今晚你回去睡吧,下一步就看你的了,回去好好地哄哄她,她好像也知道错了,不过,你也要保证这事过去就算过去了,今后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准再提。”
过了几天,这边安定下来了,公社那边的处理决定也出来了,只是撤去了骚公鸡的队长职务,其实队长也算不上是个什么官,但社员们还是觉得处分不轻,也挺解恨。听说,支书本人也受到公社书记的严厉批评,只过了个把月就将他调到了公社副业办公室去当什么副主任去了,由我来接任他的支书职务。我知道他去那里是被冷冻起来了,那个单位里安排了好几个免了职的支书,整天无所事事。人说那个地方是“书记处”。
9
第二年夏天,粉莲又生了第二个女儿。那时,庄后的莲塘里莲叶田田,开满了一池荷花,他们就给二女儿取名小荷。其实在去年出事时,粉莲已经怀着身孕了。由于营养不良,小荷生下来时瘦瘦长长的,一看就料到将来会有个高挑的身材,也不知道是不是骚公鸡的种?几个月后我家的第三个孩子也跟踪而至,让我爸妈激动不己的是我家老三是个带把儿的小子。
生产队里的情况比前几年好了些,被停了近二年的老队长又复了职,经过了一段时间“强权统治”的折腾,人们对老队长好像比以前更加敬重了些。龙锁家的口粮也比以前宽裕了,主要是因为有两个小口扯着(那时基本口粮不分大小口),但经济仍十分拮据,两个人做的工分要买四个人的口粮,粉莲有两个孩子拖着,也做不了多少工分,要不是我妈那里有个免费“托儿所”,粉莲一天工都上不成。两个人整天忙得团团转,正值壮年的龙锁倒有点像个小老头,粉莲虽然还没到三十岁,但也显得心力交瘁,风光不再,哪里还顾及到当年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后来我家桂芬做了妇科结扎手术,龙锁家又生下了个儿子,只可惜那个儿子是个“白毛儿”。据说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叫白化病,在近亲结婚的人群中发生的概率相对会大些,当然也有另外,有的表兄妹结婚生的孩子照样健康聪明,也有的不是表兄妹却生下这样的孩子。生下来时龙锁两口还不是太沮丧,他们觉得总比再生个丫头好,好歹是一条根,他们把儿子取名叫贵根子,精心呵护,疼爱有加。贵根子智商并不比其它的孩子差,小时候还挺聪明伶俐惹人喜欢,只是他的那双蓝眼睛特别怕光,将他抱到阳光下,眼睛老是眯缝着。队里有人议论说:“这贵根子倒是杨家的真种,只是可惜撑不了杨家的门户,如果粉莲不曾痛改前非,仍像以前一样“风流”,可能结果还会好一些。”也有人说:“这白毛儿可能就是他家的最后希望了,计划生育一年比一年紧,要想再生第四个恐怕是不可能了。”还有人说:“就是批准他家再生一个,估计也结不出什么好果子来,除非他婆娘再去借种。”有时候男人们还互相打趣:“要不你借个种给他家?”
分田到户那年,我得以提升,被调到公社工作。我的大女儿进了社办厂上班,两个小的都在外面上学,桂芬一个人在家种了七八亩承包地,那时还不曾有机械化了,比在大集体时还要忙。龙锁家孩子上学少,家中劳力多,每至农忙季节,都会帮桂芬不少忙。几年后,他的大女小菊嫁给了本村里的一个民办教师,后来又转成了公办,现在每月能拿到好几千元工资,比我的退休金还高一大截。二女儿小荷,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小木匠,改革开放后先是跑到东北沈阳给人家做装修,后来自己在那里与人合伙办了个家具厂,听说现在已经是身家好几百万的小老板了。令人有点婉惜的是,龙根这边的情况很糟糕。贵根子到三十岁出了头还没找到个合适的人成家。无奈之下只好化了6000多元钱买了个媳妇,那姑娘是贵州过来的,还是个弱智。生了个孙女虽然不是白毛,但比她妈更弱智,上了五年小学才读到二年级。
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他家的经济情况倒是一年比一年好,家里的承包地都是粉莲和贵根子在家里种,他一个人到苏州去收了好几年的废品,他在郊区租了人家的一间房子,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走村串户,每年能赚得好几万元。他又舍不得花钱,穿的衣服、鞋子都是从废品中挑出来的,他告诉过我,他已经存下了五六十万!
后来我退休了,回到了村里的老屋中养老。有一年过春节,他因为中风险些送命,幸好我及时找人用车把他送到市人民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老命。不过打那以后,他就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走路也离不开轮椅了,那年他正好70岁。在病中以及后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粉莲对他的照顾也算得上是无微不至了,虽然他们之间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故事,但几十年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平平常常的岁月已经将他们打磨成一对情深意笃的恩爱夫妻。
坐在轮椅上的龙锁,好像脑子还不怎么糊涂,能清楚地记得过去好些陈年旧事,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跟着他坐的轮椅在庄前的公路上散步,看到路边一排排新建起来的堪称豪华的乡村别墅,他不无感慨地跟我说:“想不到乡下人还能砌得起这样的房子。”我说:“你不是也砌得起吗?”我这话好像是触到他的痛处,他幽幽地说:“是的,我现在砌一所这样的房子,不管怎样装修也不会欠债,不过,我砌它干什么呢?再过短短的几十年,我的这个家庭可能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实在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他,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杯人生的苦酒,也许这就是“命”吧。
作者:荒村一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