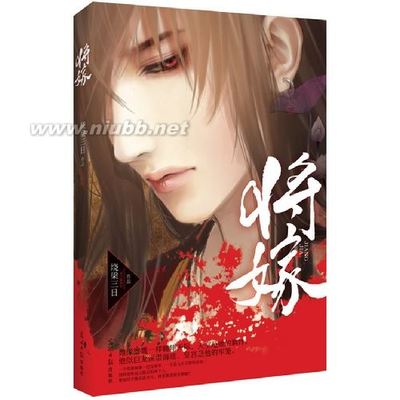粥于我
除却天寒或宿醉后的暖胃
更多的是记忆里的暖心
粥,自古以来就是清贫,淡泊的代名词,也是人们穷困潦倒时的最佳伴侣。要生存下去,粥便是最好的选择:不多的米,加上较多的水,可以填充饥饿的胃。所以粥,一度是贫穷的象征。文人墨客们在一碗粥之中品出个淡泊的精神世界,或安贫乐道,或知足不争。

清代作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粥有如下定义: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
时过境迁,粥在当今被赋予了更多健康养生的意味,内容也从先前的寡淡走向浓郁和营养。一碗粥可以包罗万象,也可以平淡无奇,而其中的精髓,都归于一个“熬”字。
宁愿人等粥,毋要粥等人。所谓熬,即不急不缓,火到自然成。耐心是制粥的关键。一碗好的潮汕砂锅粥,新鲜的虾蟹或土鸡,瑶柱,炸蒜的滋味,在水和米的交融中扩散,浓缩。慢中有进,大开大阖。一碗粥看似平静,其实已经历几个小时的文火煎熬。
好粥香而软糯,入口绵而不散,不与唇齿为难,几小时文火保留的温度润而不燥,从食管到胃,霎时遍布全身。倒是虾蟹之流竟成了陪衬,平日为人称道的紧致口感于此显得有些鸡肋,被一汪清水一掊米抢尽了风头。
粥于我,除却天寒或宿醉后的暖胃,更多的是记忆里的暖心。儿时体弱多病,每每食欲不振,母亲总是熬一小锅稠稠的白米粥,加点肉丁葱末,便能拯救我的胃口和心智。喝上一碗粥,把自己紧紧裹在被子里,对第二天早起就能康复的信心往往会增加不止一分。
如今一人在外地求学,不免思念家乡的饮食,虽然原籍新疆,却时常被记忆里寒冬之际家里那二三样精致的小菜和一锅骨汤煲粥摄了魂魄,那大概是新疆冬天里最能温暖人心的晚餐。
今年双十一母亲心血来潮寄来一个小功率的煲粥锅,自己在宿舍如法炮制,大功告成之后颇有仪式感的盛上一碗,粥一入口,烫口和想家的眼泪一齐开闸。
细细想来,所思非食,而是思念满屋的谈笑,思念围坐桌前的三口人,思念一份只属于家的暖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