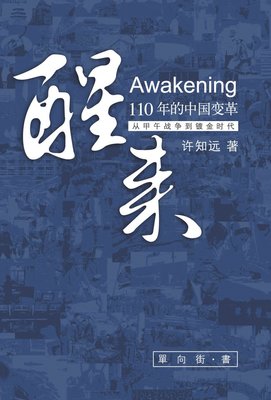许知远和吴琦是《单读》的两任主编,两个人都是从北京大学毕业。他们是不同年代的人,却在同一个时代相遇,带着自己相同的态度、不同的理解赋予《单读》独特灵魂和生命。
一个月前,在《单读12:创造力之死》出版之际,他们重回母校,进行了一场对谈。今日微信,节选了其中许知远的部分发言,聊北大、聊时代、聊单读、聊不同代的问题与变化。
1.
他们那一批人想抓住什么?
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传统是钱理群带来的,他带来的五四的鲁迅的传统。钱老师身上多了很多共产革命之后的知识分子特征,再加上鲁迅的特征,而且他的经历非常丰富,曾经在贵州下放,然后又回到北大,身上有很多这个社会所经历的痛苦、敏感,又承继着鲁迅,或者说鲁迅滋养着他。他通过讲述鲁迅也滋养了很多人。他的课永远都是在一个三百人教室里头,我不知道现在二教还在不在。他精力充沛,声若洪钟。我觉得他那种讲述传统,他不是靠讲,而是讲演。这一脉知识分子的传统,对我影响非常大。
还有一位历史系老师叫罗新,现在应该还在历史系教书,他讲魏晋南北朝,我印象特别深。在公共课上讲中国历史,讲百家争鸣的时代,讲到魏晋、竹林七贤、嵇康被杀的时候,说我中国通史我只讲到这个地方,从下节课开始换一个老师来讲,因为中国历史到此就变得非常无趣,我只关心有趣的部分。现在我办《东方历史评论》杂志都跟他的那种潜移默化的滋养有关系。
尽管潮流在变化,但其实所有的思想传承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只在书本上的。当时北大还有很多八十年代的师兄,他们会表达。上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比较自由派的老师,他们会讲对批判性的追求。孔庆东是我的高中老师,我算跟着他来到北大,我们俩现在见解当然非常不同,但他当时给我很大的启蒙。他那一批人想抓住什么?他们想抓住八十年代一直到五四那个批判的传统。尽管说北大在堕落,但我不相信传统会消失,他们可能隐藏起来,涓涓细流,但有一天它会重新地展现出来。
钱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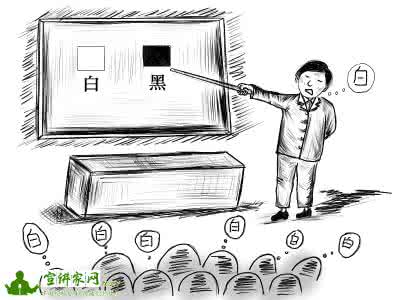
2.
眼睁睁看到黑白是非的颠倒
这次重回北大,对我来说最惊叹的一件事,是眼睁睁看到黑白是非的颠倒。
北大最重要的是培养知识分子的传统,而知识分子又是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我们在过去十年里看到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反智的潮流,知识分子本身变成了一个被侮辱的和边缘化的声音,不分青红皂白。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沦为一种笑柄,被那些假崇高的东西伤害之后,大家就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的崇高了。所以最终留下来的是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使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得到巨大满足和放大的东西,这样一种思想成为整个时代的潮流。
北大应该是成为抵御这个思想的中心,但她没有做到这点,甚至是更明确地迎合了这一潮流。
那时候我们已经非常厌倦了,1995年上学的时候,光华管理学院变成学校最重要的一个系,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北大沦为一个以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为中心的学校,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北大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人文主义传统,但这些东西被迅速地弱化。我觉得知识精英放弃抵抗也是这个变化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北大是代表知识精英的传统,但她放弃抵抗,而且放弃得特别快。
北大未名湖
我觉得大学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应该是一个收容失败者的地方,应该是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地方。并不是这些人真的是失败者,而是他们不愿意完全融入,或者被加上最主流的价值观。一个国家长远的发展,绝对是里面多元的价值观,因为你不知道某些价值观可能会出了问题,跑不动了,或者出了巨大的危机。这时候社会像一个生态体一样,多样生命体绝对是更有生命力的,互相的激发。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多元的价值观。我们一直在用商业的钱来做一些非商业的非盈利的事情。
最终个人和组织之间要有某种平衡的。我相信那些纽约厉害的知识分子们,如果少了《纽约书评》,少了那些基金会,他们也很难维持的,他们是一个生态系统。中国为什么这么困难,就因为生态系统没有形成,大学不提供主要的知识生产,本来应该是最重要的地方。基金会和 NGO 非常少,不能覆盖这些年轻人。所有人要做的最后只能投入到商业组织中,商业组织中又缺乏耐心滋养你,所以变得很困难。所谓的成名和个人品牌,并不是个人怎么样,只是个人被迅速商业化的结果。因为毕竟知识的生成思想的生成是更复杂的过程,无法用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来达到目标。
3.
我们希望《单读》更是一个
全方位探索世界精神的品牌
我办《单读》或者说书店跟北大有很大关系。1997 年的夏天,我们那时候还军训,17 天左右,非常无聊的生活,穿着军装回到学校,住在 28 楼。那时候我发现了风入松书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一个书店,它的所有书都是开架的,你可以坐在地上看书。后来,我有很多天都是在那里度过。
当时是哲学系的教授王炜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开了那个书店,他卖的书当时我看不太懂,但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也会做讲座,请不同的作家来,我就远远地在后面听他们讲这些事情。它是我大学时光的一部分。那时候我就感慨,多好的老师办这么一个空间,让我们这些人当图书馆一样用。如果我长大以后就特别想去做这样的事情,也能跟他们混在一起,我觉得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北京大学南门的风入松书店
到2005年的时候,正好我和我同事集体辞职,在圆明园那边发现了一个空间,就每人出5万、10万块钱开了这个书店。然后我们开始办沙龙,第一场就是西川和北大的毕业生。其实蛮简单的,比如被风入松影响,被 CityLight、Strand、 莎士比亚书店影响,它们都是各个城市的文化中心。这些书店都不仅是一家书店,都是跟对应的文化思考有关系。比如说 CityLight 跟垮掉一代的作家们,它出版这些作家的作品,跟整个旧金山的文化、文艺复兴精神有关系,到后来又变成硅谷文化,这是它们内在的关系。 Strand 也是战后纽约几代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从海明威一代,一直到现在。
我们对单向街的期望就是它能不能随着在北京或者中文世界的这批新的创作者——这个时代不仅是写作了,可能是影像,可能是各个不同的方面——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描绘自己的时代,甚至能做出超越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做大量的文化沙龙,这是我们跟别的书店最不一样的。同时我们又受到一些重要的影响,《纽约书评》非常重要,《巴黎书评》很重要,《新共和》很重要,这些杂志是非常知识分子的杂志,但这种西方知识分子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坦白的说,包括北大也好,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知识分子对世界的理解是很窄的,文学教授就做文学,历史的就是做历史,社会学就是社会学,写一些很枯燥的文章。我喜欢西方的知识分子系统,他们能够既理解自己的传统,又对世界作出很崭新的发言,写出的文章又非常可读,非常漂亮,有思想。我们当时想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杂志,就是《单向街》,新一代年轻创作者的平台。其实我们开始做的也不太好,但做着做着,我们发现这个杂志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2005 年,圆明园一隅的单向街图书馆
在 2008 年、 2009 年我们办单向街的时候,中国还有同类的杂志,包括《书城》还存在。随着我们做的时间越来越长,发现跟我们相似的越来越少,这个杂志可读性越来越强,我们只发很长的文章,我们只发那些对时代有感受力的东西。现在的口号是全球青年思想者的策源地。我们想这个东西能连接中文世界的作者、年轻作者,包括美国的、欧洲的、印度的、非洲的。因为过去十年全球文化真的变成很多地方的一部分,我们可能都是被社交媒体影响长大的人,都是共同面对类似的全球问题。
这也是试图想打破中国知识的另一个不太喜欢的传统,我们太着迷于独立的中国问题了,而对世界问题缺乏兴趣。如果你对世界问题缺乏兴趣的话,你就很难理解真正的中国问题。而此刻这个杂志也不仅是杂志,我们有自己的 APP,有自己的视频,有自己的音频。我们希望它更是一个全方位探索世界精神的品牌。
单向空间花家地店
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悲叹,是因为原来的精英文化的旗帜性自我瓦解了,自我消失了,跟知识精英的自我更替有很大的关系。但整体来讲,我觉得社会中层仍然在继续往上提高,对这样东西的需求在提高。这样的时代在历史上并不是只有在中国,在19世纪经过工业革命之后,那时候新媒体是报纸,英国知识分子都在哀叹英国堕落,一群没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们占领社会。当时的批评家都是面临新道德的民主和报纸带来的大众革命,非常恐惧,所以勒庞写了《乌合之众》。而且一开始确实也是,新的技术到来的时候,印刷的东西大部分都不是知识分子想让人民群众看到的东西,中国也是一样的,印刷术到中国来以后,大家认为印刷术是来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结果印的大量的是鸳鸯蝴蝶派,就是当时郭敬明的作品,是最早畅销的东西。历史上都有这样的,但是经过这段时间之后,又会演入新的秩序。
在50年代美国大陆消费市场起来之后,如果你看当时最有名的批评家麦克唐纳,他当时所写的文集,都在批评美国畅销书们的劣质,他认为好的读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知识经济和大众的冲突是不会终结的,它们应该始终存在,形成某种张力,就像我们在这里做出这样的批评一样。
4.
思维混乱是这代人非常普遍的特征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好多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向你涌来。那时候我们得去找世界,现在你们只要用 VPN ,那时候我看到一份纽约时报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痛苦死了。那时候我很重要的思想启蒙,我去北大东门的平房,那种小贩神秘兮兮地卖很多过期的时代周刊杂质,你通过那个来了解世界。
而你们,所有想知道的事情都可以涌来,所以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来充分理解这些东西呢,而且对应的书所有的图书馆都会有。虽然跟背后的训练有关系,但不是所有的责任都是归在外界的,如果你抵御不了,那是你自己有问题,要自我训练。
我确实也看到那种可悲的现象,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看到新一代留学生,真的让我叹为观止。他明明生活在纽约,他们的整个生活世界就由淘宝、湖南卫视和优酷构成的,这个世界他们在国内已经非常熟悉,带到国外去,跟所有的朋友都是在圈里,都在中国。明明给他们展现世界的机会,观察世界的机会,他反而被封闭起来。
你们最重要的思维特征是什么呢?一切都是同时涌来,陈冠希的丑闻和 911 的事件是同时在你的眼前,他们都很重要。但我们以前看报纸,第一版是很重要的,放什么样的东西,版面绝对是一代一代编辑下来的,比如社论很重要,我们要对世界,对以色列巴以冲突发生新的看法。然后到第七版是娱乐新闻,第八版、第九版是体育,第六版是书评,是这么一个关系。而这些对你们而言是同时出现的,这时候就造成思维的混乱。
思维混乱是这代人非常普遍的特征,不太会思维是上代人的特征。
所有的信息都在一起,你搞不清楚前后的关系。所以就要训练自己,要非常的刻苦地训练自己,要利用新的信息刺激你对过去传统的理解。所以我为什么对功利主义的现状非常的厌恶,因为大家真觉得人跟机器一样,做完 C 就是 D ,不存在这样的事,C 和 D 之间的距离可能不同,而且是曲折的,而且 C 也不通往 D 。
好的教育并不是让你追寻某一个路径,而是在某一个恰当的点,关键的路上面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特别忌讳自己成为某一种抽象的文学原则,为什么我不喜欢《十月》、《收获》这样的杂志,因为他们变成一个圈子游戏,并不是里面写小说的人就高级,长期做技术工人也可以写得很好。我们想打破这种行业战争,并不是你们教授都有学问,大部分教授都没有学问的,只是知道教科书而已。我们寻求的是创作者、读者之间对事物新型的感受力、贯通力。
人生的路每次特别像在边缘上行走,你要不断判断和选择,你总是要面临无穷的判断。判断其实是生活的核心。你所有的教育在做什么呢,让你做出更充分的判断。
你们可以思考人生在多少情况下是自己做出判断的,估计大部分很多都没有,都是别人判断好的。判断是教育的本质,以及文学的本质,艺术的本质。
5.
最心痛的事情是
不同力量之间失去了对话的能力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保守的更保守,激进的更激进的。激烈的也好,温和的也好,他们都有存在的理由,他们完成一个相互的制衡。有些年轻人特别激烈,因为他们的渠道太少了,你让一群没有表达渠道的人温和下来,就像你让实验二小那些老师那些家长,自己的小孩都流了鼻血,你要冷静下来,你不是胡说八道吗,他应该更激进,应该争取小孩子的个人权利,因为他没有律师渠道,没有社会媒体的呼吁。你让雷洋的妻子温和下来,她怎么温和下来?
所以我觉得可能让我最心痛的事情是,是不同力量之间失去了对话的能力,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重要,这个东西就出了问题了。
现在整个中国社会遇到的巨大的困境之一,是所有的系统之间的对话能力消失了。比如说社会新闻上,江苏那些家长们抗议自己的考生名额减少了,他们找教育厅长,他们需要的是对话,需要解释,出来的是公安局长,对话就消失了。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需要的是跟外界对话,这种对话也消失,在这里孤芳自赏,而且是堕落式的孤芳自赏。不同学科之间需要对话,也消失了。
每个行业,这个行业导演和作家对话消失了,所以电影和剧本特别烂,没有想法。知识分子跟艺术家的对话消失,所以艺术变成炫耀式的。作家不愿意跟不同的新的行业对话,所以他们只能整天写着乡村和小镇的那点经验,对新的时代没有感受。怎么重建不同领域的对话,彼此尊重对方的声音,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事情。
单向空间花家地店
我相信一个好的诗人是跟农民是可以对话的,否则就没有白居易了。而且最杰出的不同行业的人都能找到彼此的相通性,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和哲学问题,本质上来说。所以我觉得你不用被你周围的环境吓住,你可以跟各种人对话。所有的信息到我的面前你要梳理它,通过写作也好,通过思考也好,把它变成你生活沉淀的一部分,这就是对话。
人的滋养是很奇妙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某一段记忆,某一场相遇,某一段阅读,某一次谈话,都会储存在你的记忆里面,在某一时刻对你发生作用。它应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维度,即使将来被迫扔到更残酷的现实中,他体验过一段理想主义很好啊。
我印象很深的是,瑞典作家梅特林克说的一段话,我以前也特别喜欢这段话,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单读》对读者的期待,文章叫《普通读者》。他就说什么是作家理想中的普通读者,他说是那些在星期日进城的时候那些没有去小酒馆寻欢作乐的农夫,他们跑到了城边上静静看了夕阳,他们没有把自己交给一个狂欢节或者喝得烂醉,而是在树下静静读了几页书,他们都是工匠、农民。
对《单读》来讲,这也是我们心目中最美好的读者。
本篇首发于微信公号“单读”(id:dandureading),理想国重新节选编排,原文可至“单读”查看。
●
●
●
《单读 12 ·创造力之死 》
本期《单读》从文学写作、历史叙事、生活方式,从个人到社会等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这个话题,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思,批判,创作,抵御着同质化的侵蚀。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