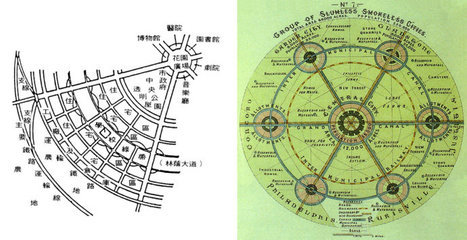上次谈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钱穆先生就此与“本来无一物”区别,认为后者是理悟,前者是修行,因此就说六祖佛法是递进的,从悟而后修,重在行,这一点是宋明儒标榜修身养性的由来。
《坛经·般若品》:“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禅宗讲心性,儒家也讲心性,宋明儒受到《易经·系辞》及《中庸》的影响,而有本体论,所以钱先生就认为禅宗与孔孟学说相近,比宋明儒还亲。就心即理言,陆王又较程朱的性即理近禅宗,是有原因的。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又主张“未知生,焉知死”,生,就要快快乐乐完成责任义务,不必顾虑后世;孟子其说,精神更加敏锐,主张大丈夫气节,倡言:“舜何人耶?禹何人耶?有为者亦若是”,敞开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大旗。就这一点是很符合现代企业精神的,日本人研究孔孟,研究阳明学说,恍然人欲即天理,在企业经营与创造发明找到一条正当的道路,兴业富国,提早现代化。
其实,这也是文字带来的麻烦,禅宗与儒家面对的问题截然不同。禅宗的本来面目涉及万生万物的共源,超乎我们所认定范围之外的生命学;儒家所关心的是现世王道的推行与实现。只要有人心与人性的存在,往哪条路上走,结局如何?没有人能找到答案。况且释儒在关于心性的认知与范畴上,是相差很大的。
钱穆先生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做修行讲,虽不符禅宗精神,但由渐而顿,走上“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修途,也是困知勉行的。
在实务上讲这条途径很实用,修行的起步在发现自己行为思想的偏差,逐项修正或放弃。用现代的心理学讲,即扬弃负面、消极的心理因素,保持正面、积极的心理因素;妄念渐渐消除,正念持续增长,这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让负面、消极的心理因素常住,而生起正面、积极的心理因素,过活健康的生活,非常符合儒家入世的积极人生态度。
再就启发心性的手眼上看,也非常值得研究的。禅宗第一公案,惠能向惠明讲:“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的悟入,不在“不思善,不思恶”,那也是一种“住”,心是开不了的,“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
因此六祖又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惠能所掌握而悟道是“无住之本性”,这不是一般学术界可了解的。
这种心要虽然出于《金刚经》,但惠能兼摄了《楞伽经》离两边,中间亦不立的心要。融摄了之后,他又在为志道解答《涅槃经》疑问时,以一句话展现他的无上智慧:“剎那无有生相,剎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
六祖之前,天台宗与法相宗盛行,尤其天台宗教观严密,法理精湛,智顗讲净:“观众生空,故名为观。观实法空,故名为还。观平等空,故名为净。一切外观名为观,一切内观名为还,一切非内非外观,名为净。”这是天台观、还、净的止观法门的后三妙法门,与惠明当时的“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颇为接近。
而南岳慧思于《诸法无诤三昧法门》说:“复次欲坐禅时,应先观身本,身本者如来藏也,亦名自性清净心,是名真实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断不常,亦非中道……无住处……生死涅槃,无一无二……从昔以来无名字,如是观察真身竟。”是观心法门。
天台宗有浓浓的哲学味,又有严细的观心法门,比诸六祖对涅槃的掌握,显然学究多了。六祖是智能型的,在经典之外,别出心裁,一句“剎那无有生相,剎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摆开了三度空间的思维,也摆开了哲学的思辨,值得参禅人用心去参。
以后就没有人可以发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精义了,因为言语道断,祖师在无可如何中另辟蹊径,这就是机锋、转语的突起。
机锋、转语是祖师辈直接从本心流露出来的应答,有时候充满了幽默;有时候又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一刀两断;有时候却让人感激涕零,花样百出,但绝对不是耍聪明手段,故弄玄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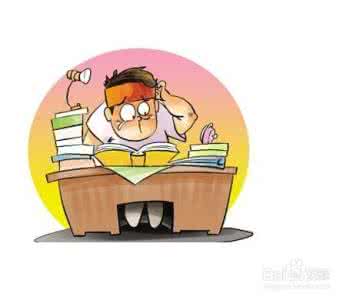
胡适博士,他研究了禅宗祖师的教育法,归纳有“不说破”原则,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属于“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渡与人”,他们都不把事情用和平语言解释,拐来拐去,总要学人自己去思考,去发现。第二阶段禅师施展机锋与棒喝,完全离开语言文字,手段狠辣,杀人不见血。第三阶段是行脚参访。
胡适虽然被推为聪明人,但他对禅宗向来没有好脸色,认为这些禅师不学无术,故意装模作样,是不可理会的一群疯子。
现代禅师一样不懂应用各种手段来展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偏偏要学人坐蒲团上数息、放下、入空、亲证空性,甚至把拈提、评唱像讲故事般的演练,然后由主事者或暗或明地标志法要,真是令人喷饭。
机锋、转语,或棒或喝,都是禅师全人格法身化的自然举动。南泉斩猫,刀起刀落,哪一刻不在启发无住生心的妙用?后来赵州从谂,一句也没讲,把草鞋放在头上,悄悄地走出堂外,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说禅,活活地表示了无住生心的哑剧,也绽露了禅师幽默、纯然的不做作。
如果赵州在斩猫的当场,会不会也把草鞋放在头上走出去呢?不会的,他也许会把刀抢来,并且说:我来斩猫,不劳尊手。如果我在当场,我会把猫放了,结束这个闹剧。
禅宗不容易推广,是公认的,全看禅师有否具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能耐。六祖踏碓八个月,才说米熟也,犹欠筛在,欠的是师父的印证。现在禅师都不必由师父印证,自己印证自己,这是冬瓜印,救不了生死。学术研究毕竟是意识活动,依文解义,难免三世佛冤。
(澄海先生《身去身来本三昧》之四十一)
(更多内容可关注安祥禅微信公众号,微信号anxiang-chan)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