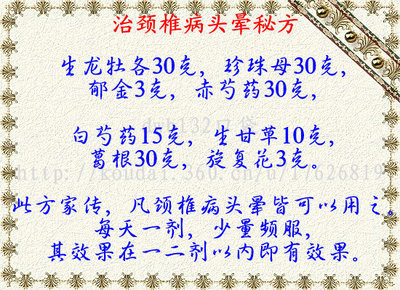利维坦按:嗯,慢慢看文章吧。

文/曾格
特别鸣谢/袁凌女士
记得好多年前,看过一部影片叫《棕兔》(2003),导演是那个忧郁到极致的人——文森特·加洛,对,对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更来自那部他执导的《水牛城66》(1998):
《水牛城66》剧照
《水牛城66》中的比利(文森特·加洛 饰)是一个典型的边缘人物:替人顶罪坐了五年牢,和父母的关系非常非常疏远,几乎没有朋友,曾经有一个单相思的女友,还被对方在现任男友面前无情地嘲笑。总之一句话,比利没有存在感。
我一直觉得,比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森特·加洛自己,这个带有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从16岁的时候就被他的父亲赶出家门,迷恋过摇滚乐,组过乐队,做过摩托车手,也非常喜欢电影,当然,最让公众所熟知的,还是曾经作为模特出现在Calvin Klein的秀场。
很遗憾,我今天说的主题不是加洛,而是他执导的影片《棕兔》中的电影原声。除了影片中让人触目惊心的口交镜头外,我印象深刻的当算是影片中男主雨中驱车时的背景音乐《Milk and Honey》了: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Milk And Honey Jackson C. Frank - Jackson C Frank
我按图索骥,搜了一下唱这首歌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杰克逊·C·弗兰克(1943-1999),我听音乐或许不多吧,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年轻时的杰克逊·C·弗兰克。
弗兰克是谁?以下,附上很零星的中文资料介绍:
……弗兰克的一生是短暂而有传奇性的,生平只出过一张专辑《Jackson C.Frank 1965 EMI Columbia》,童年的一场大火成为他一生最可怕的回忆,这场大火,使正在上音乐课的他,全身烧伤面积达到50%,虽然这场大火差点夺去他的生命,但也正是它赋予了弗兰克对音乐的顿悟,使他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
在少年时,弗兰克已经是一位在家乡布法洛(美国一个小镇)远近闻名的民谣歌手了,但是另人琢磨不透的是,弗兰克并未留在自己的当时拥有民谣领军式人物鲍勃·迪伦而被世界各地民谣音乐家都向往的的祖国,而远赴他乡。
在英国,他很快地融入了当地的音乐圈,并结识了很多音乐上的朋友,其中著名的是保罗·西蒙、Al Stewart等人。凭借自己出色的作品,弗兰克在英国的民谣界很快的树立了自己的旗帜。在1965年之前,他已经有了很多首在音乐圈广泛传唱的作品,在1965年,他的唯一的,如金子般珍贵的专辑出版,在录制专辑时,其古怪而孤僻的性格开始体现,始终坚持一个人坐在屏风后面,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包括伴奏乐手和监制。当时的民谣音乐专辑录制手法相对简单,所录出的声音的也更接近真实,当然这样简陋的录音方法也对音乐的品质提出了要求,不借助录音和包装的音乐也更接近音乐的本身,这张简简单单专辑却使他的名字永远记载在英国的民谣音乐史上。
虽然这张优秀的作品使弗兰克在英国民谣界树立了极高的权威,但这(专辑的出版)也是他一生中短暂的辉煌结束的开始,他忧郁的性格和古怪的脾气毁了他,1969年他婚姻破裂,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也死于膀胱炎,受到这一打击的弗兰克终于精神崩溃,加上酗酒,常年辗转于精神病院和医院,其余的时光就在街头和简易房中风餐露宿,70年代虽然得到一些好心歌迷的帮助,情况稍有好转,然而命运的作弄,弗兰克在一场枪击事件中被误伤左眼从此失明,尽管遭受如此之多的痛苦,但他始终都坚持音乐创作。
1999年,饱受苦难的弗兰克离开了人世,享年56岁。
1999年,左眼已经失明的弗兰克
弗兰克和妻子Elaine Sedgwick(一位当时的时装模特),他们育有一儿一女,但儿子的过早离世,对弗兰克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当时听《Milk and Honey》的时候,就觉得嗓音清澈而忧郁,但真没想到弗兰克的一生如此艰辛。不了解他的人,很难将那个唱片封面上清瘦俊朗的年轻人和后来身材肥胖、蓬头垢面的弗兰克联系在一起。他生前从未取得所谓商业上的成功,但弗兰克影响了包括保罗·西蒙、尼克·德雷克(Nick Drake)和桑迪·丹妮(Sandy Denny)在内的一批音乐人。
在利维坦之前《关于囚禁,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点红字直接取阅)一文中,其实也顺带谈到了一位生前默默无闻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布鲁诺·斯列斯坦(1932-2010,Bruno S.)。
作为妓女的儿子,布鲁诺自幼就经常被他母亲毒打,以至于三岁的时候耳朵一度被打聋,过了很久才逐渐恢复了听力。可以说,布鲁诺基本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音乐家,他拉手风琴,弹奏钢琴,除此之外,布鲁诺还对绘画情有独钟。但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他,主要还是因为他主演了两部赫尔佐格的电影:《卡斯帕·豪泽之谜》(1974),《史楚锡流浪记》(1977)。
在《史楚锡流浪记》中,布鲁诺饰演了一位街头流浪艺人,可以说,带有他自身经历很强烈的色彩
和片中的流浪艺人一样,布鲁诺从小就辗转于各种精神病院和感化院之间,缺钱的时候就靠干些叉车的活儿来维持生活。上世纪70年代初,当赫尔佐格见到布鲁诺,就决定启用这个完全没有学过表演的人来参演他的电影,这就是《卡斯帕·豪泽之谜》。在后来的《史楚锡流浪记》中,布鲁诺也是本色出演,并且在影片中说了一段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对话:
布鲁诺:我在德国备受欺凌,现在我们到了美国,我以为情况会好转,我们最终能够达成梦想,但是我错了,人们对布鲁诺视若无睹,你也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伊娃:你至少没有被拳打脚踢。
布鲁诺:没错,但精神上的凌辱却一如既往,感化院里的情况,跟这里一模一样,在纳粹时期,如果有人尿床,受到的惩罚是整天用手举着晾衣绳,背后则是拿着棍子的教官,尿床的人要是因为忍耐不住而放下手来,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伊娃:你也受过惩罚?
布鲁诺:有,但当时的凌虐是有形的,今天他们对你的伤害却是无形的,他们不会拳脚相加,而是彬彬有礼地伤害你。人们的不屑弥漫在空中,清晰可见,这比以前更残酷。
事实上,1932年出生的布鲁诺,在纳粹时期被称为“ausschusskinder”,英文garbage children,纳粹当年对这种智障儿童进行有组织的活体医学试验——这是德国历史上非常不光彩的一页,所以战后“ausschusskinder”一词已经不再被使用。在那期间,没有家人去看望过布鲁诺,即便布鲁诺知道谁是他的亲戚,但那些亲戚从来没打算和他相认。也基本是在那个时候,布鲁诺自学了手风琴,试图通过音乐排遣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布鲁诺的歌声沙哑深邃,他说自己是传递(transmits)他的歌,而不是唱(singing)它。虽然赫尔佐格曾经说过,布鲁诺是德国电影界的无名英雄,但在拍摄完上述两部影片之后,赫尔佐格就中断了和布鲁诺的联系,按照布鲁诺的话说就是:对于赫尔佐格,我就是一次性用品。
布鲁诺2008年在柏林Stadtklause的演出,身边是他最爱的各种铃铛
不过,在布鲁诺去世前的2010年,赫尔佐格和他在第六十届柏林电影节期间的一个酒馆里“偶遇”,两人相互拥抱,基本也属于一笑泯恩仇了吧。但这个所谓的偶遇,其实是酒馆的老板有意安排的。
在绘画领域,塞拉菲娜·路易斯(1864-1942)的悲剧色彩似乎也并不亚于上文提到的弗兰克。塞拉菲娜生于法国瓦兹省阿尔西一个普通的牧人家庭,1岁丧母,7岁丧父,之后,她在姐姐家寄宿了几年,便进修道院做了女佣。接着,她来到巴黎北边的桑利斯(Senlis),依旧靠做女佣维生。业余时间,她自学画画,创建了独特的“花叶画”,塞拉菲娜从来不画人物和风景,没有钱买颜料的时候,就自己找各种原材料来配制颜料。
塞拉菲娜·路易斯生前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根本不知道她。直到1912年,德国艺术收藏家威尔罕姆·乌迪到他的邻居家里作客,看见墙上有一幅画,马上被其独特的风格吸引了。乌迪以为是出自哪位著名画家的手笔,一问才知道是塞拉菲娜画的。他大吃一惊,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强烈、最奇妙的作品”。
塞拉菲娜的画作
在乌迪的赞助下,1927年塞拉菲娜举办了画展,轰动一时。但三年后,由于法国的经济大萧条,乌迪停止购买塞拉菲娜的画。此时的塞拉菲娜,经常出现幻听,精神也越来越不稳定,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四年以后,威尔罕姆·乌迪宣布塞拉菲娜已经死亡。但实际上,她在精神病院里一直活到了1942年。她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朋友,被孤独地葬在当地的一个公墓里。
她的生前经历,在2008年被拍成了电影《塞拉菲娜》(Séraphine):
《塞拉菲娜》剧照
如今,她的画作已经被各大艺术博物馆收藏,成为“朴素派”代表画家之一。然而这一切,塞拉菲娜已经无缘得见了。类似这样生前默默无闻的人实在太多。再比如下面这位抽烟的女子,现在还有几个人知道她呢?
她就是被爱因斯坦称为“德国的居里夫人”的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1878-1968)。迈特纳1905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她是史上第二名获得维也纳大学学位的女性。多亏了他开明的父亲,鼓励其雄心壮志,资助她在柏林工作,也是在那里,她遇到了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
迈特纳和奥托·汉恩在实验室
普朗克因其驱逐女学生而声名狼藉,但这次他勉强地允许迈特纳进入他的课堂。之后,他让迈特纳做化学家奥托·汉恩的研究助手,随后,她与奥托·汉恩取得了几项开创性的发现。汉恩-迈特纳组合堪称20世纪早期原子核物理学家中的列侬-麦卡特尼组合,二人联合发表了几篇关于辐射和俄歇效应(Auger)的文章,但都是由迈特纳个人推理出来的。
在纳粹掌权之后,由于是犹太人,迈特纳被迫逃往荷兰。尽管是由于她的独特见解,才使世人知道核能并非原子聚变,而是她所命名的“裂变”,但她仍被禁止在汉恩的文章中被授予名誉,而汉恩因这一发现于1944年被授予了诺贝尔奖。直到上世纪90年代,诺贝尔委员会才决定公布真相,遗憾的是,迈特纳已于1968年安详辞世。人们为了纪念她,有几个天体以她的名字命名。
这个“无名者”的名单还可以罗列很长很长:查尔斯·德鲁(Charles Drew,德鲁开创了他称之为“血库”的血液存储系统),昆虫和植物学家米里安·罗斯查尔德(Miriam Rothschild),生物化学家多萝西·玛丽·霍奇金(Dorothy Mary Hodgkin),分子生物学家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诗人埃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留意那些所谓“无名的人”,以及那些被这个主流社会视为“失败的人”,在一个相对粗暴的社会评价体系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劣币驱逐良币”的非经济学层面——价值不高的东西往往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
卡尔维诺曾在短篇小说《黑羊》(Black sheep,黑羊在英国古代的传说中是魔鬼的化身,另外黑羊的羊毛也不如白羊羊毛值钱)里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在一个人人都是贼的国家里,那个唯一不愿意去偷盗的诚实的人最后家徒四壁,活活被饿死了。因为在白色羊群中出现了一只黑羊,这只黑羊就是另类,一定会被驱逐出去。
话说得有道理,被驱逐出去似乎是肯定的,但,被驱逐到哪里?被驱逐到的那个所在,是否也可能恰恰是一个自洽的所在?
这个被驱逐出去的黑羊的自洽,初听起来有些像当年的圈地运动,但我的理解不是这样。首先,在那里,“有用”和“无用”不再作为一个必然的硬性区分——查尔斯·德鲁推进了人类血库的建立,但杰克逊·C·弗兰克这样的精神型遗产,该如何评估他的影响?
埃米莉·狄金森(1830-1886)
其次,“有用”在那里的具体表述已经更新:它不再是基于主流价值的判断,而是——“在何种意义上,对谁有用?”埃米莉·狄金森对于物质至上主义者或许完全无用,但一个身居三线城市的苦闷青年可能就会把她视为遥远的精神同类;迈特纳对于非原子物理专业领域的人而言,往往意味着枯燥乏味,但对于她的同行来说,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第三,那里有你阶段性的同类。对,抑郁症者遇到了多梦者,幻肢者碰到了幻听者,科幻爱好者与程序员面基,顺行性遗忘者和逆行性遗忘者面面相对,性瘾者和性冷淡深度交谈……所以,即便你是搏击聚乐部里面的大奶子鲍勃,也会找到互诉衷肠的对象。
即便你误入了男性乳腺癌互助俱乐部……但这真的重要吗。
所以,做一只黑羊好吗?这真是一个坏问题。
因为,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一群黑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