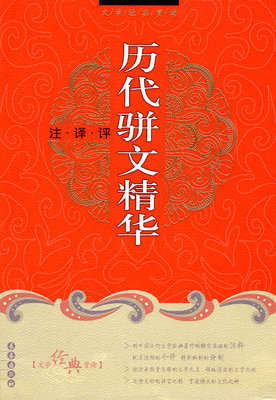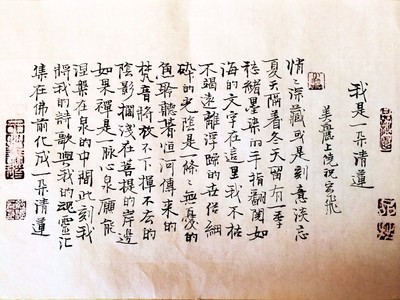花花 日期 : 2016-03-16 来源 : 阅读时间

许多人是因为叶嘉莹品的文字,而爱上了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人说,叶嘉莹就是为诗词而生的,她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一件事:诗词,她是一个一辈子都与诗词谈恋爱的女人。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是叶嘉莹的第一本传记,由本人口述,张候萍撰写,讲述了其人生经历、诗词创作、学术研究和师友交游。一般而言,传记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传主越惹是生非越好,越惊世赅俗越好,因为这样作品才容易出彩,否则,要在平易中写出奇崛,那自然是不太容易的。说实话,叶氏一生经历并不复杂,也无太多“故事”可讲,但就是因为她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挚爱,以及她所处时代与环境的别样色彩,才让她的经历更耐人寻味,也更引人入胜。
家国往事1924年,叶嘉莹出生于北平的一个旗人之家,祖上是叶赫那兰族人,与清代赫赫有名的词人纳兰性德同宗。对于自己的家世,叶嘉莹回忆说:“我们的姓氏是叶赫那兰,大家都以为是满族人,其实是属于蒙古的土默特族,努尔哈赤并吞了我们的部落,就成了蒙古裔的满族人了。”民国建立后,满族被要求改成汉姓,叶嘉莹祖父遂取叶赫那兰四个字中的第一个字为姓。
叶嘉莹父亲叶廷元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民航公司任职,母亲毕业于一所师范学校,婚后回家照顾家庭。叶家当时住在北京的一所老四合院里,这所院子是叶嘉莹做过“佐领”(旗人武职)的曾祖父购置的,叶嘉莹祖父是进士出身,所以家里大门上悬着一块“进士第”的匾额,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子。叶家的四合院很大,房间不少,后院还有个花园,著名学者邓云乡曾在文章中写过这所院子:“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我一闭眼仍可浮现在我眼前。……素洁的没有闲尘的明亮的窗户和窗外的日落,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人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吧。”
叶嘉莹是叶廷元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家里唯一的女儿,祖父不允许女孩子去学校读书,叶嘉莹便在这所大院子里接受了教育的启蒙,跟着伯父读书背诗。伯父国学素养深厚,膝下无女,见侄女爱好诗词,格外欢欣,叶嘉莹回忆说:“伯父说要我从小读中国的古书,我的姨母和母亲都在小声地念诗。虽然那时候女子没有地位,但我母亲还是在学校教过书的。当时妇女有礼教束缚,不能摇头晃脑地走来走去这样念诗,就小声念。”
祖父去世后,叶嘉莹考入笃志小学,后来又到北平市立二女中读书,由于家学渊源,叶嘉莹此时已经会写格律诗词,还能用文言与父亲通信。就在此时,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叶嘉莹的少女梦,父亲随国民政府仓促南迁,她和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后来母亲突然患病,需要去天津租界医院做手术,母亲执意不要叶嘉莹姐弟陪护,一人独自前往,不料在返回途中却因身体过度虚弱而辞世。17岁的叶嘉莹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悲伤地写下了令人肝肠欲断的《哭母诗八首》:“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
家国之运,紧密相连。
师从顾随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古典文学专业。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风严谨,当时北大和清华已迁往昆明,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强行接管,辅大是北平唯一一所不受日本人及其傀儡政权控制的大学。
在辅仁读书期间,叶嘉莹遇到了影响她一生的顾随先生。1942年9月,辅仁大学秋季开学后,国文系二年级年龄最小的女生叶嘉莹,走进了顾随先生“唐宋诗”的讲堂。多年以后,叶嘉莹在《顾随文集·代跋》中生动描述了自己初始受教时的感受:“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歌,然而却从来未曾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叶嘉莹从此师从顾随,在弥漫着唐风宋韵的诗词王国里遨游,先生的课程,她一节也没有落下,甚至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书后,她仍到母校和离家很近的中国大学旁听先生的课,直到1948年春离平南下。对于先生的讲授,叶嘉莹认为无出其右者,她在文章中曾这样评价:“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所谓记问之学的知识,先生一向都极少讲到,先生所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其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并且更能将之用多种之譬解,做最为细致和最为深入的传达。”
在追随先生的六年里,叶嘉莹记了十一册笔记和一寸多厚的活页纸,几十年来,叶嘉莹辗转海内外,一直将这些笔记带在身边,时常研读。后来她将其赠给顾随女儿顾之京,顾之京据此整理出版了《顾随诗词讲记》——如此的先生,如此的弟子,如今尚存否?
顾随也将这位清秀的女弟子视为自己的传人,在诗词创作和读书治学上都给予精心指点,他在信中对叶嘉莹说:“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1946年7月,叶嘉莹去拜望先生,并从老师那里借了几册英文书阅读,顾随一直鼓励、支持弟子学习英文,几天后他后致函叶嘉莹:“携去书数种,恐不能餍足下读书之欲;但如为学习英文计,或当不无小补耶?不佞虽不敢轻于附和鲁迅先生‘不读线装书’之说,但亦以为至少亦须通一两种外国文,能直接看‘洋鬼子’书,方能开扩心胸,此意当早为足下所知,不须再喋喋也。”谆谆教诲之意,溢于言表。
从叶嘉莹早年的照片中可以看出,辅仁时期的叶嘉莹纤瘦高挑,气质高贵,给人以距离感。据她的一些老同学回忆,大学毕业时,一些男生私下评价女生,给叶嘉莹的评语是:“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顾芳,我行我素。”
叶嘉莹是生活在诗词世界里的女神,她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
岁月流影对于这样一位一生与诗词相伴的女子,一定会有一段浪漫而传奇的爱情吧?
现实与理想其实相距甚远,“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许多年后,叶嘉莹如此平静地回忆。22岁那年,叶嘉莹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后来的先生赵东荪,正如她所言,一切与诗歌无缘,与浪漫也无缘,赵东荪是一位中学老师的弟弟,“不爱诗词,偏好政治”,当时在海军服务。不久两人在上海结婚,几年后江山易手,叶嘉莹随丈夫浮海南渡。
1950年岁末,爱议论政治的赵东荪被怀疑是“匪谍”,突然被捕入狱;次年6月的一个清晨,正在彰化女中教书的叶嘉莹也和其他老师一起被抓了起来。对于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著名散文家王鼎钧感触颇深:“国民党因为大陆的失败教训惨痛,发现许多忠实的干部都叛变了,有些干部甚至从进军校的那天起就是共产党派去的,所以到了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很严厉地要肃清一切可疑的人。当时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向敌人学习’。我们常常夜里做梦,上半夜做一个梦被共产党抓去,要杀头,下半夜又做一个梦,被国民党抓去,也要杀头。”
叶嘉莹莫名其妙地被捕,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但随之失业,没有学校敢聘用她。生活失去了来源,丈夫又杳无音信,叶嘉莹抱着孩子去高雄投奔丈夫的姐姐。姐姐的家狭小逼仄,叶嘉莹只好在走廊打地铺,第二天要在别人起床之前起来,中午又怕女儿吵闹影响别人休息,只能抱着孩子到远处的树底下暂避。对于当年那段时光,她在《转蓬》中这样记述:“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生活的磨砺让这位吟诗作曲的“林妹妹”变成了家庭妇女,以至于赵东荪的外甥、后来的台湾长庚大学校长包家驹竟然不知自己的舅妈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第一次知道舅妈是位教授,竟然是在她已任教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里。原先在我的印象中,舅妈只是一个在家里洗衣擦地、架着竹笼为女儿烘烤尿片、在厨房里洗菜的妇人。直到筹建长庚医学院时,聘来的国文老师中就有人听过舅妈的课,我才意识到,原来舅妈有这么高的成就!”
几年后赵东荪释放出狱,叶嘉莹也经人推荐到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古典诗词。1966年,叶嘉莹去美国访学,在哈佛大学与海陶玮教授合作研译中国诗词。1969年,叶嘉莹举家移民加拿大,获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职。
1970年代末,叶嘉莹与家人回国探亲,在火车上偶遇一些青年在读《唐诗三百首》。这个发现让叶嘉莹惊喜不已,也让她萌生了回国讲学的念头。经与相关机构沟通,不久叶嘉莹就站在了南开大学的讲台上,此后她年年回国与学子分享诗词之美,2014年秋,90岁高龄的叶嘉莹定居南开大学为其修建的迦陵学舍(叶嘉莹号迦陵)。
对叶嘉莹来说,逝去的是光阴,留下的是诗心。(来源/王凯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爱华网
爱华网